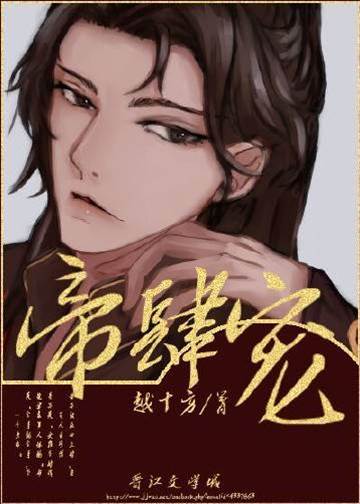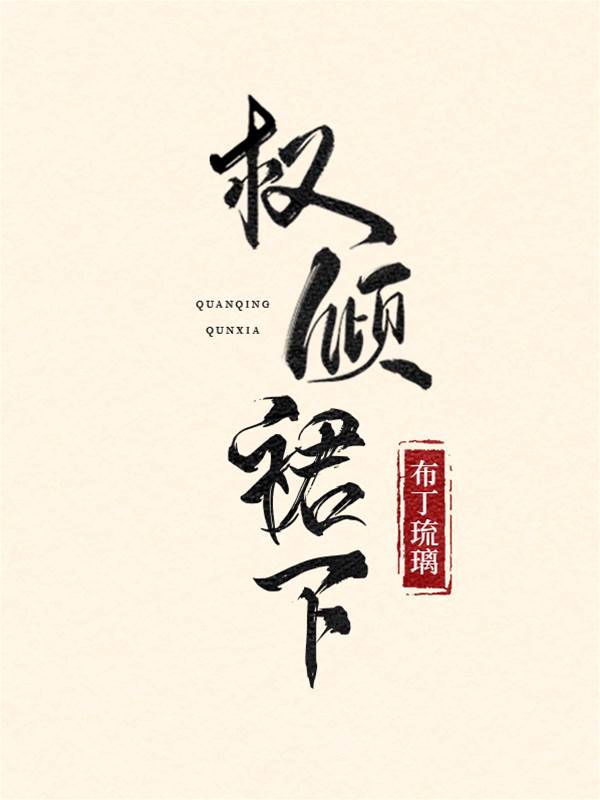《攻玉》 第70章 【雙更合一】這個局不好……
藺承佑眼里的笑意一凝。
今晚之前,他已經把三位害孕婦的底細大致過一了。
最近遇害的榮安伯世子夫人小姜氏,是榮安伯世子宋儉的續弦,宋儉的原配姜氏三年前因難產而亡,而小姜氏正是姜氏的妹妹。
據聞,當初宋儉娶姜氏時曾遭到伯爺和夫人的極力反對,原因是姜氏的阿爺過去在淮西道的某位將領帳下任幕僚,來長安后雖說有心應試,卻是屢試不第。這樣的人家,可謂門第寒微。
但宋儉對姜氏一見傾心,誓愿非不娶,巧彭震的夫人隨丈夫來京述職,聽聞此事后,彭夫人主登門拜訪榮安伯夫人,說姜家與算是遠房表親,那年在淮西道又過姜氏母親的大恩,早就認了姜氏的母親做姐姐,說起來姜氏算是的外甥。
有了彭夫人作保,伯爺和夫人稍有松,加上姜氏雖門第不高,卻算得上知書識禮,老兩口在親眼見過姜氏一面后,最終同意了這門親事。
親后宋儉與姜氏同膠漆,沒多久就生下了一對龍胎。孩子們長到兩歲時,姜氏再次懷孕,卻在臨盆時因為難產不幸亡,時隔一個月,老夫人也因病去世了。
伯爺因府中長期無主母主事,等兒子孝期滿了,有意讓兒子再娶,宋儉卻執意不肯續弦。
一年多前,妻妹小姜氏因著探小外甥在伯府小住了一段時間,過后沒多久,宋儉突然造訪老丈人,說想求娶妻妹小姜氏做填房。
據嚴司直打探后回來說,榮安伯府的下人們背地議論,宋儉之所以求娶小姜氏,除了因為小姜氏是孩子們的親姨母,還因為容貌肖似姜氏。
此外還有一些不堪的流言,例如小姜氏正是在伯府住的那段時日與姐夫有了首尾,宋儉為了顧全二人的名聲,不得不上門求娶……又說小姜氏嫁給姐夫時都已經十九了,先前遲遲不肯嫁人,是因為十五六歲時就相中了自己的姐夫。
Advertisement
姜氏姐妹都是華州人,小姜氏嫁榮安伯府整一年了,出事時恰好懷孕六個月。
第二起案子的害人舒麗娘,巧也是華州人,舒麗娘父母早亡,十七歲嫁給了華州一位落第書生,去年丈夫不幸因病暴亡,舒麗娘與婆家歷來不偕,又無父兄相依,只好投奔長安的堂親,這位堂親正是京兆府的舒長史,名舒文亮。
今日藺承佑原是打算先去找一趟舒長史和鄭仆的,除了向他們打聽舒麗娘過去在家鄉的種種,也想知道為何一個好好的良家婦人要給人做別宅婦,不料后頭撞上了耐重現世。
至于第一起案子麼……
因白氏是與丈夫王藏寶一道害的,同州府的柳法曹在排查害人的背景時,一直著重于調查王藏寶這邊的種種。譬如王藏寶是否與人結過仇、因何舍棄同州的家業來長安……而關于白氏的為人、往日可曾與人結過怨,案宗上卻只字未提。
他只知道白氏今年二十有二,懷孕五個月了。
回顧完三樁案子,藺承佑心里的疑簡直不住,照莊穆這樣說,出事前莊穆莫非調查過三位害孕婦?
這與他最初的設想有些出。
莊穆說完那句話后就不再開腔,藺承佑等了一會,起到桌上端起一壺蝦蟆陵,提壺回到鐵籠前,將莊穆上的捆綁一一松了,只留下腳銬和手銬。
做完這一切,藺承佑親自斟了一大碗蝦蟆陵,把碗放到莊穆面前,笑道:“這樣吃喝才暢快。”
莊穆咽了口口水,不顧手上還殘留著干涸的痕,捧起碗二話不說喝了起來,咕嘟咕嘟喝完酒,迫不及待把碗放到地上,兩眼閃爍著貪婪的亮,等待藺承佑給他斟第二碗。
Advertisement
一口氣喝了三大碗酒,莊穆才仿佛緩過勁來,捧起另一邊的湯碗,埋頭吃那碗冒著熱氣的牢丸,吃飽喝足之后,他并不急著把碗放下,只不聲抬起眼睛,從碗沿上方看向藺承佑。
他深深看藺承佑一眼,徑自放下碗,點點頭沉聲道:“年紀不大,倒這樣沉得住氣。”
藺承佑臉上笑意不減,耐心十足地等待著。
莊穆默了一晌:“我可以把我知道的全都告訴你,前提是你得給我準備好我要的東西:兩百金,一匹快馬,一份能保證我順利離開潼關的過所——還有放我走。”
藺承佑哂笑:“閣下倒是敢開價。”
莊穆扯了扯角:“這四條對旁人來說難辦,對你來說卻易如反掌。你應該早就料到了,兇徒很快還會再犯案,可此人太狡詐,你們大理寺至今沒找到有用的線索,而我,卻實實在在與真兇打過道。”
藺承佑氣定神閑道:“真兇肯讓你被我們大理寺捉住,自是有把握你提供的線索絕不能查到他頭上,一個對斷案未必有幫助的人,人如何答應你提出的這些無理要求。”
莊穆冷笑道:“我雖未不知道兇手的真實份,但我這一個月來知道的種種,比你們大理寺查一年都要多,想來你很清楚這一點,才會屢次跑到牢中拿好酒好菜款待我。”
藺承佑道:“你要是別無所求,大可以繼續拒絕吃喝,肯接我招待的酒菜,豈不說明你也迫切地想對付那兇徒。”
莊穆滯了滯。
藺承佑提壺給莊穆又斟了一碗酒:“我早說過,你想借大理寺之手報一箭之仇,我想利用你提供的線索找到兇手,你我各取所需,但單憑你知道的那些事,不足以在短時日查出兇手是誰。”
Advertisement
莊穆面復雜地看著碗里的酒。
藺承佑笑道:“要緝兇,把你知道的說出來還不夠,你最起碼要配合大理寺做個局,這個局若是能功將兇手捉住,你說的那四條——”
莊穆盯著藺承佑,藺承佑卻故意踟躕起來,過片刻才笑著頷首:“或可勉力試一試。”
莊穆神稍松,然而眼中卻又閃過一猶豫。
藺承佑抬頭看他:“你該知道你的機會不多了,一旦真兇率先查到了你的幕后之人,再怎麼設局也無用了,到時候你對大理寺來說毫無用,你猜我會不會答應你的條件?”
莊穆咬了咬牙,端起酒碗一口喝盡,忽道:“三月初一那日,我的一位友人突然讓人給我傳話,說他的某位下屬三年前在外地丟失了某個重要件,上月這件突然在同州出現了,友人懷疑賊人此刻就在同州,讓我即刻前去將件和賊子一道捉回長安。”
藺承佑沒吭聲,這位所謂的“友人”,想來就是莊穆真正的主家了。
“等我趕到同州境,那件卻在市廛中消失了,我在同州最熱鬧的街坊找了家客棧住下,暗中調查此事。”
“什麼樣的件?為何能一問就知?”藺承佑冷不防道。
莊穆不語。
藺承佑一嗤:“即便你不說,我到同州府查幾日也能查明白,何必浪費彼此的力。”
莊穆耷拉著眼皮道:“是一面乾坤八卦鏡,鏡面并非圓狀,而是彎月形,名曰月朔鏡。”
藺承佑長眉一揚,又是“月朔”。
“此鏡一面一面明,面為赤,面為玄,據說此鏡藏妖,只要用面對準剛死之人,能將人的魂魄打散,即便那人當場化作厲鬼,也會忘記遇害前的一些事,從此淪為傀儡,甘持鏡人的擺布。”
Advertisement
藺承佑暗忖,聽上去倒是與師公的那面無涯鏡極像,只是師公的那面鏡子照的是冤祟之氣。凡是被邪祟沾染過的件或是尸首,只消用這面無涯鏡一照便知,而莊穆說的這面能人魂魄的鏡子,顯然是用邪打造出來的害人法。
忽又想到,這鏡子擺布和折磨鬼魂的作派,倒與彭玉桂折磨田氏夫婦的七芒引路印有點像,但七芒引路印這樣的邪早已被皇伯父下旨掃除了,現今流傳在世上的,只有一些殘破的版本。
大約十五六年前,皇伯父聽一位臣子匯報了一例用邪害人的慘案,皇伯父大,發愿將天下害人的邪門暗一舉掃清,委托師公部署此事,又下旨長安各家道觀和大寺全力配合。
師公在一眾僧道的配合下,發擿伏,暗中撒網,前后花了四五年時間,終于將當時長安邪的門徒一網打盡,前后沒收了十來本邪籍,同時銷毀了數十件害人的法。
事后師公將那幾本邪門籍鎖在青云觀的寶閣里。這樣做無非是怕各州縣還暗藏著不懷邪的門眾,萬一這幫人用邪作,他們也能及時通過這些籍弄明白邪害人的原理。
他自小在青云觀廝混,早就撬開鎖看過那幾本籍,其中一本就是記錄了七芒引路印的《魂經》,他正是看過這本書之后,才知道世上還有這等厲害的拘魂。
而那本記錄了“絕蠱”邪的籍,也是他那時候無意中翻看到的。
正想著,就聽莊穆道:“這鏡子因為吞多了怨靈的殘魂,一貫怨氣極重,每逢日,鏡面里會自發流淌出污來,持鏡人若將其帶在上,往往被污弄臟而不自知,此事只有我那位友人和他的幾位朋友知道,那鏡的賊子似乎并不知。我那友人之所以知道鏡子在同州現了,是因為有幾位同州來的商人在長安酒肆中議論,說上回有個道士在市廛中行走時,好端端地從腹流出污來,奇怪那人面上并無傷痕,而且被人提醒之后,那道士馬上匆匆離去……”
藺承佑忽道:“這鏡子這樣邪門,拿它害人的時候就沒什麼講究?”
莊穆喝了口酒:“頗有講究。無論是用此鏡‘拘役魂魄’,抑或是‘打散魂魄’,都極損德,持鏡人若是不想損壞自修為,在用鏡子害人之前,最好先弄明白害人自己生前是不是做過惡事,若非良善之輩,落個魂魄不全的下場也可算因果可循,那麼反噬到持鏡人上的孽報也會一些,所以持鏡人往往只挑惡人下手。”
藺承佑想了想說:“你就是據此認定那三位害孕婦并非良善之輩?”
莊穆冷笑:“這兇徒害的可不是一個人,而是好幾位懷六甲的孕婦,即便是我這樣的潑皮無賴,也覺得這等事太過傷天害理,那人如果不想搭上全修為,手前自然會好好考量。”
藺承佑默了默:“兇徒又是如何知道這三位害婦人都做過何事的?”
莊穆道:“我也不知道,但鏡面流的事是一月前發生的,說明那賊人早就到了同州,可是這一月之并非發生離奇的詭案,可見此人起初并未挑好下手的孕婦,為何一月后將目標瞄向了白氏,應該是確定殺害白氏對自己的修為損傷最小。”
藺承佑沉不語,兇徒殺的不只是白氏,還殺了的丈夫王藏寶。
挑選懷孕婦人的時候慎之又慎,順手殺王藏寶的時候就不怕損及修為了?
據柳法曹所言,這對夫婦是因為得罪了當地的地才舍棄家業來長安。
這點早就讓他覺得匪夷所思,王藏寶夫婦開的那家五行是從父輩手里傳下來的,此前已在當地開了幾十年了,僅僅因為斗得罪了幾個地,就連祖業都不要了?
可惜這幾日他將重點全放在月朔君上,沒顧得上細究這對夫婦本的種種不同尋常之。
“我查了幾日毫無線索,本打算回長安復命,就在這時候,我住的那家客棧忽有兩位旅商說,早上進城的路上,突然看到一個道士的道袍沾染了污,旁人本想提醒,那道士卻很快就不見人影了。我打聽到那地方是郊外的烏山腳下,忙又趕往烏山。不料住下當晚,附近的居安客棧就發生了命案,死的恰是一對年輕夫妻。
猜你喜歡
-
完結8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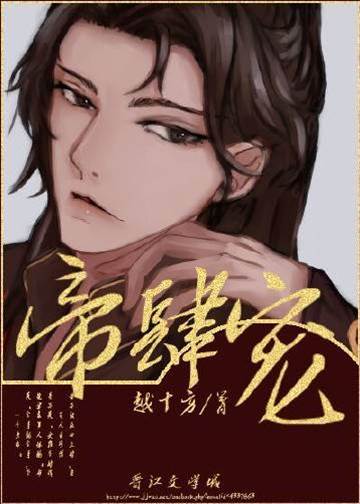
帝肆寵(臣妻)
從軍六年渺無音訊的夫君霍岐突然回來了,還從無名小卒一躍成為戰功赫赫的開國將軍。姜肆以為自己終于苦盡甘來,帶著孩子隨他入京。到了京城才知道,將軍府上已有一位將軍夫人。將軍夫人溫良淑婉,戰場上救了霍岐一命,還是當今尚書府的千金,與現在的霍岐正當…
28.8萬字8 26578 -
完結13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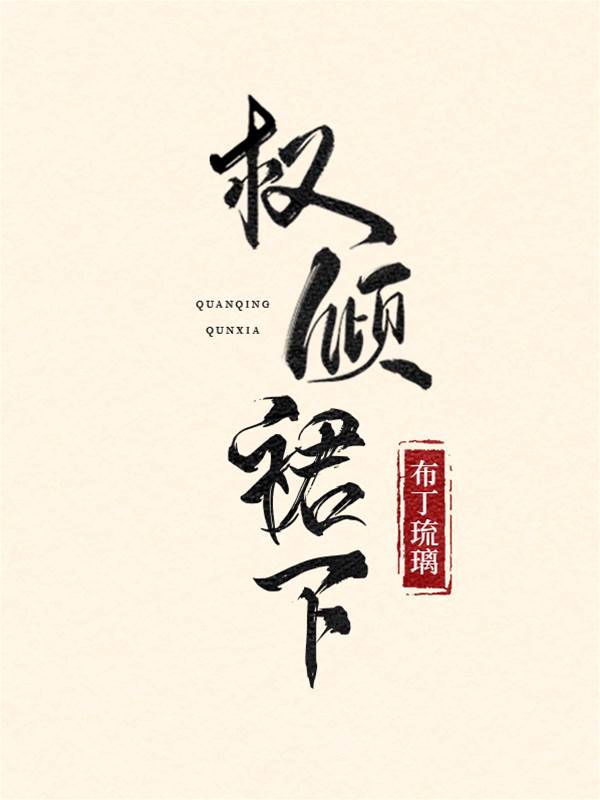
權傾裙下
太子死了,大玄朝絕了後。叛軍兵臨城下。為了穩住局勢,查清孿生兄長的死因,長風公主趙嫣不得不換上男裝,扮起了迎風咯血的東宮太子。入東宮的那夜,皇后萬般叮囑:“肅王身為本朝唯一一位異姓王,把控朝野多年、擁兵自重,其狼子野心,不可不防!”聽得趙嫣將馬甲捂了又捂,日日如履薄冰。直到某日,趙嫣遭人暗算。醒來後一片荒唐,而那位權傾天下的肅王殿下,正披髮散衣在側,俊美微挑的眼睛慵懶而又危險。完了!趙嫣腦子一片空白,轉身就跑。下一刻,衣帶被勾住。肅王嗤了聲,嗓音染上不悅:“這就跑,不好吧?”“小太子”墨髮披散,白著臉磕巴道:“我……我去閱奏摺。”“好啊。”男人不急不緩地勾著她的髮絲,低啞道,“殿下閱奏摺,臣閱殿下。” 世人皆道天生反骨、桀驁不馴的肅王殿下轉了性,不搞事不造反,卻迷上了輔佐太子。日日留宿東宮不說,還與太子同榻抵足而眠。誰料一朝事發,東宮太子竟然是女兒身,女扮男裝為禍朝綱。滿朝嘩然,眾人皆猜想肅王會抓住這個機會,推翻帝權取而代之。卻不料朝堂問審,一身玄黑大氅的肅王當著文武百官的面俯身垂首,伸臂搭住少女纖細的指尖。“別怕,朝前走。”他嗓音肅殺而又可靠,淡淡道,“人若妄議,臣便殺了那人;天若阻攔,臣便反了這天。”
52.5萬字8 22198 -
完結1141 章

腹黑萌寶藥神娘親霸道爹
她是二十三世紀的醫學博士,一朝穿越成了被父親虐打,被妹妹誣陷,被未婚夫詛咒,被灌下雙重媚葯的廢物大小姐,悲催的是在手不能動,眼不能睜,媚藥發作之時,竟被一個來歷不明的男人當成了解葯,拆骨入腹,吃乾抹淨。 五年後,她以聞名天下的藥神醫和煉丹奇才丹霄的身份攜雙寶回歸,左手空間右手丹藥,一張金色面具,一桿追魂銀鞭,上打權貴下復讎,將各路渣渣虐的生不如死。 “娘,報完仇去幹嘛?” “為你妹妹找血庫,啊不,找你們的爹爹。” 找到那個五年前睡了她就跑的狗男人,卻不料,狗男人就和她同吃同住在身邊。 “娘,我找到爹爹了。” 女兒抱著某王爺的脖子看著她。 “王爺,你身中上古火髓之毒,時日無多......” “顏幽幽,五年前,京郊城外亂葬崗,你可還記得?” 某霸道王爺抱她入懷,看著她腹黑一笑,顏幽幽咬著牙“走,找解藥去......” 一對一,男強女強,雙處雙潔,無虐不狗血。
197.4萬字8 148568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