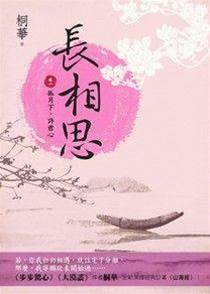《坤寧》 第060章 貓
陳淑儀也是從小到大就沒過這麼大的刺激, 又因與薑雪寧有齟齬在先, 這口氣無論如何也忍不下去, 一時被氣昏了頭,怒極之下才揚了手。
就算是沈芷不出現, 這一掌也未必就真的落下去了。
畢竟大家同為長公主伴讀,吵兩句還能說是口角, 誰先上手那就就是誰理虧,沒必要與薑雪寧這麼一番折騰。
可樂長公主不早不晚,偏偏在這個當口出現。
太尷尬了。
簡直讓人百口莫辯!
陳淑儀像是被人一盆涼水從頭潑到腳似的, 渾都寒了, 忙躬向沈芷一禮“長公主殿下容稟, 是臣與薑二姑娘一言不合爭執起來, 薑二姑娘口齒伶俐, 臣說不過, 一時氣昏了頭, 是臣的過錯,還長公主殿下寬宏大量,饒恕臣此次無禮。”
聲音有些輕, 顯然也是畏懼的。
沒了剛才的火氣輕而易舉就冷靜了下來,知道現在發生的這件事有多嚴重,更知道沈芷原本就是要偏心著薑雪寧一些的, 此刻無論如何都不能狡辯, 最好是在澄清的同時低頭認錯,忍過此時, 將來再找機會慢慢計較。
薑雪寧心底嗤了一聲,暗道趨炎附勢慫得倒是很快,先前那誰也不看在眼底的囂張到了份比更尊貴的人麵上,又剩下多?
本來相安無事,陳淑儀先先賤!
反正梁子都結下了,不想對方就這麼簡單地敷衍過去,非要氣死讓心裡更膈應不可!
於是,一副淒淒慘慘切切模樣,薑雪寧抬起了朦朧的淚眼,著陳淑儀,子還輕微地抖了起來,彷彿不敢相信竟說出這般顛倒黑白的話來一般“陳姐姐的意思,竟、竟是我欺負了你不?我,我……”
Advertisement
話到一半便說不下去了。
咬了瓣,睜大眼睛,好像第一次認識了陳淑儀一般,還流出幾分真的不忿與痛心。
整個奉宸殿安靜得什麼聲音也聽不見。
周寶櫻目瞪口呆,裝著餞的紙袋從手裡落下來,掉到地上;
尤月更是後腦勺發涼,慶幸自己剛才走了一下神沒跟著陳淑儀一起譏諷薑雪寧,不然現在……
方妙也一臉呆滯,想過這位薑二姑娘是厲害的,可沒想到“厲害”到這個程度;
……
連蕭姝都未免用一種震驚的眼神看著薑雪寧,彷彿從來沒有真正認識過一般,再一回想起當日不由分說將尤月按進魚缸裡的形,隻覺遙遠得像做夢。
那凜冽冷酷的架勢……
和現在這個弱可憐楚楚人的,是一個人?
沈芷卻是抬步走到了薑雪寧的邊,猶豫了一下,還是輕輕出手去搭住了薑雪寧的肩。
薑雪寧覺到,便要回轉頭來,繼續賣慘。
然而當轉過眸的瞬間,卻對上一雙不同尋常的眼沈芷看的眼神不再是以前那般總充滿著一種憧憬似的甜,裡麵竟有些黯然,有些悔愧,言又止,說還休。
末了偏朝綻開個安的笑。
這一剎那,薑雪寧想到的竟是昨日燕臨看的眼神,熬煎裡藏著忍,於是心底便狠狠地一――
沈芷是從慈寧宮回來的,而慈寧宮正在清查務府的事,是玉如意一案終究要牽扯到勇毅侯府的上了嗎?
若非如此,沈芷不會這樣看。
這念頭一冒出來,與陳淑儀這一點意氣之爭,忽然都變得不重要起來。
但沈芷卻沒準備就這樣罷休。
終究是記得薑雪寧一開始是不打算宮的,是燕臨來找,也想宮,是以才前後一番折騰,將強留下來。
Advertisement
想這宮中有什麼好為難的呢?
一則有燕臨護著,二則有撐腰,便是有些醃h汙穢事,也不至於就害到的頭上。
可今日慈寧宮中嗅出的腥風雨讓知道,是自己錯了,也讓忽然有些明白昨日燕臨為什麼要當眾撇清與寧寧之間的關係。
換了是,也要如此的。
可不知道時是為寧寧不平甚至憤怒,知道之後卻是埋怨自己也心疼寧寧。
也許往後,再沒有燕臨能護著,那便隻剩下自己了。
再如何天真縱,沈芷也是宮裡長大的孩子。
不至於看不出寧寧神間帶了幾分戲謔的做作,該是故意演戲氣陳淑儀呢,可方纔所見陳淑儀的放肆卻不作偽,更不用說知道絕不是一個會主陷害旁人的人――
能提筆為點了眼角舊痕,覆上瓣,說出那番話的薑雪寧,絕不是個壞人。
沈芷輕輕抬起眼睫,注視著陳淑儀,並無怒模樣,可平靜卻比怒更人心底發寒,隻一字一句清晰地道“你的解釋,我都不想聽。你為臣,被遴選宮作我的伴讀,且你我也算有相識的舊誼,我不好拂了陳大學士的麵子,讓你宮來又被攆出去。隻是你,還有你們,都要知道,薑家二姑娘薑雪寧,乃是本宮親自點了要進宮來的。往後,對無禮,便等同於對本宮無禮。以前是你們不知道,可本宮今日說過了,誰要再犯,休怪本宮不顧及麵。”
眾人全沒想到沈芷竟會說出這樣重的一番話來!
一時全部噤若寒蟬。
薑雪寧卻從沈芷這番話中確認了什麼似的,有些恍惚起來。
陳淑儀也完全不明白沈芷的態度怎會忽然這般嚴肅,話雖說得極難聽,是一個掌一個掌往臉上扇,可實在也不敢駁斥什麼,也唯恐禍到己,隻能埋了頭,戰戰兢兢應“是。”
Advertisement
沈芷又道“你既已知道自己無禮,又這般容易氣昏頭,便把《禮記》與《般若心經》各抄十遍,一則漲漲記,二則靜靜心思,別到了奉宸殿這種讀書的地方還總想著別的七八糟的事。”
陳淑儀心中有怨,麵都青了。
強憋了一口氣,再次躬道“謝長公主殿下寬宏大量,淑儀從今往後定謹言慎行,不敢再犯。”
沈芷這才轉過目來,不再搭理,反而到了薑雪寧的書案前,半蹲了,兩隻手掌疊在書案上,尖尖的下頜則擱在自己的手掌上,隻出個戴著珠翠步搖的好看腦袋來,眨眨眼著“寧寧現在不生氣了吧?”
薑雪寧原本就是裝得更多。
上輩子更多的氣都過,哪兒能忍不了這個?隻是看了沈芷這般小心翼翼待的模樣,心裡一時歡喜一時悲愁,隻勉強地出了個難看的笑容,上前把拉了起來“堂堂公主殿下,這像什麼樣?”
沈芷不敢告訴慈寧宮裡麵的事兒,隻盼哄著開心“這不逗你嗎?怕你不高興。”
薑雪寧約能猜著目的,是以破涕為笑。
咕噥道“被殿下這般在意著,寵信著,便是有一千一萬的苦都化了,哪裡能不高興?”
沈芷這纔跟著笑起來。
殿中場麵一時有種暖意融融的和樂。
可這和樂都是們的,其他人在旁邊看著本不進去。
陳淑儀一張臉上神變幻。
蕭姝的目卻是從殿中所有的麵上劃過,心裡隻莫名地想到陳淑儀平日裡也算是言出錯的謹慎人,心氣雖不免高了些,卻也算是個拎得清的,可一朝到了宮中這般頗拘束的地方遇著沖突,也不免失了常,發作出來;這位薑二姑娘宮之後,看似跋扈糊塗,可竟沒出過什麼真正的昏招,對宮中的生活並未表現出任何的不適和惶恐,宮時是什麼樣,現在似乎還是那樣,竟令人有些不敢小覷。
Advertisement
還好這場麵沒持續多久。
辰正二刻,教《禮記》的國史館總纂張重冷著一張臉,胳膊下夾著數本薄薄的書,便從外麵走了進來。
眾人包括沈芷在於是都回到了自己的位置。
“學生們見過張先生。”
張重國字臉,兩道眉濃,可一雙眼睛卻偏細,皺起眉頭來時便會自然而然地給人一種刻薄不好相之。
此刻掃一眼眾人,竟沒好臉。
他手一抬,將帶來的那幾本書給了旁邊的小太監,道“我來本是教禮,並非什麼要的學目。可讀史多年,隻知這世上是沒有規矩不方圓,周朝禮樂崩壞乃有春秋之。初時我等幾位先生說,教的是公主與達貴人家的小姐,本是將這一門定為學《誡》,隻是謝師說諸位伴讀都是知書達理,該學的早學過了,不必多此一舉,不妨教些家國大義,是以才將書改了《禮記》。然則以老朽近日來在翰林院中的聽聞,這奉宸殿雖是進學之所,可卻有人不知尊卑上下,連子溫端方的賢淑都不能示於人前,實在深覺荒謬又深覺負重任。是以今日擅改課目,先為諸位伴讀好生講一講《誡》,待《誡》學完,再與大家細講《禮記》。”
小太監將書一一呈到眾人桌上。
薑雪寧低頭一看,那封皮上赫然寫著醒目的兩個大字――
戒。
一時也說不上是為什麼,膈應到了極點,便是方纔與陳淑儀鬧了一樁也沒這麼惡心。
就連一旁蕭姝見了此書,都不由微微變。其他人則是麵麵相覷。
唯有陳淑儀終於出個舒展了眉頭的神,甚至還慢慢點了點頭,似對張重這一番話十分贊同。
張重是個規矩極嚴的人,既做了決定,便本不管下麪人包括長公主在是什麼表,畢竟長公主將來也要嫁人,聽一聽總是沒錯的。
他自顧自翻開了書頁,便眾人先看第一篇《卑弱》。
隻道“古時候,嬰出生數月後,都不能睡床榻,而是使其躺在床下,以紡錘玩樂,給以磚瓦,齋告先祖。這是為了表明其出之卑弱,地位之低下。紡錘磚瓦則意在使其明白,們當盡心勞作,從事耕織,且幫夫君準備酒食祭祀。所以,為子,當勤勞恭敬,忍讓忍辱,常懷畏懼……”
整個殿一片安靜。
沈芷的麵也有些晴不定。
薑雪寧坐在後麵角落裡,聽見這番話卻是不由自主地想起了上一世自己與蕭氏一族鬥狠時,前朝那些雪片似飛來力勸皇帝廢後的奏摺。曾在沈d病中翻出來看過,上頭一字一句,字字句句皆是婦德禍,與張重此刻之言的意思就重合了個七八。
嬰生下來連睡床都不配!
哪裡來的狗屁道理!
張重還板著一張臉在上頭講。
薑雪寧卻是豁然起,直接把自己麵前的書案一推!
“吱嘎,哐啷!”
書案四腳一下從大殿的地麵上重重磨過,發出刺耳難聽的聲響,書案壘著的書本與筆墨全都倒塌滾落下來,一片響,驚得所有人回頭向來。
張重立刻皺起了眉頭看“怎麼回事?”
薑雪寧道“先生,我惡心。”
張重也知道這是個刺兒頭了,聽見這話臉都變了“你罵誰!”
薑雪寧一臉茫然“真是奇怪,我說我犯惡心,先生怎能說我罵人呢?許是我昨日沒注意吃壞了肚子,也可能是今日聞了什麼不乾不凈臭氣熏天的東西,若再這殿中嘔出來,隻怕攪擾了先生講學。所以今日請恕雪寧失禮,先退了。”
話說得客氣,然而邊的笑容是怎麼看怎麼嘲諷,半點沒有客氣的樣子,轉從這殿中走時,連禮都沒行一個。
所有人都驚呆了。見過逃學的可逃得這麼理直氣壯膽大妄為的,可真就見過這一個!
張重更是沒想到這薑雪寧非但不服管教,竟然張撒謊當著他的麵從他課上走,一張原本就黑的臉頓時氣了豬肝,抬起手來指著背影不住地抖,隻厲聲道“好,好,好一個不服管教的丫頭片子!這般頑劣任之徒,若也配留在奉宸殿中,我張重索連這學也不必教了,屆時且人來看看,是你厲害還是我厲害!”
猜你喜歡
-
完結2877 章

傾世醫妃太難撩
一朝穿越,蘇念薇被人指著鼻子罵懷了個野種。 死裡逃生之後她活著的目的:報仇、養娃兒,尋找渣男。 一不小心卻愛上了害她婚前失貞的男人。 這仇,是報啊還是報啊? 她逃跑之後,狠厲陰冷的男人帶著孩子找上門來。 當年,他們都是被設計了。 兩個睚眦必報的人一拍即合,攜手展開了絕地反擊。 女人:我是來報仇的! 厲王:這不妨礙談情說愛。
251.8萬字8 60165 -
完結5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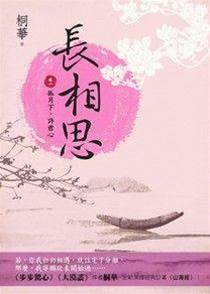
長相思
生命是一場又一場的相遇和別離,是一次又一次的遺忘和開始,可總有些事,一旦發生,就留下印跡;總有個人,一旦來過,就無法忘記。這一場清水鎮的相遇改變了所有人的命運,
63.4萬字8 5805 -
完結396 章

公府嬌奴
宋錦茵在世子裴晏舟身側八年,於十五歲成了他的暖床丫鬟,如今也不過二八年華。這八年裏,她從官家女淪為奴籍,磨滅了傲骨,背上了罪責,也徹底消了她與裴晏舟的親近。可裴晏舟恨她,卻始終不願放她。後來,她在故人的相助下逃離了國公府。而那位矜貴冷傲的世子爺卻像是徹底瘋了一樣,撇下聖旨,尋遍了整個京都城。起初他看不清內心,隻任由恨意滋長,誓要拉著宋錦茵一起沉淪。後來他終於尋到了宋錦茵,可那一日,他差一點死在了那雙淡漠的眼中。
83.2萬字8.18 46905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