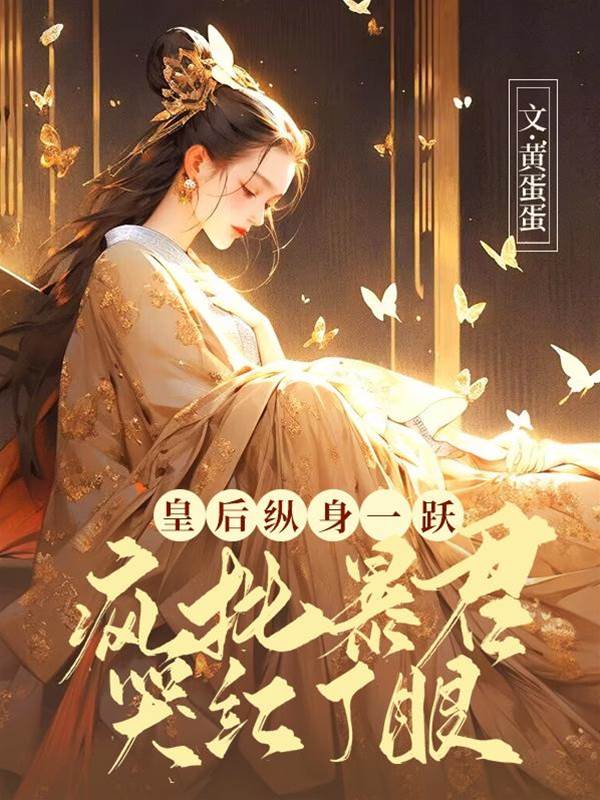《小公主變貓後,大將軍偷聽她心聲》 第45章 三兒
拓跋潯不是真的想計較香噴噴的烤鴨——好吧,他是有點。
但其真正的目的,更多是回憶過往時。
……楚陌亦想。
他們也不過二十來歲的年齡,卻已在回味往昔,回味那無拘無束,無憂無慮的歲月。
兩人或笑或吵地說了不往事,拓跋潯還罵了遠在京城的景策,奈何,如今他了太子,楚陌沒有立場說他壞話,隻能聽著,然後默默在心裏罵。
不得不說,也是個人。
“當年,竹束但凡接了那姑娘,也不至於現在還是個稚。堂堂大遂太子還是個稚,笑死我。”拓跋潯笑得直顛,笑得前仰後翻。
“還有你。”許是離了稚這個份,拓跋潯很是囂張,像是把連弩似的,大範圍無限製殺,“不是我說你,你現在……”
他上下打量,忍住笑道:“不會還是幹幹淨淨的吧?”
楚陌麵淡淡。
“其他男子在你們這年紀,孩子都不知有多了,你們倒好,跟比試似的,非要決出誰更稚?”
楚陌默不吭聲地喝酒。
拓跋潯看著他,嘲諷般地扯下角:“一個個的,什麽不當,非要當癡種。”
“人生自古有癡,此恨無關風與月。”他大口喝酒,瞥了神不明的楚陌一眼,懶懶道:“喜歡就告訴唄,不大點事。”
“不喜歡。”
“那你知道我說的是誰?”拓跋潯衝他翻白眼,又了眼京城方向,沒忍住又是個白眼,“竹束也是,還沒找到南九音?”
“嗯。”楚陌說道:“南九音在躲他。”
“天下之大,他怎能找到?”拓跋潯歎口氣:“他必稱帝,可一旦稱帝,便與南九音沒了可能。”
“嘖,跟話本子似的,還搞這一趴。”
兩個好友的之路相當不順,作為場高手的他很是頭疼。
Advertisement
但奈何,別人的路是地上的路,好友的路是天上之路。
登天路又怎會容易,哪怕是他也上不了天,又怎能提供幫助。
他們一邊回憶著過往,一邊大口喝酒觀月。
慢慢地,他們的稱呼變了——竹束,劉潯,楚三。
事實上,楚陌當年的化名為“楚跌”,諧音“楚爹”。
他主意打得好,想做全天下人的爹,奈何拓跋潯和景策又怎會乖乖認爹。
因著楚陌年紀最小,排行老三,於是兩人不顧他跳腳的反抗,直接扣一個“三兒”的稱呼。
氣得年楚陌幾天沒搭理他們,不得已才換了“楚三。”
楚陌一衡量,“楚三”總比“三兒”好吧。
行吧行吧,就“楚三”。
可憐,爹沒當,當了三兒。
那時楚陌才十四歲,哪鬥得贏大他好幾歲的哥哥們。
如今,一提起,回憶齊齊湧上心頭。
酒,一瓶瓶空了,他們也該從回憶中了。
楚陌抬頭看月,拓跋潯垂眸盯著酒杯,他們心照不宣的,沉默了。
下一刻,楚陌改了稱呼:“拓跋潯,你來玉南關,究竟有什麽目的。”
“沒有目的。”拓跋潯勾起懶懶的笑,神毫無破綻,“說了,來看貓兒,隻可惜沒看見。”
楚陌沉默片刻,又問:“離開玉南關後,直接回草原?”
拓跋潯:“……”
方才溫馨的回憶盡數破裂,他咬牙切齒道:“我才在東院那張床上睡了一個時辰,你就不停地趕我走??”
楚陌毫無疚之心:“我在關心你。”
“去你娘的關心。”拓跋潯罵罵咧咧幾句,還是回答了:“好不容易來次中原,準備四逛逛,給阿娘和阿驍買些東西。”
“拓跋潯!”楚陌驀然沉聲喝道。
拓跋潯懶洋洋擺手,不以為然:“知道知道,你別吼。”
Advertisement
“你老實告訴我!你究竟在想什麽?!!”楚陌怒道:“你明明知道!明明知道!!”
拓跋潯垂眸,複又盯著酒杯看,喃喃說道:“知道?我知道啊。”
“所以……”楚陌嗓音低沉慍怒:“究竟準備做什麽?”
“聞悉啊,三兒啊……”
楚陌眉心一跳。
“這麽多年,月亮還是月亮,可是……人怎麽就變了呢?”
拓跋潯又問了最初的問題,這一次,楚陌回答了:“沒有變,你沒有變,變的是他們。”
“我是不是真的錯了?”拓跋潯眼角泛紅,抬眸間水瀲灩,直直著他:“阿娘為什麽要怨恨我,阿驍為什麽要厭惡我?”
“三兒,他們是真的想讓我死,為什麽啊?”素來慵懶含笑的嗓音微,帶著深深的疑與哀傷。
“我是不是不該做草原王?我是不是應該隻做拓跋潯?可是,可是……做草原王,是為了保護他們啊……怎麽就本末倒置了?怎麽就……全變了?”
“你說我該手,我也知曉,我該手。”拓跋潯深深凝視著他,一字一頓道:“楚聞悉,你告訴我,我該怎麽對付他們?”
“抓了?囚?還是……殺了?”
“我變強大,是為了保護他們,到頭來,卻是我殺了他們,這不可笑嗎?”
拓跋潯垂下眸,掩去眼底的暗。
楚陌定定看著他,沉默不言。
拓跋潯的難做,他知道,景策也知道。
所以……即使那群人始終挑釁,他們也沒想過主撕毀和平協議。
和平協議或許隻是一張蓋著印的紙,輕輕一撕,便不再型。
可一旦撕毀,卷席其中的不止有千上萬條生命,還有……將家人放在心尖的拓跋潯。
拓跋潯這個人,恣睢肆意不可一世,可唯獨,家人被他放在心口,小心翼翼地著,生怕傷著著。
Advertisement
上一任拓拔族族長,也就是拓跋潯的父親是個相當重之人,這便意味著,拓跋潯有許多兄弟姐妹。
其中,他和拓跋驍的地位最特殊,因為他們是中原公主的孩子。
母親南悠是南詔的和親公主,他們是中原與草原人的混,比起健壯如山的草原人,他們自小便瘦弱矮小。
當然,也有其他中原姑娘被虜來,生了混孩子,但們不是公主,孩子也不是公主之子。
中原公主之子沒給他們帶來什麽好。
拓跋潯始終記得,小時候的他為保護小小年紀的拓跋驍,被一群人踩在腳下,肆意欺辱唾罵。
那一年,他也才六歲。
小小的拓跋驍會為了保護自己哥哥,孤注一擲地撲上前,咬住一人的大,打死不鬆口。
那一年,他也才四歲。
那時候,他們是最好的兄弟。
母親會渾抖,嗓音打地為他們博公道,訴委屈。
那時候,他們是最好的母子。
可是,父親拓跋虜卻自始至終都不是好父親。
拓跋虜不在乎南悠是不是公主,隻顧著和舞調笑,輕飄飄地說一句:“知道了,下去吧。”
南悠的一腔勇氣,兒子的渾傷痕,在他眼裏什麽都不是。
小拓跋潯不懂,究竟是為什麽。
他們在欺辱和威脅中長大,也在被迫懂事和聽話中活著。
沒過多久,小拓跋潯懂了。
很簡單,比起母親和兄弟二人,那群人對父親更有價值。
價值,是個很象的詞。
小拓跋潯花了些時間去理解,終於慢慢懂了。
說起來很簡單,不過是他們對父親更有用,他們更有才能。
這樣理解,便相當容易了。
小拓跋潯想,隻要他更強,更有才能,一切便不同了。
這時,一隻還未的野,在無人知曉之,開始長出獠牙。
Advertisement
一旦步關鍵時期,野的長速度便會令人驚歎。
拓跋潯便是如此。
拓跋驍發現,最近哥哥總是被父親表揚,發現其他兄弟總是會嫉恨地盯著哥哥。
他後知後覺地發現,哥哥和他不一樣了。
他的覺沒有錯,沒過多久,拓跋虜將拓跋潯送到德高重之人的住上,請他收拓跋潯為徒。
此人名為登,被譽為智者。
他看了拓跋潯一眼,沒有推,收了徒,後來的事實證明,這是他此生做的最正確的決定。
因為正是眼前這個神略顯張的小年,在未來了整個草原的王。
拓跋潯的獠牙,已經很長了。
在登那,拓跋潯學了很多。
十六歲那年,登讓他出去看看世界,見識這個天下。
拓跋潯去了,他化名劉潯,了兩個摯友。
那時一切都很好,他很喜歡中原,但他從沒想過不回草原。
草原有他的家人,他的阿娘還有弟弟阿驍。
拓跋潯知道,他有了價值,南悠和拓跋驍的生活變好了,這樣便值當了。
本以為,會一直這樣下去,可是,沒人能料到未來。
三年後,南詔國和草原五部聯手攻擊大遂。
大遂楚譯大將軍薨。
拓跋潯沒注意兩個好友失態的神,撂下句話後便匆匆趕回草原。
原因很簡單。
拓跋族沒有參與此次行,可是,南悠是南詔國公主,怎可能全而退?
不出他所料,為向大遂示好表態,拓跋虜很快將南悠關押。
拓跋虜是個眼獨到且長遠的人。
在他人以為殺了楚譯,大遂便不堪一擊之時,他卻看見了大遂至高位上的皇帝——遂安帝;怒不可遏勢要報此仇的楚家軍,以及萬眾一心一致向外的大遂百姓。
這樣的國家怎可能不堪一擊?
向大遂示好,是個很聰明的決定,但他千不該萬不該南悠。
因為,有隻野,他的獠牙已經泛起幽,隻待將人一舉撕碎片。
拓跋虜死了,死在了拓跋潯手裏。
他了草原王,將母親和弟弟捧上至高無上的地位,讓他們了所有草原人皆羨慕之人。
可是,很奇怪。
他將他們放在心尖,可是……南悠恨他,拓跋驍厭惡他。
拓跋潯全都知道,知道他們想殺他,知道他們想挑起和大遂的戰爭,知道那些辱罵他的話皆是他們推波助瀾。
但他真的不知道,自己究竟做錯了什麽。
在知曉一切的夜晚,拓跋潯喝了一天一夜的酒,第二日,借著酒醉,來到南悠住。
形高大的他撲進南悠懷裏,滿酒氣,嗓音低沉:“阿娘……你疼嗎?”
南悠顯然愣了下,疑:“疼什麽?”
“拓跋虜當年打你,外人欺你,眾人嘲你,你……還疼嗎?”
南悠沉默片刻,輕聲道:“不疼了,因為我有潯兒,有驍兒。”
潯兒啊。
拓跋潯嗓音發,暗的眸滿是:“潯兒當年不懂事,可能傷了您的心,阿娘可怪我?”
“阿娘從沒怪過潯兒。”南悠眸溫:“潯兒很乖,從沒傷過阿娘的心。”
拓跋潯驀然收懷抱,輕輕抖起來,“阿娘,阿娘,阿娘……”
阿娘,潯兒那麽乖,為什麽……您卻想要殺我?
這個問題,他不敢問出口。
他怕了。
野長之路上,他殺了無數人,也有無數人想要他的命。
可是,隻有這兩人,能讓他瞬間繳械。
他知道,他必須做點什麽,他也的確想到了辦法,所以才會告訴楚陌——待他回草原便知。
隻是,在那之前——
“我還想去趟京城。”拓跋潯突兀說道。
楚陌詫異:“作何?”
“去看看景君澤。”拓跋潯懶懶笑道。
楚陌沉默:“你個草原王悄無聲息地去大遂京城,還想見當朝太子殿下——”
“恕我直言,你是不是還沒睡醒?”
拓跋潯:“這不有段時日沒見他了嘛,屆時給他寫封書信,讓他來尋我便是。”
“罷了,隨你。”楚陌定定看著他,眼神晦暗不明:“拓跋潯,你最好別有其他念頭。”
拓跋潯白他一眼:“我能有什麽念頭?在京城殺太子?”
“你知,我說的不是此事。”
拓跋潯正要說話,卻忽的頓住,隻聽一道清脆悅耳的嗓音傳來——
“楚小陌——”
“楚小陌——”
楚陌角一。
拓跋潯發出洪亮的笑聲:“噗楚小陌哈哈哈哈……”
他笑得直顛,久久不歇,像是能笑到不朽。
楚陌臉一黑,眼底滿是危險。
拓跋潯跟沒察覺般,笑聲也從洪亮變了:“楚小陌可,鵝鵝鵝鵝鵝鵝……”
楚陌:“……”
他不搭理他,側眸盯著門口,很快,鮮活的藍影映眼簾。
方才沉重的心緒一掃而空,楚陌揚起抹笑,眸溫如水。
——小公主來了。
猜你喜歡
-
完結399 章
醫妃驚華
她是二十一世紀資深醫學專家,卻穿越成落魄陪嫁公主。嫡姐僞善做作恨不能取她性命,便宜未婚夫溫和謙厚暗藏野心,還有一大堆豺狼虎豹,一個個恨不能將她剝皮抽骨。在夾縫中生存的她開始了鬥渣男鬥朝堂鬥江山的生活,好不容易把那所謂的婚姻擺脫掉,卻又被那孱弱腹黑的妖孽太子給盯上了。從此又開始了鬥心鬥情鬥天下的漫長道路。這是一羣驚才絕豔的男女在亂世裡譜寫的一段愛情與江山的博弈。
74萬字7.92 42249 -
完結800 章

娘娘她不想再努力了
花漫漫沒想到自己會穿進一篇宮鬥爽文裡麵,成了書中的炮灰女配。她試圖逆襲,卻發現隻要自己不按照劇情行事,就會心痛如刀絞。既然如此,那她乾脆就躺平當鹹魚吧!但讓人費解的是,那位以陰狠詭譎著稱的昭王殿下,為何總愛盯著她看?……昭王發現自己的耳朵似乎出了點問題。他隻要盯著某個人,就能聽到那人的心中所想。比如說現在,花漫漫哭得梨花帶雨:“能得到王爺的寵愛,真是妾身前世修來的福氣!”然而她心裡想的卻是——“艾瑪,今天這辣椒油有點兒帶勁!哭得我停都停不住。”……(1v1甜寵,雙潔,日更)
137.5萬字8 32392 -
完結5096 章

傲世邪妃:誤惹腹黑王爺
一朝穿越,重生異界!她是帝都豪門的千金。上流的名媛圈內皆傳,她是一朵高階的交際花,對男人,皆來者不拒。她發現自己患了一種致命的癌癥,在某一夜的大廈之上,她被曾經的情敵下了毒香,與情敵一起墜樓而亡。再次睜眼,她卻發現自己變成了王妃。還穿越到了一個玄幻的大陸!修鍊、靈氣、煉藥?
449.7萬字8 159802 -
完結259 章

權臣重生后只想搞事業
赫赫有名的野心家秦鹿穿越成寡婦,膝下還多了個兒子。 公婆不慈,妯娌刁鉆,母子倆活的豬狗不如。 面對如此慘狀,桀驁如她懶得與這群無賴糾纏,帶著兒子麻利分家。 天下格局晦暗,強權欺壓不斷,對于生活在現代社會的秦鹿來說是一種煎熬。 既然不喜,那就推翻這座腐朽江山,還天下百姓一片朗朗晴空。 ** 鎮壓朝堂三十年的權臣韓鏡一朝重生,還不等他伸展拳腳,就被母親帶著脫離苦海。 自此,想要重臨朝堂的韓相,一腳跨進了母親為他挖的深淵巨坑里。 畢生夢想是封侯拜相的韓鏡,在母親魔鬼般的低語中,朝著至尊之位,連滾帶爬停不下來。 ** 君臨天下后,娘倆的飯桌上突然多了一個人。 男人長的風流恣意,顛倒眾生。 帝王憋著好奇:給我找的后爹? 【穿越娘親,重生兒子。女主和原主是前世今生。】 【男主不知道有沒有,出現的可能會很晚。】 【女主野心家,能造作,不算良善卻有底線。】 【金手指粗大,理論上是爽文。】
90.4萬字8.18 6983 -
完結30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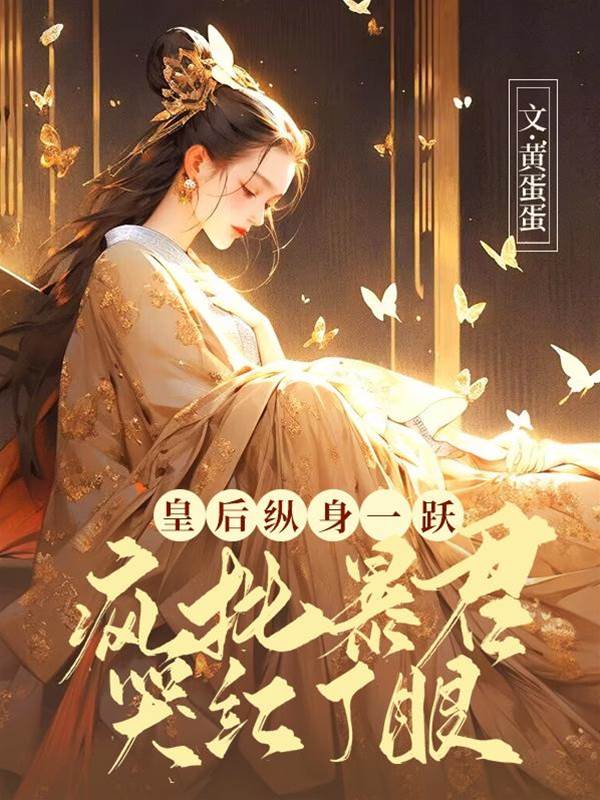
皇後縱身一躍,瘋批暴君哭紅了眼
【1v1,雙潔 宮鬥 爽文 追妻火葬場,女主人間清醒,所有人的白月光】孟棠是個溫婉大方的皇後,不爭不搶,一朵屹立在後宮的真白蓮,所有人都這麼覺得,暴君也這麼覺得。他納妃,她笑著恭喜並安排新妃侍寢。他送來補藥,她明知是避子藥卻乖順服下。他舊疾發作頭痛難忍,她用自己心頭血為引為他止痛。他問她:“你怎麼這麼好。”她麵上溫婉:“能為陛下分憂是臣妾榮幸。”直到叛軍攻城,她在城樓縱身一躍,以身殉城,平定叛亂。*刷滿暴君好感,孟棠死遁成功,功成身退。暴君抱著她的屍體,跪在地上哭紅了眼:“梓童,我錯了,你回來好不好?”孟棠看見這一幕,內心毫無波動,“虐嗎?我演的,真當世界上有那種無私奉獻不求回報的真白蓮啊。”
53.4萬字8.18 41760 -
完結267 章

盛京第一寵
大哥丰神俊朗,內心很毒很暴力;二哥風流紈絝,人稱盛京第一公子; 繼母雌雄莫辯,神出鬼沒;爹爹戰功赫赫,英勇威武; 身爲資深團寵,沈卿卿本該嬌寵一世。可一朝變故,沈家男兒無一倖存,她被心愛的表哥囚禁在深宮,生不如死。 沈卿卿臨死的那晚,宮裏漫天火光,叛軍逼城。她閉眼的最後關頭,看見了她的繼母……不!是變成了男子的繼母! 他手握滴着血的長劍,動作亦如往常的溫柔,熾熱的氣息在耳邊,“卿卿不怕。” 她的魂魄飄在皇宮上方,親眼看見“繼母”給她報仇,還當了皇帝。 一睜眼,沈卿卿回到了十三歲這年,繼母把她圈在臂彎,給她看話本子:“我們卿卿看懂了麼?” 沈卿卿:“……”
40.1萬字8 13661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