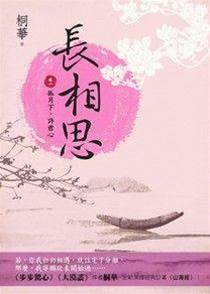《穿越后我在四爺后院當團寵》 第五十五章 兄妹相見
“你們兄妹二人確實許久未見,你去送送年將軍吧!”四爺心里有一沖不想讓去,可在看著年清婉明顯帶著些許祈求的目后,又不得不下心腸。
他也不知自己怎麼看不得傷心難過,似是有些自暴自棄的單手拄著頭,沖著二人擺了擺手。
“妹妹!方才你為什麼要一而再的阻撓我說話?”才出了院子,年羹堯就有些忍不住出口質問。
“哥哥什麼時候才能不這麼沖行事。
我在府里只是個侍妾格格罷了,份低微,平日里免不得還要小心行事。
如今若是任由哥哥胡來,豈不是越發把妹妹我推到了風口浪尖上?”年清婉停下腳步,看著這個滿眼都是擔憂自己的兄長。
心里微微嘆了一口氣,也不知道憑著自己能不能勸住他的脾氣幾分。
“妹妹當初在府里活的多自在,憑什麼在這四貝勒府里就委屈。
明個兒,我就去求了皇上,把妹妹接回府里將養子去,任憑們那些個勞什子的侍妾有什麼能耐,妹妹也都不用怕了。”
聽著年羹堯越發胡說的話,年清婉心里生出一口悶氣,平日里在府里就已經夠小心翼翼,如履薄冰的了。
現下,年羹堯不僅不知道幫襯自己,反而還過來添,幫倒忙。
連帶著這些時日心里的委屈幾乎要一腦兒的都發出來,最終年清婉閉了閉眼睛,下心底里的那子怨氣,緩著口氣說著:“哥哥!”
見著年羹堯蹙著眉頭后,才繼續說著:“哥哥什麼時候才能顧全大局,不這麼沖行事。
我知道哥哥和父親現下得皇上得青睞和重用,可哥哥想過沒有,若是哥哥總是這樣魯莽行事,被那些個言一本本奏折參上去后,會是什麼后果?”
Advertisement
“那些個老兒敢!”
聽著這話,年清婉知道他這是半點沒有把自己方才的話聽進去,不由得嘆息了一聲,繼續耐心的勸著:“縱使現下皇上不會對哥哥和年府怎麼樣,可誰能保證的了日后會如何,伴君如伴虎。
若是哥哥的脾氣始終不改,終有一日會替年府惹來滅頂之災。”
“我現下是大將軍,皇上還要依仗我去平定戰,那些個言不過是只會在奏折上快快罷了,皇上如何會信了他們的話。”
“哥哥別忘了,功高蓋主。
哥哥和父親越是得用于皇上,就越是要小心謹慎行事,萬萬不能讓人尋著錯,哥哥要謹記臥榻之旁豈容他人鼾睡。”
“妹妹……你怎的如此小心?”年羹堯只覺著都快要不認識自己這個從小一起長大的妹妹了。
“并非是我小心,只是我們年氏一族若想要長久興盛下去,唯有事事小心事事謹慎,才能保全。”年清婉低了聲音說著,見著年羹堯面上一副疑的神看著自己,一顆心瞬間了,又裝作不經意的解釋著:“這也是妹妹在了四貝勒后才看清楚的事罷了。
就比如高氏,不管以前依仗著自己家室亦或者依仗著四爺對的寵,囂張跋扈肆意妄為,現如今生生的把四爺對著的寵磨沒了,又哪里能落得什麼好下場呢?”
從前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側福晉之位,現下也不過是個末等的侍妾格格罷了,一朝從高跌落,從前那些個人必定會想著法子的作踐。
半晌,年羹堯這才略微點了點頭應著道:“今日的事我知曉了,妹妹不必擔憂。”
Advertisement
年清婉盯著他看了好一會兒,覺著他是真把自己的話聽進心里去了,這才松了一口氣,含笑的點了點頭:“哥哥府里還有事,妹妹就不送哥哥了。”
今日年羹堯大搖大擺的府,本就不合乎規矩,現下年清婉能盡早的讓他離開,也能省卻自己一些麻煩。
在逐漸看不見年羹堯的背影后,年清婉這才轉折回了前院。
四爺聽著靜后,有些手忙腳的把書重新拿在手里,只是上面的一個字都沒看進去,反而豎著耳朵仔細聽著門口的靜,半晌才聽見房門‘吱嘎’一聲,被人從外面推開,面上裝的有模有樣,甚至還翻了一頁書。
“奴才見過四爺。”
年清婉走進來,虛虛行了一禮,也不等四爺開口,就自己起走到四爺旁,探了大半個子過去,著腦袋朝著他手上拿著的書看過去,見著書都拿倒了,有些憋不住笑出聲,帶了幾分嘲弄說著:“四爺這是在練什麼功夫呢?不如也傳授奴才一二?”
四爺這才發現自己沒注意把書拿倒了,面上有些掛不住,唬著臉看著呵斥:“你膽子倒是越發大了,越來越不把爺放在眼里了。”
“爺說這話,可就著實冤枉奴才了。
爺是奴才的夫君,更是奴才的天,奴才如何敢不把爺放在眼里?”年清婉知道他沒有生氣,只是剛才被自己揭穿,面上有些掛不住,一時想往回找補找補,也樂的哄著他。
好聽的話止不住的冒出來,不一會兒就哄得四爺眉頭舒展,臉上重新掛上了笑容。
瞧著時候差不多,年清婉才開口提著今日的事:“奴才今日多謝四爺恩典,肯讓奴才與哥哥相見。”
Advertisement
“爺瞧著你們兩兄妹子倒是不盡相同。”四爺也來了興致,加之剛才的不順心也都被年清婉捋順了,眼下倒是沒什麼可別扭的,直接攬著進了自己的懷里。
手攬在腰間,著比之前瘦了些許,角的笑意往下落了幾分:“怎麼又瘦了,定是你沒聽太醫的話,好好補子。”
年清婉也跟著垂頭了腰間的,倒是沒覺著自己瘦了,輕哼了一聲說著:“奴才在胖下去,豈不是都要豬了。”
“胖一些手更好。”
“四爺越發孟浪了。”年清婉饒是臉皮厚,也被他這番話說的臉頰發紅,瞪著他時,眼波流轉別有一番風味。
四爺念著還沒養好子不能伺候,只能干看著不能吃,心里更加了。
朝著紅潤的湊了過去,離開時年清婉一雙眼眸更加含了水一般人,恨不得立即和大戰三百回合。
年清婉到自己坐著的地方生出的變化,子有些僵。
看著四爺尷尬的笑了笑,尋了個理由就跑了出去,徒就四爺一人在屋子里冷靜。
回到錦繡閣,年清婉把寫好的信吹干仔細疊好才遞給秋憐,仍不放心的叮囑著:“尋著機會,親自把信送到我母親手里。”
今日年羹堯能夠不管不顧的闖進四貝勒府,就已經說明他的子比年清婉想的還要莽撞沒腦子,今日雖說看著是勸通了,可誰知睡一晚明個兒起來還會不會出什麼幺蛾子。
也只能把希寄托在年夫人上,到底是們兄妹幾人的生母,說出來的話還是比這個妹妹有威信許多。
Advertisement
而年夫人又不是個拎不清的人,相比較于年羹堯,還是年夫人更好說一些。
汪嬙見著年清婉著自己太,面有些發白,蹙了蹙眉頭上前說著:“格格可是頭疼了?小月子雖說不如生產完那般傷人元氣,可若是不好好養著,日后子還是會落下病的。”
何嘗不知道這事,只是最近的事都跟著上趕著往前湊一般,哪能就真的不費心神,只安安穩穩的養著子。
“不礙事的,左右已經養了幾日功夫,我也沒察覺出子有什麼不舒坦的地方。”年清婉笑了笑,似是在說給聽,又像是在說給自己聽。
猜你喜歡
-
完結2877 章

傾世醫妃太難撩
一朝穿越,蘇念薇被人指著鼻子罵懷了個野種。 死裡逃生之後她活著的目的:報仇、養娃兒,尋找渣男。 一不小心卻愛上了害她婚前失貞的男人。 這仇,是報啊還是報啊? 她逃跑之後,狠厲陰冷的男人帶著孩子找上門來。 當年,他們都是被設計了。 兩個睚眦必報的人一拍即合,攜手展開了絕地反擊。 女人:我是來報仇的! 厲王:這不妨礙談情說愛。
251.8萬字8 60173 -
完結5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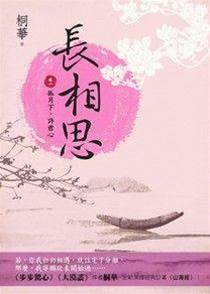
長相思
生命是一場又一場的相遇和別離,是一次又一次的遺忘和開始,可總有些事,一旦發生,就留下印跡;總有個人,一旦來過,就無法忘記。這一場清水鎮的相遇改變了所有人的命運,
63.4萬字8 5809 -
完結396 章

公府嬌奴
宋錦茵在世子裴晏舟身側八年,於十五歲成了他的暖床丫鬟,如今也不過二八年華。這八年裏,她從官家女淪為奴籍,磨滅了傲骨,背上了罪責,也徹底消了她與裴晏舟的親近。可裴晏舟恨她,卻始終不願放她。後來,她在故人的相助下逃離了國公府。而那位矜貴冷傲的世子爺卻像是徹底瘋了一樣,撇下聖旨,尋遍了整個京都城。起初他看不清內心,隻任由恨意滋長,誓要拉著宋錦茵一起沉淪。後來他終於尋到了宋錦茵,可那一日,他差一點死在了那雙淡漠的眼中。
83.2萬字8.18 47187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