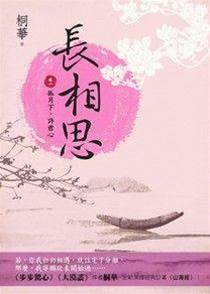《公府貴媳》 第116章 給媳婦兒化妝
晏長風覺自己是一頭撞進了裴二的視線里。他的眼神專注,溫,還有一種掙不開的執拗。鋪天蓋地的,讓人逃不開。
只是一不留神,就被他的視線層層圍住,像只纏進蛛網的小蟲,不不由己地困在其中。
驚慌著掙扎出來,還沒鬧清楚這種覺是什麼,心里先生出一陣后怕。不喜歡這樣被的事,的本能提醒這很危險,想,不能繼續這樣了。
“裴二,你……”
“夫人是想問我關于祖母的事麼?”裴修打了個哈欠,眼睛里漾出了一點水汽,他用含著水汽的眼神看著,全無方才的專注,只有疲倦,“你且等我沐浴回來同你說。”
說完就起離開了房間。
晏長風:“……哦。”
是想問裴家老夫人,但現在……
算了,明日再說吧。
有些事過了那個時機,再說就張不開了,第二日到底也沒找到機會說。
裴家老夫人是用過早飯后到的,彼時晏長風正在廚房整頓。廚房沒了管事,大家又昨日事的影響,猶如一盤散沙。
晏長風先做主給每人發了二兩銀子以辛勞,然后親力親為地領著大家做事,很快就調起了大家的勞作熱。
做了半天活,一臟污,恰好老夫人到了門口,沒時間回房去換,就這樣跟老太太見了面。
裴家老夫人意外地很慈善,眉眼與宋國公很像,但臉上的紋路卻是照著彌勒佛長的,母子倆站在前一起,乍一看不像親生的。
“一年不見,母親的子骨瞧著越發朗了。”裴延慶親自攙扶著老夫人進門。
趙氏跟在后面陪著笑,“到底是南邊養人,氣瞧著也好。”
“你們啊哄我。”老夫人許氏笑呵呵道,“我這一路舟車勞頓,水路耽擱了好幾天,不然也不至于今日才來,坐在船上啊整日腰酸背痛的,也沒心思吃飯,能朗到哪去?”
Advertisement
“母親南北兩頭跑,著實辛苦了。”裴延慶道,“往后不然就留在北都,兒子實在不忍心讓您這樣的罪。”
許氏不說是也不說不是,依舊是笑呵呵的,“其實啊我是喜歡瞧路上的景,不舒服但心好——誒,我那兩個孫媳婦兒呢?”
“就跟在您后面呢。”趙氏讓兩個媳婦兒上前給老太太瞧瞧,“這個雅靜些的是老大媳婦兒,惠容,那個高一些的是老二媳婦兒,長風。”
秦惠容立刻福見禮,“惠容見過祖母。”
晏長風則微微頷首,“長風見過祖母。”
“長得都怪好看的!”許氏上了歲數,就瞧漂漂亮亮的小姑娘,盯著兩個孫媳婦兒打量了半天。
秦惠容今日穿得鮮亮,臉頰都比往日深了些,頗得許氏的青睞。許氏握著的手問了兩句,然后當眾賞了一副鐲子。
再看晏長風,素面朝天,一的臟污,比府里丫頭還像丫頭。老夫人素來面,見不得媳婦兒這樣,“哎呦,老二媳婦兒這是去哪蹭了一的臟污,泥猴似的。”
早上裴修跟晏長風介紹老夫人,說干凈,喜歡老實安分的人,還特意囑咐得鮮亮些。
但晏長風一早要去廚房,就隨意穿了一兒,臉上沒涂沒抹胭脂,完地避開了老太太喜歡的樣子。
不過沒有刻意討好的意思,就沒所謂,正要回答,裴修握住的手代答:“讓祖母見笑了,在廚房蹭的。”
許氏見小兩口好,也就不怎麼計較孫媳婦兒不面了,“怎麼還跑廚房去了?”
這話說起來就長了,又要牽扯到牛嬤嬤,裴延慶便接了話頭,長話短說:“老二媳婦兒最近幫著母親管家,這兩日壽宴都是持的,委實辛苦。”
Advertisement
“原來是這樣。”許氏笑著打發晏長風,“那必定是因為我來了沒功夫換,快回去換兒干凈的去。”
裴修依舊拉著的手,“那孫兒跟媳婦兒就先行告退了。”
許氏笑道:“去吧。”
晏長風回房換了裳,坐在鏡前上妝,一邊問道喝茶的裴二:“老夫人好像喜歡你的?”
裴修笑,“你怎麼看出來的?”
“看眼唄。”晏長風用油面塌往臉上撲,十分不得法,撲得一塊厚一塊薄的,“老太太跟夫人關系明顯不太好,想必也不會太喜歡裴鈺,全程沒跟你說話,可眼睛往你臉上瞥了好幾眼,大約是關心你的,人前抬舉秦惠容,是給大房面子,也是變相保護你,至于對我麼,估計是真沒看上,喜歡我大姐,這我是知道的。”
二姑娘這眼力真是沒話說。
裴家老太太之所以搬去南邊跟沒爵位的二老爺三老爺住,就是不喜歡趙氏。趙氏不是個安分的,沒分家的時候打兩個妯娌,要不是背后攛掇宋國公,這家也不能這麼早分。
剛分家那會兒老太太在府里住了幾年,眼見著趙氏鬧得家里烏煙瘴氣,家里孩子一個接一個的夭折,預再住下去遲早氣死,就以養為名搬去了南邊,每年也就兒子過壽的時候回來住一陣子。
老太太也不喜歡被趙氏慣出來的長孫,裴鈺傲慢好欺負弟妹,霸王似的,看著鬧心。原本也不喜歡裴修,因為他娘白氏出青樓,青樓里出來的人能安分到哪去,妖似的,只會勾引男人。
但后來瞧著裴修這孩子老實安分,子又不好,怪人心疼的,私下里就多疼他一些。
裴修走到鏡前,拿走二姑娘手里的油面塌,拍掉上面的厚,幫修容,“老太太不是糊涂人,相久了會喜歡你的。”
Advertisement
晏長風被油面塌定住,僵地抬著臉,“喂,你別瞎撲啊,你會上妝嗎?”
“不好說,反正是第一次。”裴修手指輕輕著的下,像捧著一個瓷,輕地勻著臉上的。
晏長風無語,“那你這不是添嗎,還不如我自己來呢!”
抬手去搶油面塌,下上的力道驟然加重,愣了一下,抬眼瞪著裴二,心說這人是要造反怎麼著?
“別。”裴修松了些力,以舒服的力度錮著的下,“夫人最好別開口,我第一次撲,手上沒準兒,撲到里可就不好了。”
晏長風:“……”
裴二公子第一次撲,也不知道會不會,搗鼓了半天,晏長風差點兒睡著了。
不知道過了多久,裴二松開了,“差不多了。”
晏長風迫不及待往鏡子里看,一下子就愣住了。
鏡中的臉十分致,撲得很自然,薄薄一層,比起時下的妝容,算是淡妝,但意外的很好看。是哪里好看呢?仔細端詳自己的臉,好像胭脂口脂涂得重,很提氣,又不突兀,眉畫的神大氣,跟的氣質很相配。
“可以啊裴二。”對裴二瞬間刮目相看,“你真的是第一次畫?”
“夫人想讓我是第幾次?”裴修不會上妝,無非是依著心里的想象給畫,大概是他心里的二姑娘好看,所以畫出來的就好看。
“你是不是跟醉紅塵的姑娘混久了,所以無師自通?”晏長風不信他是第一次,一個男人第一次怎麼會畫得這樣好?
裴修笑起來,“你說是就是吧。”
什麼說是就是?
晏長風看他笑得開心,八就是真的。心里莫名有些堵得慌,頓時又覺得自己的臉不好看了。
Advertisement
兩人磨蹭了好一會兒才去到北定院,一進門就聽見老太太在發火。
“這些不省心的奴才!居然敢這樣污蔑主子!”
晏長風一聽就知道牛嬤嬤的事老太太知道了。
方才不在,趕巧廚房的人過來請示幾點上菜,被許氏聽見了,就多問了一句。
許氏對二孫媳婦兒是有些不滿,覺得晏家這二姑娘不是個省油的燈。先前聽聞原本要嫁到裴家的晏家大姑娘換了二姑娘,先為主地認為是這個二姑娘搶了大姑娘的好婚事。
大概是在后宅見識過太多爾虞我詐,姊妹相殘,心了,本能地就會往壞想。再加上晏長風居然越過老大媳婦兒管家,于是就更加誤解。
怕二孫子這媳婦兒野心太大,坑了孫子,所以就打算尋個錯,不讓再管家。豈料一問本不是那麼回事。
二之所以弄得那麼狼狽,是因為廚房沒了管事,親自接管,凡事親力親為,還跟下人一起干雜活。
廚房為什麼沒管事,因為牛嬤嬤犯了事。再往下一問,許氏好懸沒氣死。
裴延慶跟趙氏不敢說裴鈺指使,只說是牛嬤嬤與趙權對二不滿,所以挾怨報復。許氏一聽這還得了?這要不是有個厲害的媳婦兒幫襯著,二孫子早這些個惡仆趕出家門了。
當即了牛嬤嬤來,準備親自過問這件事。
此時牛嬤嬤在屋里跪著,被許氏罵得抬不起頭來。昨天被賬房的口供判了死罪,自知這次沒了翻的可能,所以也不打算反抗了,任憑許氏罵。
可被罵著罵著覺得哪里不對,聽許氏的意思,好像不知道這件事是世子跟世子夫人控的。
這牛嬤嬤不能答應,憑什麼讓一個人頂罪?這麼大的罪名扣下來,兒孫都沒了活路!
忽的,福至心靈,想到了一個好主意,大聲辯駁:“老夫人!這事不是我的主意,是世子夫人的主意!”
許氏一愣,“什麼?”
牛嬤嬤簡直佩服自己,知道公爺跟夫人想保護世子的名譽,但世子夫人就無所謂了。只說是世子夫人指使,既不得罪國公爺跟夫人,也能減輕自己上的罪過。老夫人是個慈善人,知道是被指使的,說不定大發慈悲就饒了。
“回老夫人,是世子夫人指使我污蔑二公子的,不然我縱有一百個膽子也不敢啊!老夫人,您大發慈悲,給我一次改正的機會吧,我后半輩子一定為國公府當牛做馬,任勞任怨啊老夫人!”
“這是怎麼一回事!”許氏看向兒子與兒媳,從他們躲閃的目里,似乎窺到了真相。
秦惠容走到牛嬤嬤邊,撲通跪下,“祖母,此事都怨我,怨我耳子。母親前些日子生病,不能管家,本應該是我替母親分擔,無奈我不懂這些,只能勞累弟妹幫忙。后來呢,府里莫名出現了一些怨言,大家錯信我,請我出面主持公道,我只聽了些片面之詞就武斷地認為是二弟妹不夠寬和,但我自知沒出什麼力,就婉拒了。”
“后來牛嬤嬤私下來找我聊天,說起當年二姨娘的一些事,我就多提點了一句,問二弟是早產還是足月產,誰知牛嬤嬤就誤會了去,認為我是在質疑二弟的出,于是自作主張說要在壽宴上揭穿二弟的丑事,那樣母親就不可能再讓弟妹管家。我當時也是有些鬼迷心竅,就答應了,還幫著出了一些主意,祖母,您罰我吧,我對不住二弟跟弟妹,我認罰,無論怎麼懲罰我都沒有怨言。“
許氏看向牛嬤嬤,”是這樣嗎?“
牛嬤嬤轉了轉眼珠子,覺得世子夫人這話有些推卸責任,否認:”世子夫人何不說實話呢,我哪有那樣的頭腦想這些主意,明明是您幫忙想出來的主意,夫人若是不信,大可以問道賬房,他什麼都知道!“
許氏都糊涂了,問秦惠容,”老大媳婦,你跟我說實話,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再不說實話,可別怪我不顧分了?”
秦惠容跪地磕頭,“祖母,我沒什麼可辯解的,您罰我吧,我認罰!”
許氏見不說實話,沉聲道:“去把賬房來!”
猜你喜歡
-
完結2877 章

傾世醫妃太難撩
一朝穿越,蘇念薇被人指著鼻子罵懷了個野種。 死裡逃生之後她活著的目的:報仇、養娃兒,尋找渣男。 一不小心卻愛上了害她婚前失貞的男人。 這仇,是報啊還是報啊? 她逃跑之後,狠厲陰冷的男人帶著孩子找上門來。 當年,他們都是被設計了。 兩個睚眦必報的人一拍即合,攜手展開了絕地反擊。 女人:我是來報仇的! 厲王:這不妨礙談情說愛。
251.8萬字8 60165 -
完結5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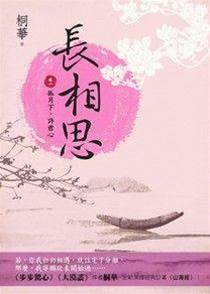
長相思
生命是一場又一場的相遇和別離,是一次又一次的遺忘和開始,可總有些事,一旦發生,就留下印跡;總有個人,一旦來過,就無法忘記。這一場清水鎮的相遇改變了所有人的命運,
63.4萬字8 5805 -
完結396 章

公府嬌奴
宋錦茵在世子裴晏舟身側八年,於十五歲成了他的暖床丫鬟,如今也不過二八年華。這八年裏,她從官家女淪為奴籍,磨滅了傲骨,背上了罪責,也徹底消了她與裴晏舟的親近。可裴晏舟恨她,卻始終不願放她。後來,她在故人的相助下逃離了國公府。而那位矜貴冷傲的世子爺卻像是徹底瘋了一樣,撇下聖旨,尋遍了整個京都城。起初他看不清內心,隻任由恨意滋長,誓要拉著宋錦茵一起沉淪。後來他終於尋到了宋錦茵,可那一日,他差一點死在了那雙淡漠的眼中。
83.2萬字8.18 46905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