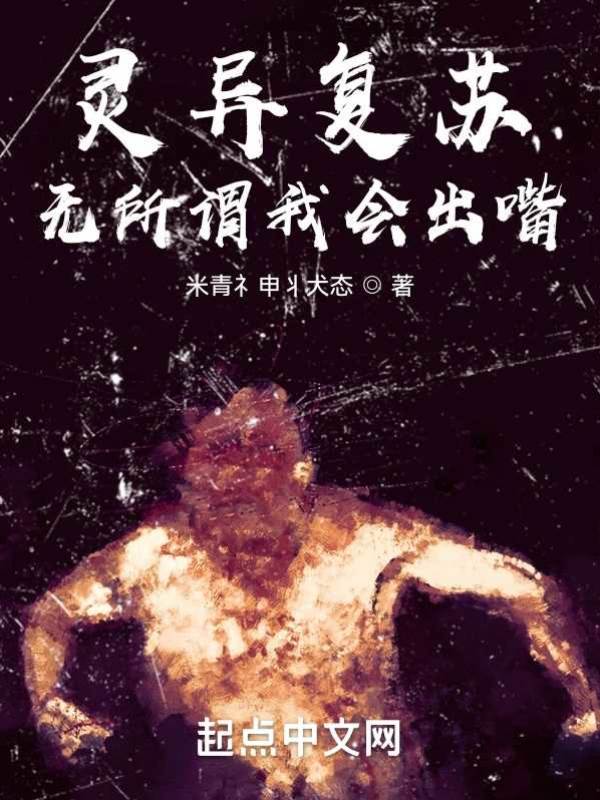《心毒》 第109章
第109章 圍剿(10)
出人意料,留存在李立文戶外刀上的大面積已清洗跡,經過提取與檢驗,確認屬於一位名肖剛的33歲男子。
而該男子已經失蹤半年。
花崇不得不召集人手急開會。
“是我們區的失蹤案唷。”曹瀚手裏拿著一個記事本,卻沒有翻開,“肖剛是一家手機APP領域創業公司的合夥人嘛。今年4月,他的妻子和父母到派出所報警,說他的手機一直關機哩,也沒有去公司上班哩,怎麼都聯繫不上,懷疑失蹤唷。”
“肖剛失蹤之前最後一次出現是在哪里?”花崇問。
“他的公司哩。”曹瀚幾乎記得過目案件的所有細節,“4月3號下午,他正常下班嘛,當天晚上就沒有回家唷。但他妻子以為他在公司加班——他那種創業公司嘛,通宵加班是常態唷,於是他妻子也沒有在意唷。直到第三天早上發現他又徹夜未歸,才給他打電話嘛,當時手機已經是關機狀態哩。派出所是當天晚上接警哩,不過因為沒有任何傷害跡象,也沒有財產丟失,屬於無故失蹤嘛,所以沒有立即立案唷。”
花崇皺著眉,“後來呢?”
“後來當然立案了唷,但一直沒有查到有價值的線索嘛。”曹瀚說:“這類失蹤案,沒有第一現場嘛,失蹤者又是無故離開嘛,實在難以著手唷。不過關於肖剛這個人哩,我們隊員經過集走訪,還是瞭解到一些他的事唷。”
肖剛與妻子龔小帆結婚七年,看上去和睦,卻一直沒有生養孩子。龔小帆最初不願意跟員警底,後來才說,自己當初與肖剛結婚,其實是被騙了婚。肖剛是個雙,但比之人,更鍾于男人。結婚之前,龔小帆並不知道,婚後半年,才漸漸察覺出異常。不過,在發現肖剛與不男人保持著“炮友”後,龔小帆並沒有激憤慨地提出離婚,而是心平氣和地與肖剛談了一回。從此,兩人了“表面夫妻”,肖剛繼續在外面飄彩旗,龔小帆花著他的錢自己的生活,如此竟然也共同度過了七年“相敬如賓”的生活。
Advertisement
這也是肖剛第一天沒回家時,龔小帆沒有立即打電話詢問的原因——他們的早就破裂了,繼續生活在一起,無非是為了避開來自社會和各自家人的閒言碎語。
據龔小帆和肖剛一些朋友說,肖剛有去酒吧找樂子的習慣,但因為公司還在發展階段,實在是太忙了,所以這一兩年去酒吧的次數很。立案之後,警員去肖剛曾去的酒吧、夜店走訪過,該調的監控也調了,只有寥寥幾人對他有印象,但都說他是個很安靜的客人,一個人坐在吧臺上喝酒,沒什麼存在。
而僅有的幾段視頻裏,也沒有任何形跡可疑的人靠近肖剛。
他的失蹤,看上去就像一場主離開的惡作劇。
但現在,對命案極其敏的重案刑警們明白,他很有可能已經被害了。李立文的那把沾的刀,也許就是兇。
??
聽到“肖剛”三個字時,李立文怔了片刻,然後像突然驚醒一般,雙目幾乎瞪到最大。
可花崇從他眼中看到的,卻是不應有的恐懼與害怕。
那種恐懼與作案之後擔心被抓捕的恐懼不同,後者藏著顯而易見的暴戾,而李立文流出來的恐懼卻帶著幾分懦弱與無助。
柳至秦點出肖剛的照片,“你認識他,對嗎?”
李立文近乎本能地搖頭。
“今年3月25號,他去過你工作的酒吧。”柳至秦說:“那天你沒有休,從晚上8點一直工作到淩晨4點。你見過他吧?”
“沒有!”李立文聲音抖,“我沒有見過他!我不認識他!店,店裏每天都有很多客人,3月份接待的客人,我,我怎麼可能還記得?”
柳至秦卻像沒有聽到他的解釋一般,又問:“接下去的幾天,肖剛找過你——但不是在酒吧。你記不記得,他在什麼地方攔住你,對你說了什麼話?”
Advertisement
李立文臉越來越難看,右手用力撐住額頭,“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麼!我都說了我不認識他!他,他……不是什麼好人。你們要調查他,就去找其他人!”
“既然不認識他,為什麼說他不是好人?”花崇半瞇著眼,“昨天我們在你住的地方找到七把刀,其中一把對魯米諾測試有反應。我當時就問過你,是不是覺得用水把刀上的跡清洗掉就萬事大吉了。你既不肯承認最近使用過它,也不肯承認它沾過。但現在,我們已經在刀上提取到一個人的DNA,你猜這人是誰?”
李立文的瞳孔驟然,“肖,肖剛?”
“原來不是認不得嘛。”花崇單手搭在桌沿,視線停在李立文臉上,“他半年前失蹤了,你知道嗎?”
李立文已是滿臉的汗,惶恐地點頭,“派出所的人來調查過,但,但是沒有問過我。”
“你刀上的跡並非新鮮跡。”花崇說:“你對他做了什麼?他現在在哪里?”
“我不知道!”李立文有個抱住雙臂的作,但很快放開,“我只是自衛,我沒有傷害他!他失蹤不關我的事!”
“自衛?”
“他強迫我!”李立文想是回憶起了什麼痛苦的往事,肩背不停抖。
“慢慢說。”柳至秦聲音輕輕的,“你把事待清楚,我們才好去調查。”
李立文用力吞咽口水,瞪大的雙眼死死盯著桌面,“他,肖剛只來過我們店一回。給他送酒的不是我,我本沒有靠近過他,天知道他怎麼就盯上我了!那天我下班之後,他在店後面住我,讓,讓我陪他。”
酒吧街的夜店個個裝修得別一格,正面彩照人,背面卻很不講究,堆著垃圾,淌著髒水,真實詮釋著什麼“明背後的黑暗”。
Advertisement
花崇不久前才從那裏經過,想像得出肖剛住李立文時的形。
“我在這一行也幹了好幾年了,像他這樣的客人不是沒有見過,我知道他是什麼意思。”李立文吸了吸鼻子,“他就是想跟我睡。但我又不是gay,為了錢也不能答應他啊。兩個男的做那種事,太噁心了!”
柳至秦輕咳了一聲,花崇倒是無所謂,接著問:“後來你和他起了衝突?”
“他是客人,我怎麼敢和他起衝突?”李立文猛地抬起眼,接到花崇的目後立即又撇開,“後來幾天,他經常來纏著我,還,還威脅我。”
“威脅你什麼?”
“還能有什麼?他們這些人,不就是看我們這些當服務生的好欺負嗎?他要是去店裏找我的麻煩,我馬上就會丟工作。事如果鬧大,我在別的店也找不到工作。”李立文又急又氣,“我被他纏得不了,答應用,用手和,和給他做一回。”
“就是他失蹤的那天嗎?”花崇問。
李立文深吸一口氣,“是。但我不知道他後來失蹤了,我只是,只是割了他一刀!”
“在哪里?”
“富康區一個招待所。”
“富康區?肖剛帶你去招待所?”
“他說那種地方比較安全。”李立文捂住大半張臉,“酒店什麼的,監控太多,份證也查得嚴。”
花崇小幅度地抬起下,“既然已經說好了,你為什麼還會割他一刀?你特意帶著刀?”
“不是特意!我有在包裏放刀的習慣!我沒有故意捅他!”
“‘捅’和‘割’是兩個完全不同的作。”花崇手指疊,“到底是‘捅’,還是‘割’?捅的哪里?割的哪里?”
柳至秦在桌上丟了一包紙巾,“汗。”
Advertisement
李立文連忙扯出幾張,“是說好了,但肖剛中途反悔!我已經給他那個了,還不止一次。他不滿意,強迫我跟他做。我不了他們那些gay的玩兒法,跟他吵起來,他還扇了我幾耳,罵我這樣的人就是天生命賤,長著舌頭就該男人的,長了個屁眼就該翹著讓人!他比我高,也比我強壯,要拼力氣的話,我本打不過他。”
“但你有刀。”花崇說。
李立文半天沒說話,接著竟然泣起來,浸滿汗水的紙巾被捂在眼睛上,審訊室響起低沉又抑的哭聲。
柳至秦偏頭看向花崇,花崇卻仍舊面不改,“後來發生了什麼?”
“我捅……”李立文一邊吸氣一邊說:“我割破了他的手臂,刀上的就是那時候沾上的。不過那時候我們在衛生間,我很害怕,他跑掉之後,我就將地上牆上的清洗乾淨了,把刀也洗乾淨了。”
花崇不大相信,“肖剛在被你割破手臂之後‘跑掉’了?”
李立文用力點頭,“後面的事我就真的不知道了。我沒有割到他的脈,他不可能因為那一刀死掉!”
“你割他的時候,不擔心他到酒吧找你麻煩?”
“我哪兒還想得到那麼多啊?咬了他那個,我已經噁心得不了了,他還想上我,我只能和他拼命!”
花崇歎了口氣,“他‘跑掉’之後,再也沒有來找過你?”
“沒有了。但我一直很害怕,擔心他突然出現。不過過了一段時間,派出所的人來我們店裏,我才知道他失蹤了。”
“那你有什麼想法?”柳至秦問。
又是一陣沉默,李立文低著頭緩慢道:“我希他再也不要出現,死,死了最好。”
??
離開審訊室,花崇沉著一張臉,快步走到走廊盡頭,有些暴地把門推開。
這幾日降溫降得厲害,哪間警室裏都開著空調,又悶又熱,連著開會、審人,幾小時下來簡直頭昏腦漲,太痛得比剛出車禍那天晚上還嚴重。
柳至秦跟著來到臺上,順手關上門,吹一陣涼風,半煙,腦子果然清晰了一些。
“李立文也許沒有撒謊,但他肯定還瞞了一些事。”花崇穿了件戴兜帽的外套,雙手抄在袋裏,不停在欄桿邊踱步,“他給我的覺很奇怪。肖剛的失蹤肯定和他有關。”
“一個手臂被割傷的男人,半夜離開招待所,會去哪里?”柳至秦走到花崇邊,抬起右手,拉住了花崇的兜帽。
頭被厚實的兜帽罩住時,花崇愣了一下,思緒突然一斷,直勾勾地看著柳至秦。
“別這麼看我。”柳至秦為他整理了一下兜帽,順勢在頂上拍了兩下,“我會走神,注意力都在你上,無法專注案子。”
花崇略一低頭,兜帽沿幾乎遮住眼睛,半秒後出手,想把兜帽扯下去。
“這兒風大。”柳至秦目,阻止道:“你才過傷,吹久了不好。”
花崇籲了口氣,語氣帶著幾分無可奈何,“那你也別這麼看我。”
“嗯?”
“我也會走神。”
柳至秦眼中的一定,角幾乎瞬間揚了起來。
花崇當然注意到了,卻收斂心思,話歸正題,“重案組理不了這麼多案子,既然刀上的不屬於尹子喬,那李立文和割案的關係就有限。一會兒跟曹瀚說一聲,讓他分點人手繼續查肖剛失蹤案,我們這邊盯割案。”
??
大麻屬於毒品,而涉及毒品的案子由緝毒支隊負責。安區酒吧街涉毒的消息,花崇已經第一時間報告給陳爭,陳爭又與緝毒支隊隊長急通。緝毒支隊迅速出擊,以最快速度控制了十幾名重要販毒分子。
不過這算不上大規模的緝毒行,查繳的毒品僅有數量不多的大麻、搖頭丸,沒有高純度冰毒、海因之類極難戒斷的毒品。
猜你喜歡
-
完結911 章

鄉野詭事
在民間有一種說法,養“仙家”的人,仙家無論幫他賺多少錢,給了他多少好處,臨死前,仙家全都會收回去。聽村里的老人說,步規并非親生,而是七奶奶托“仙家”送養來的孩子。七奶奶是遠近有名的神婆,如今,七奶奶快死了。一系列奇怪的事情找上了步規,步規為了活命,只能硬著頭皮,面對將要到來的危機。鄉野詭事,民間傳聞,奇詭禁忌,一副光怪陸離的民間雜談,在步規面前展開……
196.6萬字8 5253 -
連載137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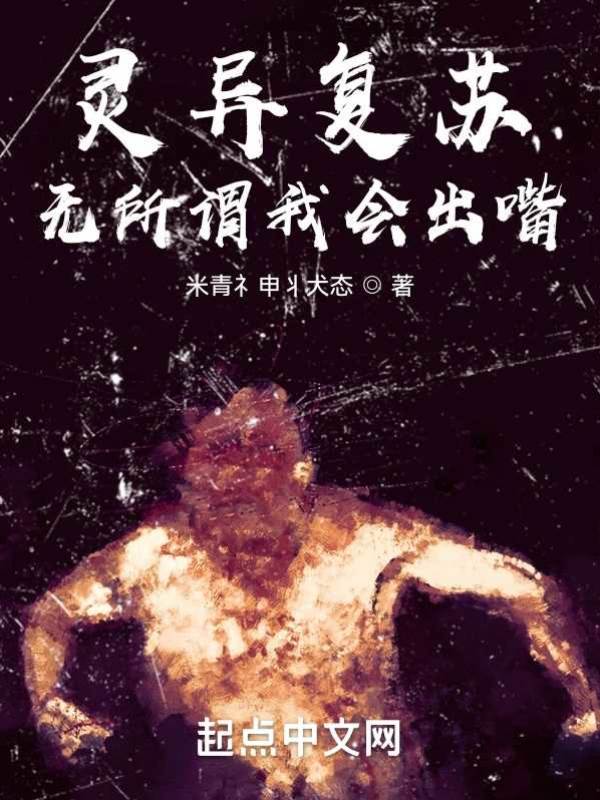
靈異復甦?無所謂我會出嘴!
每天看十個地獄笑話,再攻擊十坨答辯,然後隨機抽取十名幸運路人激情對線,最後再對佛祖進行毫無悔改之意的懺悔。 終於,我的功德掉完了,但我也無敵了。 我本以爲我只是無敵於人類, 直到白天下葬的死者被我在晚上從墳裡刨了出來...... 江湖術士,通天法師,半步仙人,自在真神; 冤魂擾心,厲鬼傷人,兇煞毀德,煞神滅道。 靈異復甦在即,百鬼夜行或在今朝! 不過,現在有個很重要的問題… 誰能告訴我爲什麼我用佛法修出了邪術啊?!
32.9萬字8.18 383 -
完結301 章

第三十年明月夜
第三十年,明月夜,山河錦繡,月滿蓮池。 永安公主李楹,溫柔善良,卻在十六歲時離奇溺斃於宮中荷花池,帝痛不欲生,細察之下,發現公主是被駙馬推下池溺死,帝大怒,盡誅駙馬九族,駙馬出身門閥世家,經此一事,世家元氣大傷,寒門開始出將入相,太昌新政由此展開。 帝崩之後,史書因太昌新政稱其爲中興聖主,李楹之母姜妃,也因李楹之故,從宮女,登上貴妃、皇后的位置,最終登基稱帝,與太昌帝並稱二聖,而二聖所得到的一切,都源於早夭的愛女李楹。 三十年後,太平盛世,繁花似錦,天下人一邊惋惜着早夭的公主,一邊慶幸着公主的早夭,但魂魄徘徊在人間的小公主,卻穿着被溺斃時的綠羅裙,面容是停留在十六歲時的嬌柔秀美,她找到了心狠手辣、聲名狼藉但百病纏身的察事廳少卿崔珣,道:“我想請你,幫我查一個案子。” 她說:“我想請你查一查,是誰S了我?” 人惡於鬼,既已成魔,何必成佛? - 察事廳少卿崔珣,是以色事人的佞幸,是羅織冤獄的酷吏,是貪生怕死的降將,所做之惡,罄竹難書,天下人恨不得啖其肉食其血,按照慣例,失勢之後,便會被綁縛刑場,被百姓分其血肉,屍骨無存。 但他於牢獄之間,遍體鱗傷之時,卻見到了初見時的綠羅裙。 他被刑求至昏昏沉沉,聲音嘶啞問她:“爲何不走?” 她只道:“有事未了。” “何事未了?” “爲君,改命。”
48.8萬字8 5261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