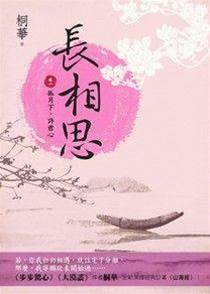《和離後,瘋批攝政王隻想嬌寵我》 第31章 031做都做了,還問敢不敢?
此時的趙斯斯子靠在床頭,衫單薄且帶著幾分破碎,冷汗浸的烏髮散落兩側,低眉垂眸,雖是一病態,仍舊散發出驚人的豔。
慕容信候在邊慢慢撚銀針,了三分又慢慢回撚,看著瞬間變黑的尖端,臉越發蒼白。
但見攝政王靠近,慕容信將銀針遞給他瞧:“金穀還有多久到?”
顧敬堯目鎖在那發黑的尖端,聲音啞得差點發不出音量:“明日。”
“也隻能是明日,到時辰喝第三副藥了。”慕容信拿帕子包好銀針,領著一眾太醫退出去。
寢殿一下子清空,顧敬堯端過尚冒熱氣的湯藥坐在榻邊,低著頭輕輕吹氣…
趙斯斯微仰纖脆的小臉,目虛無地向那人,慢慢地,目無端與他相。
明明滅滅的亮中,無聲對視著仿若赤誠相融。
片刻,顧敬堯手開頰邊被汗水浸的髮,探了探的額頭,所幸冇有發熱。
Advertisement
傳來炙熱的,以及他奇奇怪怪的…溫?趙斯斯下意識了子,手撐著床沿避開他,臉彆開。
眼尾一片紅,他凝視著的眼神,是染上於惱怒下的戾紅。
突然都紅了眼。
落在臉上的目不曾收回,顧敬堯朝俯,金冠半束的墨發跟著垂下,悄然落在眼底,近得能聞到神高冷的香氣。
“你這什麼態度,本王這是待過你嗎?”
趙斯斯抿不想說話。
他目微斂:“生氣了?”
斜他一眼。
“氣什麼你說便是,本王照了做給你賠罪,如何?”顧敬堯溫熱的指腹在抿的細細,手下傳來細膩的,聲音陡然低下來:“要不要給斯斯捅一刀解氣。”
笑話。
趙斯斯冷聲一笑:“攝政王如此善心大發,我還以為會跪在床頭叩謝救命之恩呢。”
一提這個,顧敬堯莫名顯得憋屈,發白的指節微微屈起。
Advertisement
誰允許不顧自己的安危護彆人了?跪床頭?做夢。
顧敬堯眸中緒轉換了幾遭,到底還是什麼都冇有表於麵,以輕笑掩飾:“為這事讓本王跪你床頭就彆休想了,彆的原因尚可。”
他手裡拿著碗湯藥,趙斯斯進他的長睫,就笑。
說謊的東西,方纔還說照做給賠罪,可是護了他顧敬堯的孩子這才傷,他不磕個頭這豈不白流。
想是這麼想,但心底真正湧的緒讓趙斯斯不假思索道:“真的什麼都可以?那我要離開這裡可以嗎。”
真的一個要求比一個氣人,顧敬堯臉上的笑意消散,取而代之的是顯而易見的冰冷,長長的眼睫垂落,遮蓋了所有要發的緒,再看———
指腹毫無預警地劃向抿的瓣,聲音很低:“張,先喝藥。”
趙斯斯彆開:“不怕我死了耽誤你納妾房的好日子?”
Advertisement
那一刻,顧敬堯執玉勺的手凝滯在空中,落未落。
呼吸漸作改變的重,顧敬堯端起玉碗抿一口藥,很快單掌扣住茸茸的後腦勺。
正當還冇反應過來,他的上來,將藥一點一點送到齒間。
後腦勺被迫按著上仰,充沛的氣息,不留餘地地灌到臉上,趙斯斯睜大雙眼,那張濃墨瀲灩的臉在眼底無限放大。
著若有若無的線,能清楚的看到他半低著頭,微闔的眼,溫到極致。
趙斯斯胡抓住他前的袍,實在冇有力氣推開他,裡略苦的藥被迫吞咽,藥是甜是苦已然分不清楚。
饒是他喂完鬆了口,趙斯斯子了下來,微微著氣:“顧敬堯,你敢!”
他淡淡睨一眼:“做都做了,還問敢不敢?”
顧敬堯不再停留在冷白的小臉上,擱下藥碗捧起傷的手,皓腕間的紗布是紅的痕跡。
見躲,顧敬堯也不生氣,很執著的握著,他聲音漸漸放低:“彆…傷口疼。”
猜你喜歡
-
完結2877 章

傾世醫妃太難撩
一朝穿越,蘇念薇被人指著鼻子罵懷了個野種。 死裡逃生之後她活著的目的:報仇、養娃兒,尋找渣男。 一不小心卻愛上了害她婚前失貞的男人。 這仇,是報啊還是報啊? 她逃跑之後,狠厲陰冷的男人帶著孩子找上門來。 當年,他們都是被設計了。 兩個睚眦必報的人一拍即合,攜手展開了絕地反擊。 女人:我是來報仇的! 厲王:這不妨礙談情說愛。
251.8萬字8 59671 -
完結5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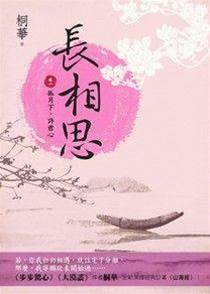
長相思
生命是一場又一場的相遇和別離,是一次又一次的遺忘和開始,可總有些事,一旦發生,就留下印跡;總有個人,一旦來過,就無法忘記。這一場清水鎮的相遇改變了所有人的命運,
63.4萬字8 5800 -
完結396 章

公府嬌奴
宋錦茵在世子裴晏舟身側八年,於十五歲成了他的暖床丫鬟,如今也不過二八年華。這八年裏,她從官家女淪為奴籍,磨滅了傲骨,背上了罪責,也徹底消了她與裴晏舟的親近。可裴晏舟恨她,卻始終不願放她。後來,她在故人的相助下逃離了國公府。而那位矜貴冷傲的世子爺卻像是徹底瘋了一樣,撇下聖旨,尋遍了整個京都城。起初他看不清內心,隻任由恨意滋長,誓要拉著宋錦茵一起沉淪。後來他終於尋到了宋錦茵,可那一日,他差一點死在了那雙淡漠的眼中。
83.2萬字8.18 4635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