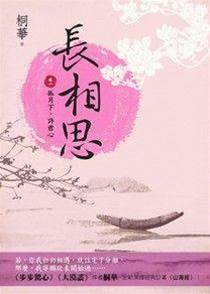《嫁病嬌后我咸魚了》 第81章 第 81 章
征伐高句麗一事往后推遲了, 衛澧除卻吃飯睡覺的時間,幾乎都悶在書房里了,除卻陳若江和幾個親信的將領往來送公文信件, 旁的都不曾見過。
趙羲姮怕他憋出病,也怕他現在用勁兒用猛了三分鐘熱度, 這樣的日子過了幾天后,有點兒忍不住,帶著人去書房找他了。
桌上糟糟堆著公文, 書簡,衛澧坐在桌子前,一見進來, 然的看了看糟糟的桌子, 然后急忙收拾起來。
趙羲姮哭笑不得,也不說他,只是搬了個椅子, 坐在一邊兒剝了個橘子給他,一瓣一瓣的塞進他里,“你這些天都看什麼了?連房門都沒出一步。”
前幾天跟條韁野狗似的,這幾天實在太安靜了。
衛澧一口一口的吃橘子, 覺得很甜。
他搬來了一摞冊子給趙羲姮, “你看看。”
趙羲姮翻了翻, 全都是阿耶的手札容,一共十本手札,每本謄抄了十遍。
一皺眉,字是真丑, 但衛澧正眼的在一邊兒看著, 趙羲姮也知道這些東西是誰抄的了, 當然不能傷他的心,說字丑。
仔細瞧瞧,還有些照貓畫虎臨摹出來的錯別字,難道平常與陳若江他們通訊都是靠畫圖的嗎?他們就沒說衛澧字寫得不好?
衛澧挑了盤子中最大的一個橘子,剝開后吃了一瓣,似乎比方才的那個更甜,甘微涼的水順著嚨下食道,整個人都治愈了。
他摘干凈絡,給喂給趙羲姮,“我嘗過了,這個甜。”
趙羲姮他的投喂已經形了習慣,一邊吃一邊看冊子,衛澧勾勾的小手指,“你看,我每本都抄了十遍,我很認真的在看,而且都背下來了。”
Advertisement
趙羲姮略有吃驚,他遞過來的橘子瓣也忘吃了,“你全都背下來了?”
這十本手札,說也有幾萬字,才不到五天,衛澧不但每本抄了十遍,還全都背下來了?
“自然,寫兩遍不就都背下來了嗎?”趙羲姮的吃驚讓衛澧很用,他微微揚起下,用一種若無其事但充滿炫耀的語氣道。
“求夸獎”三個大字都印在他臉上了,趙羲姮隨便挑了一本,考問他,“最后與高句麗一戰,設立平州,用了三十六計中的哪幾計?”
“反間計,反客為主,聲東擊西。”衛澧想也不想,對答如流,他甚至還能結合孫子兵法與平州當年的況一一做出解釋。
趙羲姮眼睛一亮,又隨手撿了幾個問題問他,不想每一問他都答得上。
才短短五天的時間,不說能不能吃理解,單就是能記住,就已經很不錯了,可見頭腦還是聰明的。
衛澧臉上的得意更甚,幾乎是憋不住了,趙羲姮安的起抱抱他,親親他的臉頰,“真棒,主公變得越來越厲害了。我和孩子將來就靠你了。”
他顯然是很吃趙羲姮這一套的,臉頰和耳朵都紅紅的,心里也激,“你男人當然厲害,將來會變得更厲害的。”
趙羲姮欣之余,另覺得有些心酸,衛澧不笨,若是能投胎在個什麼富貴人家,想必也不會養這樣的子,至以他的聰明,會是個才學淵源,心有壑之人。
但是現在這個字啊……
趙羲姮磨了些墨,將筆塞進衛澧的手中,“你坐好,不要看我。”
衛澧著筆桿,有些奇怪,但還是乖乖聽話。
“你寫個富裕的裕字給我看看。”趙羲姮站起來,在他后吩咐。
Advertisement
讓他寫字?
衛澧思及自己那狗爬一樣的字,腦海中不自覺拿自己的同趙星列來對比,簡直一個天上一個地下,臉頰燥熱,一個頭兩個大,“要不不寫了吧,我累了。”
趙羲姮推推他的手臂,“寫嘛,只寫一個字,累不到你的。”
衛澧沒辦法,又犟不過,只能一筆一劃,像爬一樣的在紙上寫下一個“裕”。
他飛快將紙一團,“這次不算,我重新寫一個。”
他不知道為什麼,方才手抖得厲害,分明前幾日謄寫手札的時候都沒這樣張,趙羲姮的目落在他的脊背上,似乎能給他灼出個來。
衛澧提起筆,試圖穩當當的落在紙上。
而趙羲姮的目如有實質,好像又順著脊背,落到了宣紙上,衛澧不自覺的將的更低,來遮擋的視線。
他像個初進學堂,寫字姿勢不規范的學生。
一連作廢了好幾張紙,衛澧的耳已經紅到快要滴,趙羲姮抬手了,給他降溫,心里好笑,這家伙,又害了。
給看那十遍謄寫的時候,狗爬字兒也拿得出手了,現在當著面兒寫就不好意思,真是……像個小孩子一樣。
一自己的耳朵,衛澧子不由得一,最后自暴自棄似的,也不遮掩了,將寫好的字出來給。
“就寫這樣兒了,你笑話也沒辦法……”他看著趙羲姮揚起的角,垮下了肩膀,“你想笑就笑吧。”
趙羲姮覺得他現在可極了,從背后抱住他,親親他的耳尖,然后把著他的手,在紙上一筆一劃寫了個“裕”字。
“你看到沒有,這里這筆是不能出頭的。你當時讀書寫字是誰教你的?”衛澧既然字寫得不好,趙羲姮就要教,至旁的不會,教人寫字這種活兒,做得還是能得心應手。
Advertisement
衛澧是因為年時候的經歷,所以知識文化跟不上,趙羲姮覺得自己不能兇他,要好好教,不自覺的將語氣放得更了些。
衛澧沒回應,他現在已經麻了,渾上下都彈不了,也說不出話,腦袋里原本運轉飛速的思維一下子漿糊住了,僵的像是一座石碑。
他只能會到趙羲姮溫熱甜暖的氣息,吹拂在他頸側耳廓的皮上,的。還有方才親過的地方,滾燙的要燒著了一樣。
的綿綿的,在他的脊背上,兩個人的溫相融,而的手正包著自己的,一點一點在紙上挪移,糯的時不時輕輕過他的耳廓,令他渾的逆流,耳朵里嗡嗡的,最后連問了什麼都察覺不到。
分明平日里,兩人更親的相每日都有,但總覺得這次不一樣……
書房里正正經經的地方,天大亮著,窗半開著,外頭有走來走去的腳步聲,而他們相著,四周好像都充滿了曖昧的氛圍。
怪不得那些人都喜歡紅袖添香。衛澧結上下滾,往懷里靠了靠,綿綿的。
他思緒不知道飄去哪兒了,臉紅了一片。
趙羲姮說得很認真,是準備好生給衛澧當個習字先生的。
一低頭,看見他在出神,忍不住用筆桿敲了一下他的腦袋,“我剛才跟你說的你聽見了沒有?”
衛澧眨眨眼睛,“能再講一遍嗎?”
趙羲姮瞇了瞇眼睛,耐下心來,把著他的手在紙上又寫了個“裕”字,他人太大一坨了,從背后抱著并不怎麼方便,只能盡力把低。
衛澧這個做學生的,一邊占著先生的便宜,一邊聽課,世上再沒有比他更快活的學生了。
Advertisement
趙羲姮問他,“我剛才說這個豎出頭嗎?”
衛澧迷迷糊糊,令智昏,點頭,“出出出。”
趙羲姮一扯他的耳朵,罵道,“出什麼出?出你個大頭鬼出!我什麼時候說這個豎要出頭了?你耳朵里是不是塞驢了?我剛才跟你講話你都聽哪兒去了?到底出不出?”
衛澧耍無賴一樣的抱住的腰,卻不敢使勁兒,臉不知道往哪兒不可言說的地方,“阿妉我累了,我們現在去睡午覺吧,等明天我再寫。”
他其實聽懂了,就是想多親近親近,讓多握著自己的手寫點兒字。
但見趙羲姮要生氣了,連忙哄道,“我真的會了,不信我寫給你看,寫完了咱們倆去睡午覺。”
他連忙挽袖,落筆工工整整寫了一遍,倒是沒什麼錯的,就是不怎麼好看。
趙羲姮見他的確是會了,氣稍微消了,看了眼天,是已經過了晌午了,洗了手后干,“是應該睡午覺了。”
衛澧顛顛兒的跟著要一并出去。
“我說要跟你一起睡午覺了嗎?好好教你寫字你不學,把那個字給我抄一百遍!不然晚上也不要回去睡覺了!”趙羲姮轉走了,將書房的門摔上。
衛澧當然不能死纏爛打的再跟上去,生怕晚上也不能抱著人睡覺。失魂落魄的坐回書桌前,準備完趙羲姮給他的任務,千分萬分的不愿,早知道就好好回答了。
趙羲姮去而復返,衛澧眼睛一亮。
仰著下道,“以后我天天給你檢查功課寫字,寫不好就不要回房間睡覺了。”
衛澧的眼睛又黯淡下來,他抓抓頭發,愁容滿面。
寫字能看懂不就行了嗎?干嘛非要半點兒不差。
“那你明天還要這樣教我好不好?”但是如果有額外福利的話,他還是很樂意的。
猜你喜歡
-
完結2877 章

傾世醫妃太難撩
一朝穿越,蘇念薇被人指著鼻子罵懷了個野種。 死裡逃生之後她活著的目的:報仇、養娃兒,尋找渣男。 一不小心卻愛上了害她婚前失貞的男人。 這仇,是報啊還是報啊? 她逃跑之後,狠厲陰冷的男人帶著孩子找上門來。 當年,他們都是被設計了。 兩個睚眦必報的人一拍即合,攜手展開了絕地反擊。 女人:我是來報仇的! 厲王:這不妨礙談情說愛。
251.8萬字8 60165 -
完結5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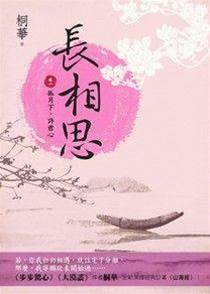
長相思
生命是一場又一場的相遇和別離,是一次又一次的遺忘和開始,可總有些事,一旦發生,就留下印跡;總有個人,一旦來過,就無法忘記。這一場清水鎮的相遇改變了所有人的命運,
63.4萬字8 5805 -
完結396 章

公府嬌奴
宋錦茵在世子裴晏舟身側八年,於十五歲成了他的暖床丫鬟,如今也不過二八年華。這八年裏,她從官家女淪為奴籍,磨滅了傲骨,背上了罪責,也徹底消了她與裴晏舟的親近。可裴晏舟恨她,卻始終不願放她。後來,她在故人的相助下逃離了國公府。而那位矜貴冷傲的世子爺卻像是徹底瘋了一樣,撇下聖旨,尋遍了整個京都城。起初他看不清內心,隻任由恨意滋長,誓要拉著宋錦茵一起沉淪。後來他終於尋到了宋錦茵,可那一日,他差一點死在了那雙淡漠的眼中。
83.2萬字8.18 46905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