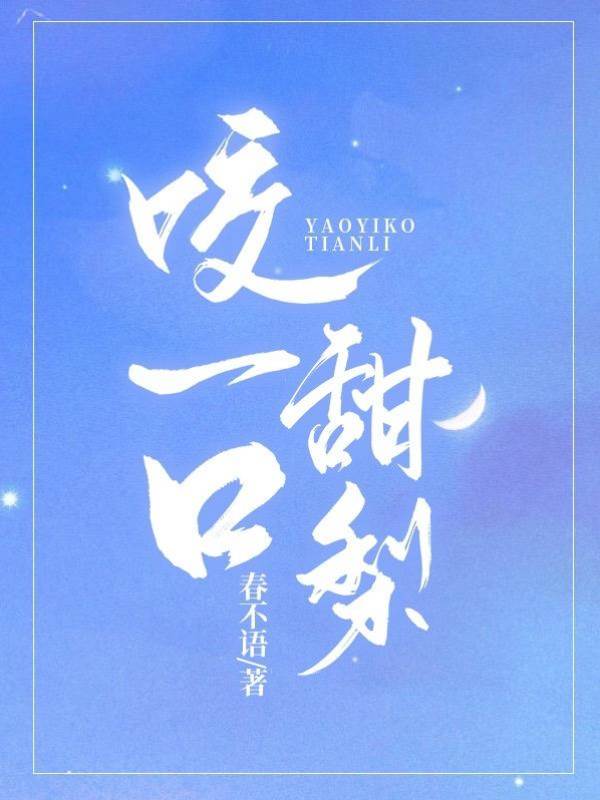《強勢鎖婚:傅少的啞巴新妻》 359 你別不識好歹!
“喬先生,你有什麼事,很著急嗎?”
安平管家對喬深的稱呼已經從喬助理改為了喬先生。可盡管這樣,喬深還是生出了一種無力,心里生出了對自己的諷刺。
不管他怎麼努力,從平凡人到權貴之間的差距,不是只憑著幾年時間就能越過去的。
也難怪張業亭
喬深握了下手指,擺了下手道:“沒事。”
他轉離開傅邸。
安平管家皺眉看著他的背影,覺得喬深心事很重。但他又沒說是什麼,安平管家也只能無奈搖頭。
夜幕降臨,街燈車影幻化出夜中盛景,一輛法拉利在1988的門口吱的一聲停下。
莫非同看到喬深進來,詫異的看他:“你小子怎麼跑過來了?”
莫非同坐在吧臺上,看到喬深沖著他走過來,那一臉急的樣子讓他收起了玩笑,從吧凳上站起來。
喬深站定,說道:“莫先生,想請你幫一個忙。”
莫非同擰了擰眉,還沒說什麼,目看向了喬深的后。
喬深覺到了異樣,轉頭看過去,就見裴羨跟燕伶站在他的后面,裴羨轉頭正看著別,好像故意不看喬深似的。
燕伶對著喬深點了下頭:“喬先生。”
喬深便也對點了下頭,視線他們握的手臂上一掃而過。他急著救人,對著莫非同道:“莫先生,能借一步說話嗎?”
這時,裴羨轉過頭來,看了喬深一眼。
喬深微擰了下眉,莫非同看了眼裴羨,再看看喬深,點了下頭往門口走去。
莫非同一揮手,角落站著的兩個看著像是保安的便離開了。莫非同點了煙:“跟喬影有關?”
在莫非同的眼里,喬深是個努力認真的乖寶寶,不流連酒吧會所,頂多電影院看看電影。他來會所定是有重要的事,而不能當著裴羨的面說的,也就跟喬影有關的事了。
Advertisement
喬深看了他一眼,眉頭深深的皺起。
當喬深說明幫什麼忙時,莫非同驚愕的香煙差點掉在地上:“你、你說什麼?”
喬影是醫生,是救人的,竟然捅人去了?
“捅了什麼人?”
喬深的眉頭皺得死,語氣卻是極為冷淡,好像這個名字不值一提:“張業亭。”
驟然聽到這個名字,莫非同怔愣了下,好像在哪里聽說過,猛然想起時,煙頭落在地上,一臉震的看著喬深。
喬深的眉頭皺得更深了一些:“莫先生,這件事請你不要告訴任何人,也不要問原因。”
莫非同呆愣看他:“不問原因,那我怎麼保釋?”
喬影拿手剪捅人,認證證都有,傷者還在醫院沒有醒來。莫非同也是無語了,他不是警察局局長,就算是局長,也不能不問任何緣由的答應放人吧?
喬深默了默:“我再想想辦法。”
他轉要走,莫非同攔住他道:“你等一下,我先去看看。”
認識一場,莫非同既然知道了這件事,哪里能不幫忙。
說著他便往門外走,連回去跟看場子的經理打聲招呼都沒有,從門口的泊車小弟那兒拿了車鑰匙就走。
會所里面,裴羨拿著一杯尾酒慢慢轉,沒有沾一口。
莫非同沒回來,便是很要的事了。
傅寒川調教出來的人,不會那麼不頂事,除非是真的遇上了不能解決的事兒。
喬深雖然出平凡,但是骨子里很傲氣,讓他低下頭來求人辦事,又是避開了他
裴羨的眼底氤氳不明,抬起酒杯抿了一口。
車子在馬路上疾馳,不一會兒就到了看守所。
莫非同跟警局的大隊長打了通電話,一會兒人就過來了。
Advertisement
大隊長姓邢,先跟莫非同寒暄客套了幾句,然后對著喬深道:“喬先生,不是我不給你面子,就算你把莫先生搬過來,這件事我也很難辦。”
誰不知道喬深是傅寒川面前的紅人,誰不給他一點面子,要是普通的事他早就放人了。
邢大隊長嘆了聲氣,又要應付莫非同,一副為難的模樣說道:“莫先生,當事人不愿意開口,我們總不能就這麼放人吧?”
“是醫患糾紛,還是別的原因,我們總要有個說法,你說是不是?再者,我們查到傷者是籍”
說到這里,邢大隊長不用繼續說下去,莫非同也知道這里面的復雜了。
那個張業亭居然是籍,他的眉頭高高皺起,這事兒確實難辦了。
邢隊長再看了一眼喬深:“也就這兩天的時間,人在我們這里,我一定好好照顧著。不過你們也勸著點兒,讓代點什麼,我們好辦事,吃苦,你說是不是?”
邢大隊長打道的人多了,權貴要求最多最難辦,他已經很給面子,答應讓手下照顧著點兒,可千萬別再找他的麻煩。
莫非同這邊,他也知道沒有任何代就人放人難辦,現在上面盯得,不是給錢或者施就能解決的事兒。邢大隊長肯松口說幫著照看已經是很大的面子。且不說這里關押的都是什麼人,是接警詢調查,就不是一個普通人能的了的。
莫非同皺著眉:“那我能去看看嗎?”
邢大隊長一聽,立即親自帶路,心想只要這位小爺不要蠻不講理,胡攪蠻纏就好。
喬影被單獨隔離了起來,沒有跟別的關押人員放在一起。
大隊長把人帶到以后就走了出去,沒有多停留。
Advertisement
莫非同鐵門,喬影蜷坐在角落,看到莫非同進來,眉頭只是皺了下,轉眸看了眼喬深。
喬深道:“我沒有讓他知道。”
喬影便把目收了回去。
莫非同來回看了看這對姐弟,說道:“喬影,你現在不愿意說,可等到那個張業亭醒過來,警方還是一樣會知道,又何必在這里吃苦?”
喬影冷笑了一聲道:“我倒是要看看他敢不敢說實話。”
出去了,還要再補上一刀,讓他徹底醒不過來。
莫非同看到了喬影眼中的殺氣,怪異的看了眼喬深。喬深道:“那種狼心狗肺的東西,有什麼不敢說的。他要是用這個來要挾你,你就要吃這個虧嗎?”
所以,喬深才覺得喬影沖,捅了他那一下,反而被人抓住了把柄。
喬深現在著急的,就是怕那姓張的醒來以后用這作為理由倒喬影,或是喬家的人。
要是張業亭鬧到了父母那里,這件事就更難收場了。
喬深現在做的,就是早做防范,不然他也不會求到莫非同那里去。
莫非同聽著云里霧里,要說人之間不歡而散的多了去了,可到了要殺死對方的地步,這到底是什麼深仇大恨。
跟那個小孩有關?
當年喬影怎麼生下了孩子,還能若無其事的跟裴羨在一起,又莫名其妙的狠心分手,現在又為了殺死對方把自己弄到看守所來了
莫非同腦子里一團,完全看不明白了。
按照那個小姑娘的年齡推算,是張業亭的兒嗎?
若是這樣的關系在,喬影還能恨到要殺了他,那到底是怎樣的仇恨?
再者,殺了他,自己就要坐牢。拼著坐牢也要殺了對方的心理,對那個小姑娘就沒有半分顧念了嗎?
Advertisement
莫非同覺,這件事不是喬影在看守所待幾天的事兒。
正琢磨著怎麼把喬影弄出去,莫非同的手機響了起來。他看了眼號碼,眉頭皺了皺,瞥了一眼喬影。
喬影的目看過來,在不停歇的鈴聲中,莫非同鎮定自若的道:“我先接個電話。”
他往外走出去,到了喬影聽不到的地方才接起了電話。
裴羨慵懶的聲音混著會所的音樂傳過來:“三,人在哪兒呢,還喝不喝了?”
莫非同撓了下下,想他也許不應該淌了這趟水。他道:“一會兒就來,你先喝著吧。”
他掛了電話,轉時,喬深走了過來,一臉無奈的道:“我們先回去吧。”
他往后面看了一眼,那個方向是關著喬影的單間。看樣子,喬影把他也趕出來了。
莫非同一臉嚴肅的道:“喬深,問你一句真話,那個小姑娘,跟那張業亭是什麼關系?”
“你知道這里面的厲害關系。那人要是醒來告喬影的話,是蓄意傷人,要坐牢的。”
往大了說,喬影那是殺人未遂。
喬深的眉頭就沒松開過,他淡淡道:“莫先生,很激你來了一趟。我送送你吧。”
喬影擔心莫非同會告訴裴羨,剛才把喬深罵了一頓,說若他再找莫非同幫忙,就連他也不要手了。
莫非同回到了1988,裴羨還在那里,不經意的問道:“喬深讓你干嘛了?”
莫非同道:“沒什麼。”一句話就這麼打發了過去。
莫非同回來以后沒多久,裴羨跟燕伶就說要回去了。他把燕伶送回了公寓,燕伶道:“不留下來嗎?”
裴羨道:“想起來還有一點事要理。”
燕伶沉默了下來,大概過了兩秒,抬起眼眸道:“是的事兒嗎?”
裴羨抿住了,他微低頭,淡淡說道:“在看守所。”
莫非同離開1988的那段時間,裴羨借著打電話定位了他的位置。
得知在看守所,裴羨的心臟那時清楚的了下。他白天的時候跟那個人不歡而散,怎麼晚上就進去了。
他想不明白。心里明明告訴自己不要再管的破事,可知道了又心里鉆了牛針似的搗得他心思不定。
燕伶得到了答案,角微牽了下,他回答的倒還算坦白。
道:“我能跟你一起去看看嗎?”
站在的立場,是裴羨的友,自己的男朋友去見前友,是應該鬧脾氣阻止的。可那個人在看守所,那定是出了什麼事兒。
燕伶不想讓自己變得不近人,再者,就算阻止了裴羨,他心里反而更加放不下。
更何況說起來,跟喬影也是認識的。
燕伶能想到的,就是跟裴羨一起過去,看能不能幫上什麼忙,也是守住了自己的男朋友。
裴羨微怔,看著燕伶。
其實莫非同已經去過看守所,說不定已經把問題解決了。燕伶大可以說不需要他摻和進去。
他點了下頭道:“那就去吧。”
兩人一起再去往看守所,此時已經是深夜了。邢大隊長剛到家里正要睡下,枕頭還沒沾上就又被電話了起來。
電話里,值班警員又說有人來探視,邢大隊長極力控制自己的脾氣不要發。現在都流行夜里探監了,他們以為這樣的番轟炸,他就會妥協了嗎?
邢隊長對著電話吼:“你就不能隨便找個理由把人應付了不就完事了!”
警員小聲道:“是裴家的二公子。”
“裴、裴家?”
邢大隊長愣住了,裴夫人的妹妹嫁的是省書長,也就是說,省里那位是裴羨的姨夫。
裴家低調,但對這些人來說,這些權貴之間的關系得門清,邢大隊長頓覺頭都大了,說道:“你先在那兒應付著,我一會兒就來。”
說著,他又停頓了下,補充道:“除了不能把人放出去,別的你都隨便。”
電話那頭警員哎哎的答應了,然后就帶著裴羨去單間了。
警員掛在腰間的鑰匙叮叮當當的響,在空曠的看守所,在這樣的深夜中,聽起來有種詭異的覺。
過門上鑲著的觀察口,可以看到關押著的人都已經睡下了,來到盡頭的一間單間,里面的人靠著墻壁,還有之前見到時的那個姿勢。
警員說道:“喬影,有人來看你了。”他開了門就離開了。
喬影眼眸微了下,看到面前站著的人時,瞳孔倏地震了下,呼吸也梗住了。嚯的站起來:“誰讓你來的!”
猜你喜歡
-
連載223 章

總裁追婚記:嬌妻哪裏逃
三年前,初入職場的實習生徐揚青帶著全世界的光芒跌跌撞撞的闖進傅司白的世界。 “別動!再動把你從這兒扔下去!”從此威脅恐嚇是家常便飯。 消失三年,當徐揚青再次出現時,傅司白不顧一切的將她禁錮在身邊,再也不能失去她。 “敢碰我我傅司白的女人還想活著走出這道門?”從此眼裏隻有她一人。 “我沒關係啊,再說不是還有你在嘛~” “真乖,不愧是我的女人!”
29.6萬字8 5203 -
完結1939 章

替嫁后我被大佬纏上了
所有人都說,戰家大少爺是個死過三個老婆、還慘遭毀容的無能變態……喬希希看了一眼身旁長相極其俊美、馬甲一大籮筐的腹黑男人,“戰梟寒,你到底還有多少事瞞著我?”某男聞言,撲通一聲就跪在了搓衣板上,小聲嚶嚶,“老婆,跪到晚上可不可以進房?”
290萬字8.18 188313 -
完結105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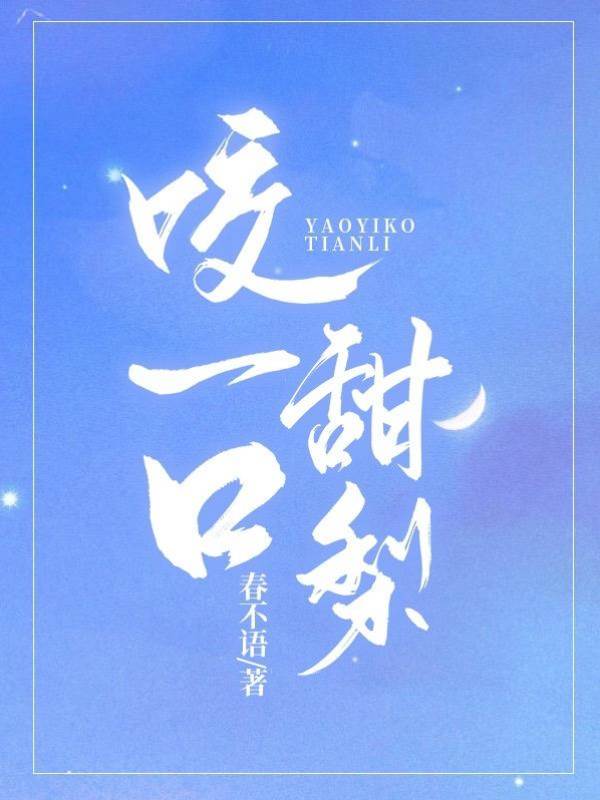
咬一口甜梨
白切黑清冷醫生vs小心機甜妹,很甜無虐。楚淵第一次見寄養在他家的阮梨是在醫院,弱柳扶風的病美人,豔若桃李,驚為天人。她眸裏水光盈盈,蔥蔥玉指拽著他的衣服,“楚醫生,我怕痛,你輕點。”第二次是在楚家桃園裏,桃花樹下,他被一隻貓抓傷了脖子。阮梨一身旗袍,黛眉朱唇,身段玲瓏,她手輕碰他的脖子,“哥哥,你疼不疼?”楚淵眉目深深沉,不見情緒,對她的接近毫無反應,近乎冷漠。-人人皆知,楚淵這位醫學界天才素有天仙之稱,他溫潤如玉,君子如蘭,多少女人愛慕,卻從不敢靠近,在他眼裏亦隻有病人,沒有女人。阮梨煞費苦心抱上大佬大腿,成為他的寶貝‘妹妹’。不料,男人溫潤如玉的皮囊下是一頭腹黑狡猾的狼。楚淵抱住她,薄唇碰到她的耳垂,似是撩撥:“想要談戀愛可以,但隻能跟我談。”-梨,多汁,清甜,嚐一口,食髓知味。既許一人以偏愛,願盡餘生之慷慨。
20.2萬字8 7276 -
連載256 章

全球通緝令,抓捕孕期逃跑小夫人
曾經顏琪以爲自己的幸福是從小一起長大的青梅竹馬。 後來才知道所有承諾都虛無縹緲。 放棄青梅竹馬,準備帶着孩子相依爲命的顏鹿被孩子親生父親找上門。 本想帶球逃跑,誰知飛機不能坐,高鐵站不能進? 本以爲的協議結婚,竟成了嬌寵一生。
45.2萬字8 4335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