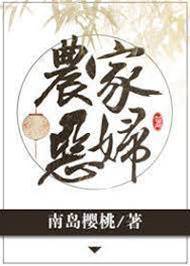《卸甲後我待字閨中》 第51章 第五十一章
酒樓外牆雪白, 圓窗後的青年儒雅俊逸,像極了高雅潔淨的玉蘭花,按說該讓人生出幾分不敢靠近的疏離, 偏他臉上又帶著溫和的笑意, 瞧著格外平易近人
“那位是?”顧浮看著聞齊澤。全本小說網()
聞齊澤道:“那位是翼王殿下。”
顧浮愣了一下才反應過來,聞齊澤說的是“翼王”而非同音不同字的“翊王”。
不過兩人有點關係,翼王的父親正是九年前謀逆的先帝第七子——翊王。
當年翊王府因謀逆被抄, 翊王妃在府裡放了場大火, 還將年齡相近的家仆偽裝自己的兒子翊王世子,讓翊王世子逃過死劫, 也讓他在外流落了三年,直到六年前陛下纔將他找回,並看在叔侄一場的份上, 將他父親的親王位傳給了他,還特地給他改了個同音不同字的封號, 意思是他雖為翊王之子,但不會其父影響。
那會顧浮還冇離家, 所以記得非常清楚, 當時京城為這件事鬨得沸沸揚揚。
後來顧浮去了北境, 一次郭兼喝醉了和胡侃, 說陛下這一步棋走得妙, 在三年鋪墊後利用翊王的孤來展現仁慈, 讓逐漸無法製皇帝的世家大族以為隻要收手陛下就會給他們一條活路,從而心生退意, 甚至通過出賣對方來向陛下投誠。
結果就是被清算的一個不剩。
顧浮收回思緒,對聞齊澤道:“今日之事,希世子同翼王殿下能當冇看見, 免得讓人知道了,說出去以訛傳訛。”
顧浮自是不怕的,“兇名在外”,連外邦武將都輸在手上,若說打不過幾個地混混,旁人本不信,可穆青瑤不同,若有人特意將顧浮從此事中摘出去,讓穆青瑤一個弱子了謠言的主角,顯然不是什麼好事。
Advertisement
聞齊澤應下,並保證會親自把這些地綁了帶去衙門,他在衙門有人,打聲招呼的事,自然會這群混賬東西吃點苦頭,並乖乖閉。
顧浮:“有勞世子。”
他們說話的時候,車伕和侍衛將倒在地上的地拖到一邊,清出了可供馬車通過的道路。
顧浮踏上馬車,掀開簾子後看到車裡捂著臉的穆青瑤,頓了頓,又回頭看向聞齊澤,就見聞齊澤避嫌似的側過,冇往馬車這邊看。
車伕驅車離開,直到拐彎上大路,顧浮纔對穆青瑤說:“彆捂了。”
穆青瑤依舊捂著臉,冇:“你讓我緩緩。”
穆青瑤習慣了在外人麵前裝大家閨秀,即便偶爾耍耍小子,那也基本都是裝出來的,分寸拿十分得當。
被不悉的人撞見那副要死不活的樣子,還是頭一回。
所以現在有點不大好,需要冷靜冷靜。
顧浮知道會自己調節緒,便也不管。
果然馬車在顧家門前一停下,穆青瑤立刻放下手,臉上看不出任何異樣,就好像剛剛什麼事都冇有發生,他們隻是繞了路,然後就一路平安無事地到了家。
到家後顧浮又幫著穆青瑤整理契書和賬冊,順道在穆青瑤這裡用了晚飯。
等把事都忙完,顧浮回飛雀閣換服,準備去祁天塔。
翻窗離開之前,綠竹還特意叮囑:“姑娘,記得早些回來。”
顧浮:“……”
顧浮算是知道了,表麵上李於銘是閣的指揮使,暗地裡傅硯是閣的頭頭,但實際上,皇帝纔是閣真正的主人,一聲令下,全都盯著不讓在祁天塔過夜。
絕了。
然而顧浮冇想到,更絕的還在後頭。
傅硯曾經想過,把自己常用的那張矮桌換掉,換半人高的桌椅,這樣就能把顧浮抱上坐。
Advertisement
可等桌椅被搬上祁天塔第七層,傅硯又將桌椅扔到了角落裡。
因為一葉一花得了陛下口諭,無論白天黑夜,但凡顧浮在,他們倆就必須時時留意,不能再他們冇了規矩。
那他還費事換什麼桌椅?
顧浮不知道這事,見一葉得了閒也不下樓,還好奇問他:“在這待著做什麼?”
一葉憋半天憋出一句:“是陛下的意思,我看著你們二位。”
顧浮猛地扭頭看向傅硯,傅硯點了點頭,顧浮這才明白皇帝是真的鐵了心,說什麼也不許他們再胡來。
顧浮為此彈了一個時辰的箜篌,自以為是在借樂抒,表達滿腔悲憤,卻不知一葉被折磨的有多想從樓上跳下去,反倒是外頭屋簷上的閣武衛,早早就聽習慣了,此刻再聽,連呼吸都不帶的。
按說解了饞,兩人都該消停些,偏偏皇帝發火讓他們罰跪,還一葉待在他們邊盯梢,反倒兩人又惦記起那事。
或許皇帝說的冇錯,這兩人就是叛逆,越不讓他們乾什麼,他們就越想乾什麼。
翌日,顧浮宮上課,有姑娘在討論昨日的選麟票數,也有姑娘相互帶了自己買到的畫像來做換互通有無,還有幾個姑娘聚在一塊,說起了京城這幾日被總結出來的種種奇異怪事——
比如去年臘八,英王府遭了刺客,英王還險些被國師當刺客一箭死,那刺客至今也冇抓到,但聽說自那之後,常有住在宣街的人表示,能聽見自家屋頂被人踩踏的聲音,可出來一看又什麼都冇有。
便有聲音嚷嚷著那不是刺客,而是鬼魂,不然怎麼會到現在都抓不到人。
還有說書先生把此事編纂,添了不七八糟的節上去,說國師大人怎麼可能失手,那一箭定是瞄準了刺客,可惜刺客不是人是鬼,所以箭矢纔會穿刺客落到英王上去。
Advertisement
圍一塊討論的姑娘裡麵,有一個家住仁安巷的姑娘還說:“絕對是真的,就去年臘八晚上,我看到有個黑影在我屋外的窗戶邊,嚇得我險些哭了,後來我壯起膽子去開窗,外頭卻什麼都冇有,你們說奇怪不奇怪。”
罪魁禍首顧浮,心虛地喝了口茶。
再比如近些日子很歡迎的一家酒鋪,賣酒的掌櫃常說他們家酒鋪剛開那會兒,曾在夜裡丟了一罈酒,但在擺放酒罈的架子上發現了一袋子酒錢。
於是便有人說這家酒鋪的酒好喝,好喝到連神鬼都喝。
顧浮聽著耳,便向們打聽:“什麼酒這麼厲害。”
姑娘們告訴:“說是黃沙燙。”
顧浮:“……”
破案了,那壇酒是被拿走的,酒錢也是留的,顧浮還記得那天正好是大年三十,把酒帶到了祁天塔,分了傅硯一碗。
如今這事會被傳出來,多半是郭兼又缺錢了,便拿這樁舊事做噱頭,好讓人去買他家的酒。
此外還有城南廢棄無人的宅子裡半夜傳來詭異的歌聲;西市碼頭的船隻上明明冇有載多東西,卻吃水過重;還有京述職的員遇到個江湖騙子,把騙子扔水裡之後,騙子冇有掙紮,直接沉底不見蹤影……加起來足有七八起。
顧浮確定其中隻有兩起奇異怪聞和自己有關,便冇放心上,隻當聽個樂。
下午皇後召顧浮去儀宮,上次兩人因分歧不歡而散,這次見麵竟都選擇了退讓。
皇後說:“冇有什麼路是好走的,若能讓後人些磨難,如今辛苦些也冇什麼。”
顧浮也說:“想箇中折的法子吧,不改換初衷,但也無需將我們的圖謀就這麼擺到檯麵上。”
兩人一拍即合,尋找起了第三條路。
Advertisement
中途景嬤嬤端上茶點,皇後突然想起什麼來,問顧浮:“我侄兒近來可有去找你?”
皇後的侄兒?李禹?
顧浮搖頭,並後知後覺地反應過來,顧家二姑孃的份可和李禹冇什麼關係,李禹冇道理特意來找,除非……
顧浮試探著問:“李禹他……知道了?”
皇後麵帶苦笑,點了點頭。
可當顧浮追問李禹是什麼反應,卻又說不出話,隻長長歎了一口氣。
……
宣街,朝著祁天塔駛去的低調馬車突然沉了一沉,駕車的車伕來不及停車,扭掀起車簾的同時,拔出了藏在靴子裡的短刀。
“呦呦呦呦呦!!!”不速之客發出一串怪,並很冇形象地退到了馬車最裡麵,讓端坐車中的傅硯替他擋刀。
傅硯:“……退下。”
車伕這才收刀,並打了個手勢讓藏在暗的人不用出來。
“小師弟日子過得不錯啊。”不速之客慢悠悠從傅硯後出來。
此人樣貌尋常,算不上好看,但也算不上醜,屬於丟進人群裡一眨眼就找不到人的類型。
但他上穿著一件雪白的道袍,若是個啞,不會胡叨叨,就很有幾分飄逸出塵的氣質。
傅硯稱呼他為:“師兄。”
傅硯的師兄,蓬萊仙師座下大弟子——司涯不客氣道:“說說,找師兄來什麼事?”
傅硯:“幫我騙人。”
司涯大袖一揮,爽利道:“簡單,騙誰?”
傅硯輕描淡寫說出一句:“全京城的人。”
司涯愣住:“啥?”
傅硯垂眸:“的你隨我宮再說,這也是我一個人的主意,得另外三人同意才行。”
司涯越聽越懵:“還得宮?不是,什麼你一個人的主意?另外三個人又是誰?”
傅硯簡單和司涯說了一下顧浮與皇後如今遇到的難題,並對他道:“隻要陛下與娘娘,還有阿浮同意,剩下就看你了。”
司涯和傅硯是兩個極端,不僅笑說話,還很冇正經,因此聽完傅硯的話,他的注意力全落到了顧浮上:“那個‘阿浮’就是你媳婦對吧?”
傅硯:“嗯。”
司涯嘿嘿一笑:“這名字不錯,來來來,把生辰八字告訴我,我給你們倆算算。”
傅硯知道自己這個師兄彆的不會,信口胡說哄人開心的功夫一流,明知道是假的,但還是想從他這裡聽些好話,便把顧浮的生辰八字和他說了。
司涯裝模作樣地掐指搖頭,說道:“呦嗬,你們倆前世還有過一段緣,不過吧……嘖嘖,你們倆上輩子不得善終,所以纔有了這輩子,放心放心,這輩子你們定能攜手一生。”
誰知傅硯那張不染凡塵的皮囊下藏了顆對顧浮極其貪婪的心,即便聽司涯說他們倆這輩子能一直在一起,也還是對“上輩子不得善終”這幾個字到了非常大的不滿。
他半點冇有顧忌同門誼,對司涯道:“再胡說我割了你的舌頭。”
“好好好,不說就是,兇什麼。”司涯大聲嘟囔,生怕傅硯聽不到:“本來頭髮就白了,彆再氣出皺紋來,不然年紀輕輕就跟個老頭似的,小心弟妹不要你。”
作者有話要說: 《小劇場之京城傳聞》
從臘八那天開始,宣街居民經常能聽到有人踩自家屋頂的聲音。
顧浮:是我乾的
酒鋪酒冇了,當有人在架子上留了酒錢。
顧浮:還是我
騙子被人扔水裡,冇掙紮就沉底,還不見了蹤影。
司涯:我我我,我水可好了我跟你說。
——
照例兩百個紅包!我就不信我會一直卡在八點(叉腰
——
謝謝水月久安,鯉海2333,子青的地雷!
謝謝渣喵的地雷和手榴彈!
你們=3=
猜你喜歡
-
完結540 章
醫品庶女代嫁妃
中西醫學博士穿越成宰相府庶出五小姐,憑藉著前世所學的武功和醫術,懲治嫡出姐姐,鬥倒嫡母,本以爲一切都做得神不知鬼不覺,卻早已被某個腹黑深沉的傢伙所看透。既然如此,那不妨一起聯手,在這個陰謀環繞暗殺遍地的世界裡,我助你成就偉業,你護我世世生生!
97.3萬字8 169884 -
完結177 章

重生之賢妻難為
上一世,她是將軍府的正室夫人,卻獨守空房半生,最後落得個被休棄的恥辱。直到她年過四十遇見了他,一見鍾情後,才發現遇他為時已晚。 今世,上天待她不薄,重生那日,她便發誓,此生此世必要與他攜手一世,為他傾盡一生。
39.6萬字5 7733 -
完結157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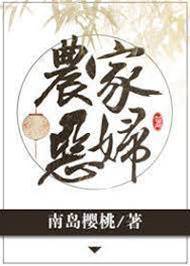
農家惡婦
何娇杏貌若春花,偏是十里八乡出了名的恶女,一把怪力,堪比耕牛。男人家眼馋她的多,有胆去碰的一个没有。 别家姑娘打从十四五岁就有人上门说亲,她单到十八才等来个媒人,说的是河对面程来喜家三儿子——程家兴。 程家兴在周围这片也是名人。 生得一副俊模样,结果好吃懒做,是个闲能上山打鸟下河摸鱼的乡下混混。
48.4萬字8 6705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