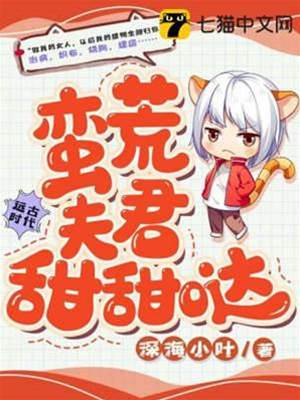《替嫁以后》 第63章
為了兒子的事,洪夫人的火氣遲遲下不去,二房那邊幾乎到了人人自危的地步,方伯爺也好不到哪里去,他比洪夫人強一點的地方就是沒怎麼尋下人出氣,但是焦躁得連家都不愿意呆了,天天早出晚歸。
他協管的選秀那攤子事已到了最后請皇帝過目的階段,照理該清閑下來了,還總在外面,不知忙些什麼。
方寒霄為此想法跟替他牽馬的小廝打聽了一下,方伯爺倒沒走,天天不是去禮部,就是去承恩公府,只在這兩個地方打轉。
那他的目的就比較明確了:如方老伯爺警告他的,摻和這種事真的沒多大用,再下勤力,事完了也就完了,不會因為這樣得到什麼功績封。
方伯爺大概是此時才意識到了方老伯爺說得沒錯,好容易混到手的差事不到幾個月就要沒了,他不甘心又個空頭伯爺,抓住最后的機會往里下功夫。
下得怎麼樣,方寒霄暫不知道,數日一晃而過,他該赴隆昌侯府賀壽去了。
隆昌侯府的岑老侯爺與方老伯爺是一個輩分,做的是人生七十古來稀的大壽,隆昌侯府為了沖淡先前被參的晦氣,著意往大了辦,把消息盡量廣地散播了出去。
八月十二正日子這一天,朱紫衫盈門,差不多層級的勛爵人家全到場了,有些關系遠一點的,人不來禮也要到,禮單源源不絕地送進來,在堂前唱禮的先生念得嗓子都嘶啞了,換一個又接著念。
打眼去,一派鼎盛興榮的氣象。
岑老侯爺這麼大把年歲,人其實已經有點糊涂,來給他祝壽的這些人,他基本上沒見幾個,不過不妨礙人們喜氣洋洋地來,因為所謂祝壽,祝的是岑老侯爺的壽不錯,敬的實際上是隆昌侯的總兵要職。
Advertisement
隆昌侯現在任上回不來,岑老侯爺又老糊涂了,在前面擔迎接賓客重任的,是現任世子岑永春。
他今日直忙了個腳不沾地。
因為太忙了,有些事他就管不到那麼周全,比如說,把徐尚宣的座位給安排錯了。
徐尚宣本來不想來,但惜月還耗在選秀里沒回家,徐大老爺怕和徐大太太吵架,仍舊躲得不見影子,徐大太太拿丈夫沒有辦法,只好強著兒子去給兒撐一撐場面。
這樣的好日子,徐家作為姻親,只搞個禮到人不到是說不過去的。
徐尚宣被嘮叨不過,只好來了。
他是岑永春的大舅子,這麼近的關系,照理說錯誰的也不該錯他,可偏偏吧,岑永春不只他一個大舅子。
月是續弦,在前面的原配也是有兄弟的,三個。
岑老侯爺這回做壽,原配家的舅爺們十分捧場,全來了。
事前沒有說會來得這麼齊全,人家三兄弟,也不能把人拆開了坐,引路的小廝措手不及,跑去問岑永春,岑永春忙得滿頭汗,不耐煩地道:“那就讓他們一起坐得了!”
小廝道:“舅爺們要一起坐,那一桌就有別人坐不下了——”
“看那桌誰還沒來,等來了就引到旁邊去,還能缺席面不,這點小事也要來問爺!”
小廝聽他口氣不好,答應一聲,忙跑了。
像這樣親眷關系的通常會安排得靠近一些,位置也會好一點,舅爺們那桌被下來一個,這一個也是岑家親戚,論關系雖不如舅爺們近,也不能隨便慢待,小廝不敢再去討岑永春的煩,自己費腦筋想著,好容易找個差不多的位置把他安了,不過這麼一來,那一桌又被下來一個,這麼繞來繞去,兩三過去把徐尚宣的位置占了。
Advertisement
這有一點怪徐尚宣自己,他不愿來,到得就晚,不過畢竟沒有遲到,還是在開席前到了,他和隆昌侯府來往的這些人家本來不,送過禮單說完吉祥話,進廳匆匆坐下來時,也沒意識到有什麼問題。
他覺得坐他對面有個青年有一點眼,似乎難得是他認識的,還盯著人家多看了兩眼。
但想不起來是誰,只覺得他生得是真不錯。
不由又看了兩眼。
那青年注意到他的目了,向他笑了笑,拱了拱手,但沒說話。
徐尚宣見他不語,覺得他們應該是不認識,他總盯人看也失禮,倉促地回了個笑,忙把目移開來了。
然后他東看西看,別桌都在寒暄著,他捎帶著也聽了一耳朵。
聽著聽著,他覺出不對來了。
原配家三舅爺那桌尤其熱鬧,三兄弟就是說不完的話了,與同桌的對談也是很稔的樣子,稱呼都是這兄那弟叔伯侄兒的,隔著一段距離都能聽清,周圍兩桌言語中也很悉,而他們這里對比之下就顯得冷清,不是說同桌誰和誰有矛盾,就是都不太,關系不近,說話間自然要客氣生疏不。
徐尚宣遲鈍地意識到自己被慢待了。
他按理應該是算到親眷那里去的,排不上首席,次席總該有他,再不濟,原配續弦兩家人不好相見,那再旁邊那桌總該著他吧?
結果把他當一般客人到這里來了。
徐尚宣原不是很在乎俗禮的人,月這門親事要是他喜歡的,那他作為親眷不是不能諒一點,坐哪都是坐,無所謂,但他先頭印象就不好,還被來了這麼一出,登時火就上來了。
捋袖子就出去找岑永春算賬。
他回來也有一陣子了,岑永春還沒有去見過他,雖然他只是大舅子,不算長輩,但兩樣疊加起來,要訓一頓岑永春也是夠理由的。
Advertisement
花廳外有小廝,他抓住一個就問:“你們那世子爺呢?”
今日來人太多了,小廝不認識他,茫然道:“還在外面迎客呢。”
徐尚宣虎虎生風就往外走。
這回再走出去幾步,被一個人從后面拉住了。
勁還大,他掙一下沒掙掉,只好轉頭。一看,正是席上他覺得眼的那個青年。
徐尚宣以為自己滿臉惱怒被人看出來了,他是岑家親眷來勸架的,揚著頭道:“你管閑事啊,跟你沒關系。”
青年收回手,搖搖頭,虛空里給他劃了個“方”字。
這字筆畫,劃在半空里徐尚宣也認出來了,但他生著氣,一時沒明白,只覺得這青年臉長得不錯,腦子是不是有問題?
瞎比劃什麼,什麼方,他還圓呢——?!
他忽然反應了過來!
方寒霄很溫和地和他笑了笑,又拱拱手。
徐尚宣滿腔的氣瞬間全泄掉了,腰桿都不覺要矮一截。
無它,心虛使然。
他妹子干出那種事,他現在見到苦主,哪里氣得起來呢——怪不得他還看人眼,五年前他們可不是見過。
“原來是、是妹婿啊。”
徐尚宣說話都打磕,心里很不孝地把徐大太太埋怨了一頓,真嫌人家,不如直接退婚,非把三妹妹又塞給他,別別扭扭地還要做這個親戚,真是想得出來。
他心里同時也訝異,因為沒料到方寒霄會愿意踏足隆昌侯府,所以席上看他眼,偏偏沒想起他來。
方寒霄比他自然多了,閑庭信步般往外走了兩步。
徐尚宣下意識就跟上去了,他以為方寒霄有話——或者是有賬要跟他算,到了更苦的苦主,他也不記得自己被慢待那點事了。
但跟了一會他發現,方寒霄沒話跟他說,也沒方向,好像就是隨便出來走一走。
Advertisement
無論多麼豪闊的宅院,前庭后院這個基本格局是不會變的,他們只在二門外的前庭這一片地方轉悠,像是在屋里坐得悶了,出來氣似的,沿途見的下人們都沒有阻攔。
只有轉悠到一個地方的時候,門前有明確的守門小廝,站姿很筆,方寒霄遙遙看了一眼,沒有靠近。
那應該是隆昌侯的書房。
這是他第二次來隆昌侯府,上一次來時是晚上,不好走,也看不清楚,這一次,他才大致確定了外院各的布局。
從他返京開始,他冷眼旁觀月高攀,與岑永春虛與委蛇,最終為的,就是在不引起隆昌侯警覺而進隆昌侯府的這個機會——或者說,這些機會。
因為他不能保證一次就能找到他要找的東西。
隆昌侯的那樣東西如果真的如他所推測的那樣藏在京中,一定十分蔽,對于自己的命門,那是怎麼保護也不為過的。
他返京真正的任務,就是找到這樣東西,證死隆昌侯——不能翻的那種,如之前徐二老爺那種小打小鬧不夠,那可能拉下隆昌侯,但無法一并將潞王打殘,砍斷他向儲位的手。
所以,他給徐二老爺出了主意,讓他去找徐大老爺鬧,通過談判的方式解除了隆昌侯的危機。
他當然不是潞王一伙的,當時這麼做一則是不能讓總兵重回方伯爺手里,二則他并不怕隆昌侯倚漕運之繼續資助潞王,金錢越是源源不斷地流到潞王手里,他能找到的證據就越實,越能讓潞藩遠離儲位。
不過,他也不能讓潞王在這過程里太得意了,在他找到證據之前就把儲位撈到手里,該打他的時候,還要他一下。
他因此用了一條線上的于星誠。
于星誠的傾向深藏于心,外人不知,但他作為朝廷員,不管站不站隊,都算是明面上的人,在博弈階段,他可以提供的幫助有限,許多事,仍是方寒霄一人來。
與于星誠不一樣的是,方寒霄的啞廢是他最好的障眼法,但同時,他要藏好自己,就要盡量地借助他背后之人的力量,只利用自所有能利用的東西。
大約是走在隆昌侯府的土地上,方寒霄的思維前所未有地清晰,他看似隨意走著,其實眼睛沒空,腦子里也沒閑著,將自己至今以來的所為都過了一遍。
徐尚宣什麼也不知道,傻呵呵地被他溜了一圈,開始不敢說話,漸漸憋不住,終于主想搭個腔:“那個,妹夫啊。”
方寒霄回過神,轉臉看他。
他趁勢跟著徐尚宣出來,是覺著跟他一起蔽更強,他要一個人在這轉悠,上眼尖的說不準能看出他在窺視,兩個人一道,就好像出來聊事一樣,一般識趣的下人也不會靠過來。
徐尚宣頓了片刻,想找個合適的說辭,失敗了沒找著,索一拍掌,直接道:“你是不是看岑家那小子不痛快?別跟這撒悶氣了,走,你看我去罵他一頓,揍他兩掌也行,他要還手,我們就跑,這勞什子壽酒不吃也罷!”
他自以為是明了了方寒霄轉圈的意思——不管他為什麼來的,他在這里心肯定不好,所以不愿意坐屋里看人家的富貴熱鬧,寧可出來瞎轉清靜清靜了。
方寒霄:……
徐尚宣是真打算這麼干的,他子莽,不怕得罪岑永春害妹妹吃苦頭,反正妹妹原來日子也不好過,揍岑永春一頓,下下他勛貴子弟的驕氣,他對妹妹也許倒能客氣些。
方寒霄搖頭,他自己是習武之人,看得出來徐尚宣腳步沉重,下盤虛浮,所有的本領恐怕就只有一膀子力氣,這樣張口要在人家的地盤上去揍人,他真是服了。
徐尚宣殷勤地邀請他:“你不用手,你看我來就行。”
方寒霄后退,再搖頭,見徐尚宣居然還要來拉他,轉頭想尋個木枝條之類的告訴他不必這麼干,這一張,無意間便瞥見隆昌侯那書房附近多了個人在走。
這本來不奇怪,今日府里來客眾多,別人要是悶了,出來走走也很尋常。
奇的是,這個人他認得并算。
是方寒誠。
方寒霄瞇起了眼——他不知道方寒誠也來了,他們不是一道出的門,位置可能也沒安排在一起,起碼他在的那個廳里,沒看見有他。
方寒誠來便來了,隆昌侯府要是給方伯爺下了帖子,方伯爺自己不想來,派兒子來做代表也說得過去,可是他卻在這個位置出現——
難道一直以來,都是他燈下黑,忽視了這個堂弟?
**
稍早一些時候的隆昌侯府院之中,瑩月在眷席上,也到了人。
不是孟氏,薛嘉言這次沒來,他上次都是湊熱鬧的,本和隆昌侯府并沒有這個。他不來,孟氏更沒有必要來了。
不過,瑩月見的這個人也是薛家的人。
大姑薛珍兒。
薛珍兒與不在一個席面上,兩人各坐臨近著的兩張團桌,恰是個相背而對的席位,這距離不是同桌,勝似同桌。
瑩月從坐下起,就覺得有如芒刺在背,后面時時有冷箭過來,得背上涼颼颼的。
背對著薛珍兒,薛珍兒也是背對著,這麼不擰過脖子來瞪,不累呀。
瑩月心中小小腹誹,對于別人的惡意本該心生畏怯,但不知怎的,薛珍兒這麼對,不但不怕,還不知打哪生出很抖擻的神來。
要吵架,就吵,哼。
猜你喜歡
-
完結66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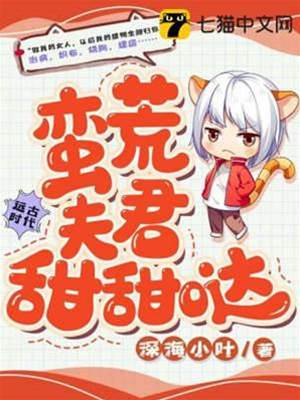
蠻荒夫君甜甜噠
薛瑤一覺醒來竟穿越到了遠古時代,面前還有一群穿著獸皮的原始人想要偷她! 還好有個帥野人突然出來救了她,還要把她帶回家。 帥野人:“做我的女人,以后我的獵物全部歸你!” 薛瑤:“……”她能拒絕嗎? 本以為原始生活會很凄涼,沒想到野人老公每天都對她寵寵寵! 治病,織布,燒陶,建房…… 薛瑤不但收獲了一個帥氣的野人老公,一不小心還創造了原始部落的新文明。
117.6萬字8 36849 -
完結385 章

朱門繼室
一朝穿越,竟成官家嫡女,本想安安穩穩清靜度日,卻偏偏被嫁給了那名據說八字過硬的朱家下一代家主為繼室!名門望族是非多,一顰一笑,皆是算計!成為當家長媳,管教穿越兒子,教育機靈女兒,收拾蛇蠍姨娘,降服冷漠丈夫,保地位,生包子,一個都不能少!
109.4萬字8 30609 -
完結1433 章

醫妃張狂:厲王,請上榻
前腳被渣男退婚,厲王后腳就把聘禮抬入府了,莫名其妙成了厲王妃,新婚夜就被扔到一群男人堆中,差點清白不保,月如霜表示很憤怒。老虎不發威,當她是病貓?整不死你丫的!可當某一天,厲王看上邪醫……月如霜一襲男裝,面具遮面:夜墨琛,本邪醫已經六十高齡…
239.2萬字8 77423 -
完結247 章
命定太子妃
死前巨大的不甘和執念讓柳望舒重生,只是重生的節點不太妙,只差最後一步就要成為晉王妃,走上和前世一樣的路。 柳望舒發揮主觀能動性,竭力避免前世的結局,也想將前世混沌的人生過清楚。 但是過著過著,咦,怎麼又成太子妃了?
15.6萬字8 9073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