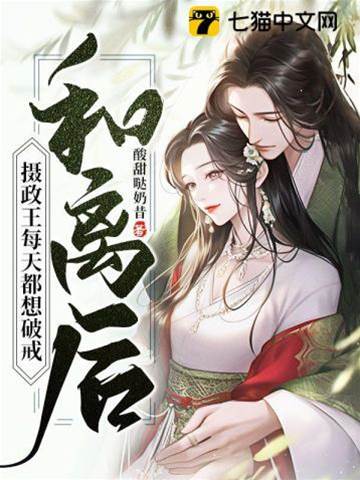《攻玉》 第129章
庭中只有他二人,滕玉意笑瞇瞇地說:“在下名號甚多。在外人稱‘王公子’,在家有個小字‘阿玉’,捉妖時另有道號,‘無為’二字便是我師兄賜的。”
藺承佑笑著點點頭:“無為,無為,‘道常無為而無不為,萬將自化’,有了這道號,剛好幫你這多災多難的小道士一。有師兄若此,無為道長本事不會差吧?”
“馬馬虎虎,目前尚有一樣本事遠不及我師兄。”
“你且說來聽聽。”
“臉皮。我就沒見過比我師兄更喜歡夸自己的人,說起臉皮厚,他算是天下第一。”
藺承佑嘖了一聲:“我的好無為,孺子可教也。知道自己尚有不足之就好,今日打算跟師兄出門長長本事麼。”
“東西都備妥了,特來延請師兄。”說話間已走到紅梅樹下,含笑低眉著藺承佑。
“要我帶你出門長見識倒是。”藺承佑不肯,“就是地上雪未消,我走路易,待會得一直有人扶著我才行。”
這樣厚臉皮的話也就藺承佑能說出口。滕玉意看看四周,王府的仆從甚懂規矩,大約知道小主人不喜被打擾,早就遠遠地躲開了。
偌大一座庭院,一時只能聽見微風掃過紅梅枝頭的輕響。
滕玉意扶著藺承佑起,扶是一定要扶的,但兩人畢竟尚未完婚,假如就這樣大剌剌扶著藺承佑四走,多有些不妥。
踟躕間,滕玉意看向藺承佑的袖,心念忽一:“那我得跟師兄借樣東西。”
藺承佑從袖中抖出鎖魂豸:“這個?”
滕玉意掰開藺承佑的手讓他握銀鏈,自己則穩穩牽住另一頭,然后叮囑長蟲:“你好好的,千萬別隨便松開你主人。”
Advertisement
長蟲很不愿意被滕玉意支使,不過還是慢騰騰纏住了藺承佑的手。
滕玉意檢視一番確定足夠穩固,這才牽著藺承佑往前走:“有我在,絕不會讓你磕著著。”
藺承佑笑靨愈發深,就那樣不不慢跟在滕玉意后頭。
長長的銀鏈,一頭在滕玉意手里,一頭在藺承佑手里,相距不算近,卻又跬步不離。
每走過一株花樹,都會有花瓣紛紛落到兩個人的頭上和上,形如春雨,若虹霓,再往前走,又有杏花初綻,花瓣隨風回旋,活潑潑地追逐兩人的影而去,遠看好似一幅舒卷絢爛的畫。
走著走著,畫中的某個人笑著開了口:“老回頭看我做什麼?”
藺承佑雖然看不見,但能聽到滕玉意回頭時鬢邊首飾搖晃的聲響。
滕玉意正用目仔細確認藺承佑腳下是否有石子,那次在被耐重擄到地宮,藺承佑就是用鎖魂豸牽著走出地宮。
“你想想那回在玉貞冠觀我和你在地宮里是何景,就知道我為何會如此了。”
藺承佑慢悠悠道:“我只記得你生怕我把你弄丟了,為了纏得些把鎖魂豸欺負得哇哇直。滕玉意,你是不是打小就霸道?”
滕玉意鼻哼一聲:“不對,你再想想,當時在地宮你是如何待我的。”
藺承佑笑著不說話了。
滕玉意一默,忍不住再次回頭瞥他,這一眼看得有又有緒,目的,卻是無比,當時藺承佑就像現在這樣,每走幾步就會回頭確認是不是還在自己后。
打從相識那日起,他要麼口口聲聲嫌煩,要麼專程跟作對,但一顆心早就系到了的上。
心里正是又酸又甜。藺承佑笑著提醒:“當心自己腳下,別我沒摔著,你自己先摔著了。”
Advertisement
卻見王妃邊的管事嬤嬤采蘋找來了。
采蘋看到兩人這景,只一訝,旋即又笑了。
眼盲這幾月,大郎臉上從未開過笑臉不說,更從不肯讓人攙扶自己。
今日這景,讓人發自心想笑。
虧這兩個孩子能想出這法子。
藺承佑側耳聽了聽,對滕玉意道:“這是阿娘邊的采蘋嬤嬤。“
滕玉意忙恭恭敬敬斂衽。
采蘋細細打量滕玉意,笑得合不攏:“王妃問大郎和滕娘子是不是要出門。早膳備在花廳,叮囑你們用過早膳再走。”
今早滕玉意急著來找藺承佑,的確沒來得及用早膳。
藺承佑道:“突然想吃點心了,有紅梅糕嗎?”
采蘋錯愕,世子可向來不吃點心,不過還是笑著說:“有有有。”
藺承佑又道:“替我和阿玉同阿娘說一聲,今日我們出門查案,中午估計回不來,府里不必等我們用膳。”
到了花廳,滿屋都是孩子,兩人坐下同大伙熱熱鬧鬧吃了一頓早膳。
膳畢,滕玉意到阿芝房里換上道袍,阿芝繞著滕玉意走來走去,一會兒滕玉意臉上的易容面,一會兒看上的裝束,越看越覺得新奇有趣,纏著自己的哥哥,鬧著要跟他們出門辦案,末了還是王妃以檢查兒新學的劍法為名,讓人把阿芝帶到上房去了。
喜鵲巷比前晚喧嚷許多,巷子里的住戶心有余悸,三三兩兩聚作一堆討論昨晚新發生的命案。
衙役們忙著驅散人群。
昨晚被殺的人名王大春,并非喜鵲巷的居民,而是一名打更的更夫,大約是四更天被人殺害的,第一個發現陳大春尸首的是附近巡邏的武侯。
王大春的死狀同上回被人謀害的劉翁一樣,也是首異。
Advertisement
巧的是,王大春就橫尸在劉翁的宅子外。
衙役們找了一大圈未找到王大春的尸首,對陳司直道:“王大春今年六十有五,也是一位鰥夫。原先本在義寧坊打更,前些日子才調到通化坊。事發時附近鄰居并未聽到呼喊聲,應該是一擊致命,看樣子,兇手昨晚曾潛劉翁的宅子,巧王大春來此打更時撞見兇手,兇手為滅口便將其殺了。”
陳司直正要接話,忽聽那邊有人道:“錯。王大春不是剛巧路過,而是有備而來。”
眾人驚訝回頭,不知何時多了兩個人,藺承佑半蹲在跡噴灑之,用手指輕輕著什麼。他的邊,蹲著個面生的小道士,小道士一邊仔細察看地面,一邊對藺承佑形容跡的形狀和范圍。
陳司直等人忙迎上去:“藺評事。”
藺承佑笑道:“劉翁的案子本就有許多蹊蹺之,聽說今早又出了人命案,所以我過來轉轉。陳司直,王大春的傷口也跟劉翁一樣齊整麼?”
眾人小心翼翼往地上一覷,沒提防藺承佑腳下竟未到殘,先是一愣,隨即意識到是藺承佑邊的小道士起了作用,再看滕玉意時,面上便多了些好奇。
“陳司直?”
“哦。”陳司直回過神,“沒錯,而且王大春的頭顱也尚未找著。藺評事,你因何說王大春是有備而來?”
藺承佑用手在面前虛虛畫了一大圈:“當時是四更天,前不久此宅才有人被殺害,按照常理,王大春打完更點個卯便會匆匆離去,但經過仔細比對,大門有一串干凈的腳印,大小形狀正與王大春相符,怪就怪在并未沾染跡,可見是王大春遇害前留下的。但此宅不僅每晚都上鎖,還會上大理寺的封條,若不翻墻進去,本不可能在里頭留下腳印。這說明王大春昨晚潛此宅,結果剛巧與兇手撞上,王大春手不敵兇手,忙又翻墻逃出,剛跑幾步就被兇手取了命。”
Advertisement
陳司直順著這話宅里宅外一檢視,果然全都對上了,先前那些藐視和不耐煩的神,終于徹底收起來了,他忙堆起笑容道:“藺評事斷案如神。陳某萬想不到一個更夫竟有這麼多貓膩。”
滕玉意在藺承佑后打量這位大理寺員,看人時不看皮相,專門往人的骨子里瞧,陳司直三十多歲,面上看著也是斯斯文文的,但他上既沒有嚴司直辦案時的那份耐心,目也遠不及嚴司直清正。
這樣一對比,愈發凸顯嚴司直的可貴。
滕玉意憾嘆氣,是人非,藺承佑失去的何止是一雙眼睛,還失去了一向最信賴的同僚和搭檔。都能想象當初藺承佑得知嚴司直的死訊時有多難過。
“依我看,他們三人過去可能是相識。”藺承佑道,“王大春原本在義寧坊打更,前不久才設法調到此,說不定他本就是沖著劉翁來的,這也與兇手的意圖不謀而合。三人或是訌,或是搶奪同一件東西,兇手不單行兇,事后還將二人的頭顱帶走,這樣做多半是怕我們通過冤魂之口問出他是誰。頭顱被割下,意味著口舌的靈竅都不在了,即便化為厲鬼也無法言明自己是被誰殺害的。除此之外,兇手過去應該不只殺過一個人,昨晚我來此時,發現巷中有游魂,假如當時兇手在附近窺伺,說明他上殺孽很重,無論走到何,都有冤魂跟著他。”
陳司直疑地說:“那依照藺評事看,兇手和王大春究竟在找什麼?劉翁生前只是個賣炭翁,照理是沒有值錢家私的。”
“東西值不值錢,得找出來看了才知道。”藺承佑思索著說,“這兩樁案子最大的疑點就是兇。究竟什麼樣的利能那麼快割下一個人的頭顱,邊緣整整齊齊不說,劉翁和王大春遇害前甚至沒來得及呼救,這種手法,倒教我想起了一種悉的暗。”
滕玉意心口一跳,腦海中突然浮現那件銀暗。
盡管已經得知幕后主家是淳安郡王,但淳安郡王只說這銀武是當初皓月散人花重金買來的。他們圖它輕便好用,且能殺人于無形,至于皓月散人最初是從何弄來的,一直是個謎。
記得那回大伙在彩樓討論對付尸邪的法子時,曾說起劍南道的軍士們在南詔國遇到過尸王,軍營里正是利用一琴弦似的武鋸下了尸王的獠牙才得以驅邪。
會不會這種殺人暗最初是從南詔國傳到中原來的。
“對了陳司直,昨日下午我來時,曾讓董衙役去長安縣討要劉翁的戶籍,現在可取回來了?”
陳司直噢了一聲:“找著了。原來劉翁并非長安人士,十幾年前才從劍南道遷來長安,他過去曾在專程在南詔國和劍南道之間往返,據說靠販貨為生,至于賣的什麼貨,那就不大清楚了。”
滕玉意一震,莫非真與南詔國有關。
“不如順道一起查查王大春的來歷。”藺承佑道,“他來長安做更夫前,說不定也在劍南道和南詔國待過。去歲坊間曾暗中流行過一種昂貴的銀武,大約是從南詔國的巫蠱地傳來的,假如劉翁和王大春都是被這種暗所害,我大致能猜到兇手的目的是什麼了。”
記得查辦皇叔和皓月散人一案時,他曾打聽過這種銀武在坊間售賣的價錢,以莊穆為例,此人手里的銀一價萬錢,彩樓的老板彭玉桂家資鉅萬,也僅購買了一做防用。
聽說有不江湖人士想得到這種武,只不過因為朝廷打,不敢明目張膽易。
可惜先后出了彭震和皇叔的事,對方有如驚弓之鳥,嚇得再也不敢冒頭了。
看來風聲一過,這幫人又蠢蠢了。
又聽聞,南詔國有偏僻的巫蠱之地,當地百姓因為常年與世隔絕,歷來稟純良,為了獲取食,百姓們常將本地的一些珍異之以賤價賣給中原人士和胡人。
這種銀暗說不定就源自南詔國的某深谷里的礦池,如果一個人掌握了制作這種銀暗的獨門笈,只需悄悄售賣個兩三年便可富甲一方。
陳司直也聽說過去歲那幾樁案子,忖度著說:“照這樣說,劉翁、兇手、王大春很可能共同做過販賣銀暗的營生。但不知怎麼回事,三人鬧掰了。兇手和王大春以為劉翁私藏了剩余的貨,所以他們倆一個殺了劉翁之后到翻找,一個專程跑到喜鵲巷打更。兇手甚至冒著被發現的危險再次潛回劉宅。”
猜你喜歡
-
完結620 章
秀色滿園
成爲地位卑下的掃地丫鬟,錦繡冷靜的接受了現實。她努力學習大宅門的生存技能,從衆多丫鬟中脫穎而出,一步步的升爲一等丫鬟。丫鬟間的明爭暗鬥,小姐們之間的勾心鬥角,少爺們的別有用意,老爺太太的處心積慮,錦繡左右逢源,努力活出自己想要的生活。到了適婚年齡,各種難題紛至沓來。錦繡面臨兩難抉擇……尊嚴和愛情,到底哪個更重要?---------------
157.9萬字8 43123 -
連載886 章

穿越女尊農門妻主不好當
她本是現代女神醫,一手金針起死人肉白骨,卻意外穿越到一個女尊王朝。一貧如洗的家,還有如仇人一般夫郎們,水玲瓏表麵笑嘻嘻,心裡。沒辦法,隻能賺錢養家,順便護夫郎。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
82.4萬字8 21764 -
完結2595 章

神醫毒妃腹黑寶寶
穿越當晚,新婚洞房。 雲綰寧被墨曄那狗男人凌虐的死去活來,后被拋之後院,禁足整整四年! 本以為,這四年她過的很艱難。 肯定變成了個又老又丑的黃臉婆! 但看著她身子飽滿勾人、肌膚雪白、揮金如土,身邊還多了個跟他一模一樣的肉圓子……墨曄雙眼一熱,「你哪來的錢! 哪來的娃?」 肉圓子瞪他:「離我娘親遠一點」 當年之事徹查后,墨曄一臉真誠:「媳婦,我錯了! 兒子,爹爹錯了」
470.9萬字8.18 60927 -
完結199 章

癡傻王妃太難追
在丞相府這讓眼里,她就是那個最大污點,丞相府嫡女未婚生下的粱羽寧,從小受盡侮辱,終死在了丞相府,一朝穿越,心理醫生重生,她看盡丞相府的那點把戲,讓她們自相殘殺后笑著退場,大仇得到! 可在小小的丞相府能退場,在感情的漩渦越來越深之時,她能否安然離開? 一場大火,翩翩佳公子,變成了殘忍嗜血的戰神,接連死了八位王妃,當真是自殺,還是人為?
45萬字8 10423 -
完結567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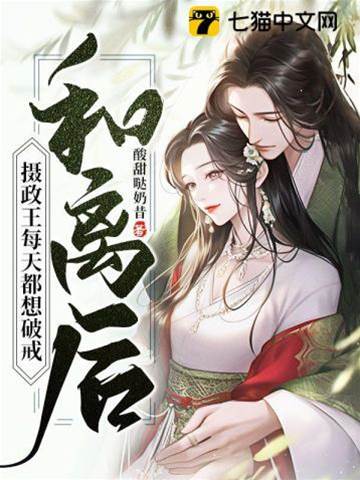
和離後攝政王每天都想破戒
葉芳一朝穿越,竟然穿成了一個醜得不能再醜的小可憐?無才,無貌,無權,無勢。新婚之夜,更是被夫君聯合郡主逼著喝下絕子藥,自降為妾?笑話,她葉芳菲是什麼都沒有,可是偏偏有錢,你能奈我如何?渣男貪圖她嫁妝,不肯和離,那她不介意讓渣男身敗名裂!郡主仗著身份欺辱她,高高在上,那她就把她拉下神壇!眾人恥笑她麵容醜陋,然而等她再次露麵的時候,眾人皆驚!開醫館,揚美名,葉芳菲活的風生水起,隻是再回頭的時候,身邊竟然不知道何時多了一個拉著她手非要娶她的攝政王。
99.6萬字8 9486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