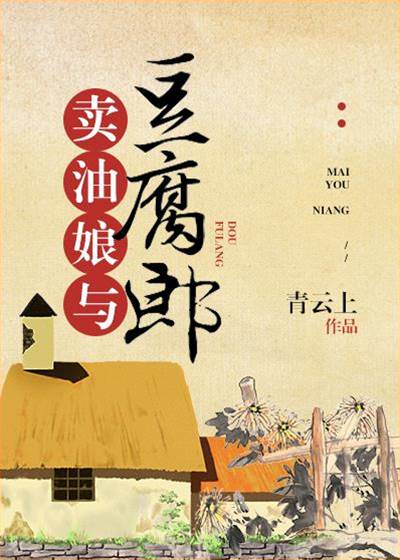《宦妃天下》 大漠孤雁終章
白珍送了一口氣,隨後看著手上的服發起愁來,正在此時,簾子忽然一掀,陳爽全副武裝地一臉凝重地走了進來:“珍姑娘,真於的人看樣子找不到隼剎可汗的蹤跡,如今已經往我們這裡來了。”
白珍一頓,隨後點點頭,看向隼剎,又看向陳爽,隨後立刻拿定了主意,幾步上前,一把拉住了陳爽,隨後附耳在他耳邊嘀咕起來,。
陳爽越聽,眼珠子瞪得越大,隨後錯愕地看向隼剎,有點口吃地道:“你是說……但是……。”
白珍搖搖頭,一把拽住陳爽,咬牙道:“沒有但是了,就這樣!”
隼剎忽然睜開眸子,警惕地看向白珍,他忽然有點不太好的預。
……
——老子是分界線——
“你們到底要怎麼樣,這是我們送嫁的營地,已經答應讓你們進去搜了,如今沒有搜到人,你們還想怎麼地!”
“這裡就算是送嫁的營地,但是這裡卻是我們赫赫的國土!”
“你們別欺人太甚。”
天朝送嫁隊伍的營地外,如今已經是裡三層外三層的圍滿了赫赫人,他們臉上都帶著濃濃的暴的氣息,手上的刀子都沾染了,腥之味和燒焦的味道彌散在空氣裡,和著濃黑的夜一樣讓人窒息。
一直冷眼看著的副將齊飛忽然站了出來,對著那爲首的赫赫人冷聲道:“都拉爾,你們舍於部和真於可汗原本都是姻親,我能理解你們爲了真於可汗復仇的心切,但是別忘了,我們也算是這沙漠上的老人了,既然已經答應讓你們進營地去搜查,而且你們也沒有搜出什麼來,就別太過分,否則,我們死亡之海遲早會讓你們再一次試試有頭無發的滋味。”
Advertisement
他頓了頓,又道:“哦,不好意思,這一次很可能就是有發無頭了。”
這話一出,原本在領頭囂得最厲害,眼裡都是殘忍嗜殺意的男子瞬間看過來,一看清楚來人的模樣,已經是覺得眼,不由一僵,又聽得他話語,瞬間臉一青。
他爲領頭者當然是知道齊飛到底是在說什麼。
當年死亡之海里的惡鬼們出來‘獵野’,一向讓西域各國聞風喪膽,那些惡鬼們人雖然不多,但是手段了得,他們‘獵野’就是一種爲了證明年已經年的儀式,也是一種保持戰鬥力的方式。
‘獵野’的一種方式就是選擇一國的王公貴族,半夜潛伏進去將對方的頭剃,留下髮作爲戰利品——既然守護森嚴的王族的頭髮都能被不聲的取走,那麼於千軍萬馬之中取上將首級又有何做不到。
各國王公對此痛恨骨,但是就是沒有一個人能有辦法,再多的軍隊都沒有辦法進死亡之海,甚至抓住一個獵野的年。
但幸運的是,這些人人數不多,而且很沉默,出來得並不算多,非常神。
而留頭不留髮,每個沒割掉頭髮的人頭邊都會留下這麼一句話,而都拉爾就是曾經被獵野過的對象,那種可怕的覺到現在都讓他沒忘記過,如今一聽到陳飛的話,瞬間臉就是一白。
他方纔想起沒有錯,是聽說了死亡之海的惡鬼們不去了中原,而且……竟然那麼的巧合,居然就是在這裡遇上了!
都拉爾遲疑了片刻,和邊低聲說了些什麼,隨後,他一咬牙,冷聲用有些蹩腳的中原話繼續道:“我說了我們這些人都是拼死一搏,只爲復仇,所以我們只要找出隼剎,絕對不會爲難你們,所以我們只有一個要求!”
Advertisement
齊飛環冷冷地道:“你們要怎麼樣?”
都拉爾瞇起眼,目冷地落向那個最大的帳篷:“我要搜那個帳篷!”
那是他們唯一沒有進去過的帳篷。
齊飛一顰眉還沒有說話,一道音便了進來,地道:“那是送嫁的陳將軍的帳篷,只怕你們確實不太方便。”
都拉爾等人齊齊地看過去,便看見白珍正領著月彌和月珍走出來,都拉爾細長的眼睛裡閃過一貪婪的,迷迷打量著白珍幾個人,隨後出大黃牙一笑:“這就是我們的”閼氏“嗎,真是可惜啊,這麼麗的人,連侍都那麼麗。”
月裳和月彌兩個人出個厭惡的表,們忽然覺得原來怎麼看都不順眼的隼剎,如今想起來順眼了不。
都拉爾忽然語氣一轉,沉地道:“不過就算是死大神站在這裡,我們都要進去搜一搜,何況是一個小小的”閼氏“站在這裡!”
月裳瞬間臉上閃過怒,就要開口,卻被白珍按住了手腕,冷冷一笑:“既然如此,但是都拉爾大人如果什麼都沒有找到就不要怪我們的人不客氣了,我們這裡的送嫁的將們全部都來自死亡之海,雖然他們已經是朝廷的人了,但是我也只是一個沒有權利的小小縣主,所以如果他們被激怒了,我也無能爲力。”
這般威脅的話語讓都拉爾遲疑了片刻,還是一咬牙道:“我們要搜,如果沒有我們馬上走!”
他們必須找到隼剎,否則讓那個野狼王逃了,等待他們的絕對是大漠上無止境的追殺!
而唯一不怕隼剎的就是死亡之海的人,但是這一次他們都得罪了,卻也還要博一搏。
Advertisement
白珍挑眉:“好,請吧!”
隨後都拉爾立刻招呼人去搜。
在他前面剛剛進帳篷的人,忽然就一聲慘跌倒出了帳外:“啊!”
都拉爾等人瞬間張起來,看向帳篷,所有赫赫的叛軍都齊齊唰的一聲拔出了戰刀。
氣氛立刻張了起來。
都拉爾看了眼被用刀鞘砸暈的手下,警惕地用刀子挑開了簾子,隨後看到裡面的景,便立刻一下子漲紅了臉,但還是沒有放下簾子,而是一下子領著幾個人鑽進了簾子裡頭。
頓時,裡面響起了一聲子的尖:“啊——!”
衆人只覺得張又奇怪,只覺得似乎看見了陳爽赤著上站在牀邊,而他後的牀上還有一個妖嬈的異國人只穿著肚兜?
過了一會便聽見陳爽破口大罵:“都拉爾,格老子的,遲早有一天割了你的頭!”
隨後便是一陣七八糟什麼東西落地的聲音。
過了好一會,便見都拉爾等人一臉狼狽地從帳篷裡鑽出來。
他惡狠狠地看了眼白珍等人,毫沒有掩飾臉上的殺氣,他剛剛對邊的人使了眼,氣氛詭譎起來,所有赫赫人不但沒有撤退,都慢慢地拔出了刀,但是下一刻卻見白珍忽然擡頭看著月一笑:“啊,看樣子死亡之海的惡鬼們今日都要來這裡和親人們聚會呢。”
都拉爾一驚,立刻擡起頭,看向天空,果然看見天上不知道什麼掠過好幾只烏——那是惡鬼們圈養的寵。
他立刻低頭,臉變幻莫測,隨後森猙獰地瞪了白珍,轉就走:“抱歉!”
隨後一干赫赫叛軍便只能跟著他匆匆離開。
白珍終於鬆了一口氣,看向齊飛,齊飛看了看天上,嘆了一口氣:“這是把他們都詐走了,這些鳥還好放出的及時。”
Advertisement
鬼衛衆人們都鬆了一口氣,隨後陳爽也穿戴整齊走了出來,臉有些古怪,但是很快他就開始重新和安排佈置,準備先行按照原本撤退的路線離開。
畢竟這個時候只怕是很快要有一場圍剿戰了,剛纔赫赫叛軍只是一時間被嚇走而已,萬一一會子回來的話,會不好收拾了。
白珍看了看帳篷,想了想,還是沒有進去。
想,隼剎,需要一點時間調整下損的自尊和惡劣的心。
但是一刻鐘之後,正當所有人準備離開,而白珍準備進去出隼剎的時候,忽然營地外響起了一陣猛烈的廝殺聲,還有無數的馬蹄聲。
慘聲不斷地響起,四面八方,永無停歇,讓人心聽得發冷。
黑暗之中,彷彿有無數的鐵騎衝殺過來。
衆人瞬間又警惕了起來,但是還沒有來得及派出人去刺探,便看見有幾十騎攜著重重殺氣策馬向他們衝來。
陳爽瞬間擡手,正要下令埋伏的弓箭手箭,卻被白珍拍了拍肩頭,有些張地道:“等一下,陳大哥,你看下那個領頭穿長袍子的人,他是不是哈蘇大祭司?”
陳爽一愣,仔細一看,果然,那個馬上矮矮胖胖的頭,不是狡猾的哈蘇大祭司,又是誰。
哈蘇是隼剎的親信,如今在這裡出現是不是意味著……
果然,還沒有到帳篷,便見哈蘇大聲地興地嚷嚷著衝過來。
白珍忽然心中一轉過看向後,果然見著那大帳前已經站了一個人,靜靜地,高大的形,披著的披風被夜風掀起一角,還能看見下面一抹奇特的幽暗的嫣紅,正如他溼的線條分明臉龐,依然殘留的嫣紅金、披散到腰間的結著長辮子的發一樣。
與他的形與森冷孤傲的氣息格格不,又有一種奇特的契合。
“你……。”白珍一愣,在月下,覺得自己彷彿有一瞬間的錯覺,幾乎認不出他來。
隼剎金的眸子裡落在白珍的上時閃過一種奇特的幽,隨後又移開了目,看向哈蘇。
哈蘇俐落地跳下馬,領著一羣提刀的武士們衝到隼剎面前,齊齊跪下,隨後將手裡提著的頭顱放在了隼剎腳下。
“您沒事吧!”哈蘇張地上下打量著隼剎。
隼剎低頭看了眼地上的頭顱,譏誚地勾起了脣角:“我沒事。”
白珍看著那死不瞑目的頭顱,竟然是不久之前趾高氣揚的都拉爾,瞬間臉微微一變,再看向陳爽,和陳爽換了一個眼神,立刻明白了什麼。
隨後,隼剎也看向一邊的白珍,又看向一邊的陳爽,神從容地道:“本可汗和哈蘇大祭司早就知道了叛逆者的存在,只是不知道他們什麼時候會發起叛,所以這一次我讓哈蘇一直潛伏在外觀察,就爲了能將真於的殘部和叛者他們一網打盡,但是就像你們中原人說的兵行險招,所以如果沒有你們的幫助,我們也不可能順利完這一次的圍剿。”
白珍神冰涼地一笑:“是麼,我們還是小瞧了隼剎可汗,我還真以爲您險境。”隨後,就別開了臉,而一邊的月裳和月彌臉都不虞。
陳爽則微微顰眉,卻沒有說話。
哈蘇是個機靈的,看了看白珍的臉,隨後嘆了一聲:“白珍閼氏,您不要錯怪了可汗,我們佈置這一次的事很久了,只是一直都不知道他們到底什麼時候手,這一次,如果不是閼氏您機敏,可汗一定險境,結果如何倒是真的不一定。”
白珍脣角微微一抿,冰冷的神稍緩,還是沉默著沒有說話。
隼剎卻忽然走了過來,一彎腰,將白珍攔腰抱起,徑自大剌剌地就向外走去。
月裳一驚,立刻衝上去:“喂,你——!”
但是卻被陳爽一把拉住:“不要輕舉妄,赫赫大軍就在周圍,何況,白珍……早已下了決定的。”
月裳看了看陳爽,又看了看前面,果然沒有看見白珍在隼剎懷裡掙扎,瞬間有些茫然了,看向天空的冰冷的月。
一切,都已經不能再回頭了麼?
……
“你還可以選,看在你救了我這一次的機會上,我給你一個選擇,留下,或者離開,我不會派人追。”
幽暗的大帳裡,一盞燭幽幽地閃爍著,勾勒出男子健碩修長的影,他單膝跪在牀前,姿態像一頭狼,俯視著自己的獵,冰涼的金眸子裡此刻閃著幽幽的芒。
猜你喜歡
-
完結177 章

攻玉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對于成王世子藺承佑而言,滕玉意便是他攻不下的那塊“玉”。天之驕子作死追妻路。
99.9萬字8.18 23286 -
完結1403 章

空間農女:家有悍妻來旺夫
啥?被個收音機砸穿越了?還好上天有眼,給她一個神奇空間!啥?沒爹沒孃還窮的吃不上飯?想啥呢,擼起袖子就是乾!養家,賺錢,虐渣,鬥極品,順便收了同為“後來者”的..
250.7萬字8.18 199431 -
完結512 章
侯門嬌女狠角色
易阳侯府的嫡小姐疯了!原本温婉端庄的人,一夜之间判若两人,狠厉至极,嚣张绢狂!一把火烧了半个寺庙,封闭府门三日,赶走大半奴仆,夺了掌家令牌,更是以一人之力捣了阳城最大的青龙帮!关键人家背后还有端庄雅正,清冷凉薄的景逸王撑腰!“外面现在可传,我闯了你们皇家的菜园子,还偷了最根正苗红的一颗白菜,你就一点不恼?”他点头,“恼。”(恼的是我家菜园子里的白菜太多了。)
157.8萬字8 68998 -
完結145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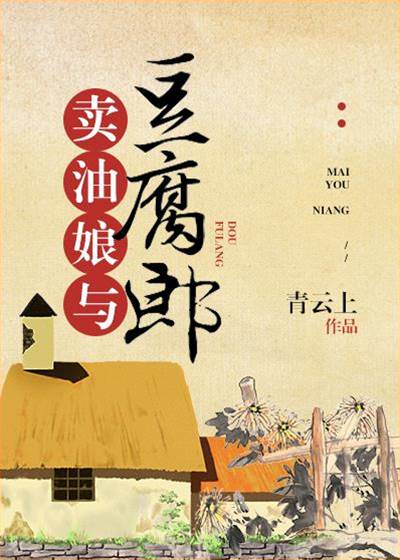
賣油娘與豆腐郎
每天早上6點準時更新,風雨無阻~ 失父之後,梅香不再整日龜縮在家做飯繡花,開始下田地、管油坊,打退了許多想來占便宜的豺狼。 威名大盛的梅香,從此活得痛快敞亮,也因此被長舌婦們說三道四,最終和未婚夫大路朝天、各走一邊。 豆腐郎黃茂林搓搓手,梅香,嫁給我好不好,我就缺個你這樣潑辣能幹的婆娘,跟我一起防備我那一肚子心眼的後娘。 梅香:我才不要天天跟你吃豆腐渣! 茂林:不不不
77.7萬字8 13071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