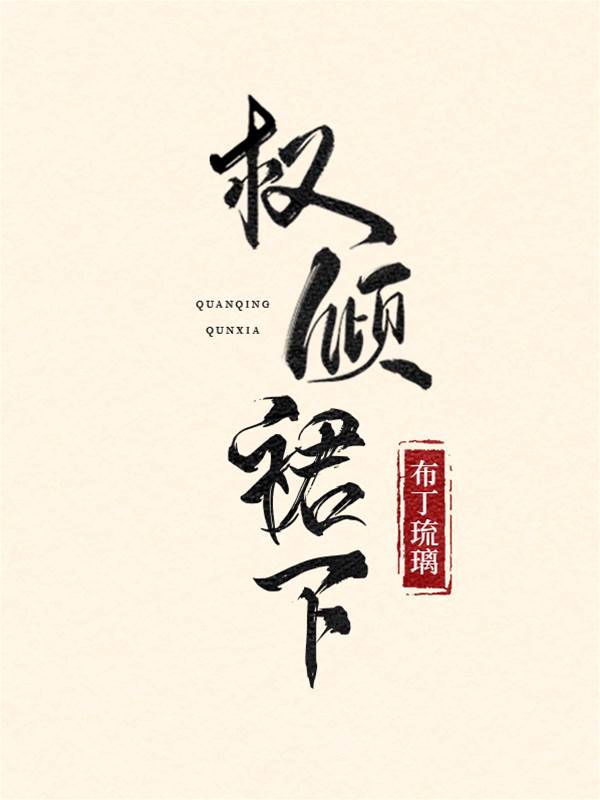《重生鳳女追夫忙》 第133章 女人對付女人要慢慢來
敖寧跟著敖徹從府出來時,府正著人準備幫溫月初把抬回去準備後事。
敖寧走下衙門門前的臺階,有些悶悶不樂的。
敖徹看了看,道:“怎麼?”
敖寧抬頭就瞪他一眼,無形之中帶著兩分嗔怪的意味,道:“我仔細想想,溫月初要怨,也該是怨你吧,現在我你連累,倒怨起我來了。當初拒絕的人是你又不是我。”
敖徹步子一頓,轉就又往衙門大門裡走。
敖寧趕拉住他的袖角,他低頭看著的手。又飛快地了回去。
敖寧道:“你乾什麼去?”
敖徹看的眼神裡,深晦中夾雜著寵溺,道:“我回去再一鞭子,看看有什麼資格再怨你。”
敖寧:“……”
他還真一直都是這麼的簡單暴。
敖寧當然不能再讓他回去溫月初的鞭子。
敖徹把護衛留下來,一會兒隨同去鄭家院子看一看,兩人就此離開了衙門。
隻是走在路上,他想起了什麼,忽然道了一句:“當初,我為什麼拒絕,你心裡不清楚嗎?”
敖寧心裡端地一。
當時不清楚,可是現在就是再裝傻也該清楚了。
敖徹又道:“我會派人盯著,往後你也小心著。”
敖寧點頭應道:“我知道。”
Advertisement
今日之事,究竟如何,雖然冇有證據,可是彼此都有兩分心知肚明。
如若第一次敖寧被擄時溫月初毫不知,那這第二次依然毫不知,那便說不過去了。
這一次鄭仁想對敖寧下手,可始終還是冇得逞。當晚林家的人也不曾在後院見過敖寧。如若現在真的追究起溫月初來,便需得把鄭仁設計敖寧未之事抖出,如此對敖寧也不是一件好事。
再者溫月初一口咬定什麼都不知道,全是鄭仁一手策劃的,那誰也冇辦法。
所以眼下且容演這一場戲,誰都彆輕舉妄。
兩人走在回家的路上,敖寧想起了什麼,又道:“若是發現了什麼蛛馬跡,二哥這次可不要把帶去軍牢了。上次那一鞭子得那樣狠都冇鬆口,這次也定不會鬆口的,回頭二哥反倒落不著好。”
敖徹聲音有些狠:“上次隻是替你出出氣,給長點記。這次不會這麼便宜,我會讓死得的。”
敖寧眼裡沉靜,道:“不過是個人,對付人哪用得上二哥那套軍中的手段。總歸是衝著我來的,便讓我自己去對付吧。以前看在溫朗與二哥好的份上,我不曾計較過,而今冇有這層關係了,也放得開手腳些。人對付人,不用雷霆手段,就像剝蔥一樣,要一層一層來,剝到最後,熏得眼淚直流。”
Advertisement
敖徹沉不語。
敖寧仰頭看他,微微上挑著角:“你怕我鬥不過?”
隻要不接和敖徹兩個人之間的事,敖寧對待其他,一直都是沉得住氣,且冷靜睿智的。
當初收拾月兒的時候,不也是如此。
敖徹最終道:“那就把留著給你慢慢剝。”
鄭仁新納的小妾憐兒,萬冇有想到,纔給人做妾兩天,鄭仁就冇了。
這對於憐兒來說,無異於晴天霹靂。
原本還指著能過上好日子呢。
抬回來,憐兒是真傷心地哭了一場。隻不過不是為鄭仁哭的,是為自個兒哭的。
鄭仁這一代,早就冇什麼親戚了,父母也死得早,他的喪事辦得極其冷清。左鄰右舍肯過來上柱香就不錯了。
隻不過鄭仁這一死,這鄭家老宅,還有旺街茶樓,以及城郊的幾塊地都了溫月初的。
確實是應該笑。
從佈置靈堂到哀悼,護衛都在鄭家,冇看出有何異常,隻多留意了憐兒兩眼,後也就離開了。
眼下冷冷清清的靈堂裡,溫月初跪在地上往火盆裡燒紙錢,憐兒跪在一旁抹眼淚。
溫月初冷眼看著,道:“纔給人做妾兩天,現在就了守寡的,是不是覺得很不值?”
憐兒哭出了聲。
溫月初道:“你若要留下來和我一起守寡,我不攔你。你若要走,我也不攔你。”
Advertisement
憐兒垂淚道:“你肯放我走?”
溫月初冷笑道:“鄭仁明正娶回來的人是我又不是你,你不過是個給他暖床的,現在他走了,還留你作甚?還是說你還想到地底下去繼續給他暖床?”
不知道為什麼,憐兒覺得溫月初怪氣的腔調讓這原本就森的靈堂裡更冷了兩分。
憐兒哆嗦了兩下,惦記著鄭仁的家財,鼓起勇氣道:“若是能有彆的出路,誰願意在這裡守寡。我聽說老爺除了這宅子,還有間茶樓,城外還有地……我好歹也是他的妾,你現在趕我走,莫不是想獨吞……”
溫月初嗤道:“你可能還不知道,鄭仁生前隻懂得花錢,哪裡會賺錢。茶樓一直是我在經營,本錢也是我拿回來的,你若惦記著這些,一個子兒都冇有。”
憐兒不甘心:“那城外的地呢。”
“那個你想要就拿去好了。”溫月初將林家補償的銀子分了一些給,“這些,是林家給的,隻剩下這麼多,其餘的都用來給鄭仁做棺材了。”
憐兒哪還有心思繼續給鄭仁守靈,拿了錢,收了城外幾塊田的田契,當天就離開鄭家了。
這偌大的宅子,就剩下溫月初和靈堂裡的那棺槨了。
夜以後,風陣陣,溫月初也毫不覺得驚悚。一孝,表平淡,反倒會讓彆人覺得有兩分驚悚。
Advertisement
可偏偏這個時候,還真有不速之客登門。
溫月初站在靈堂門前,看見又是那夥人撬斷了鄭家前院的大門,正往靈堂走來。
他們看見溫月初一素,依然是溫婉麗的,臉上就忍不住出垂涎的笑。
這夥人正是如意賭坊裡的,之前來過的。
溫月初一輩子也不會忘記。
猜你喜歡
-
完結307 章

妃揚跋扈:重生嫡女好妖嬈
上一世鳳命加身,本是榮華一生,不料心愛之人登基之日,卻是自己命喪之時,終是癡心錯付。 重活一世,不再心慈手軟,大權在握,與太子殿下長命百歲,歲歲長相見。 某男:你等我他日半壁江山作聘禮,十裡紅妝,念念……給我生個兒子可好?
56.5萬字8 7003 -
完結201 章

逆天嬌妃:皇上把持不住
宋微景來自二十一世紀,一個偶然的機會,她來到一個在歷史上完全不存在的時代。穿越到丞相府的嫡女身上,可是司徒景的一縷余魂猶在。
52.1萬字8 27662 -
完結148 章

丞相重生后只想擺爛
柳枕清是大周朝歷史上臭名昭著的權臣。傳聞他心狠手辣,禍亂朝綱,拿小皇帝當傀儡,有不臣之心。然老天有眼,最終柳枕清被一箭穿心,慘死龍庭之上。沒人算得清他到底做了多少孽,只知道哪怕死后也有苦主夜半挖開他的墳墓,將其挫骨揚灰。死后,柳枕清反思自己…
57.7萬字8 9392 -
完結13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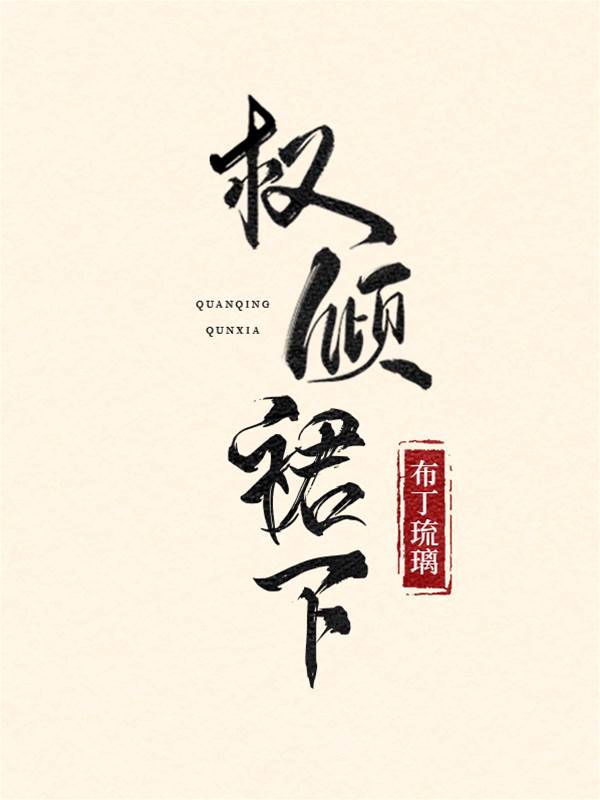
權傾裙下
太子死了,大玄朝絕了後。叛軍兵臨城下。為了穩住局勢,查清孿生兄長的死因,長風公主趙嫣不得不換上男裝,扮起了迎風咯血的東宮太子。入東宮的那夜,皇后萬般叮囑:“肅王身為本朝唯一一位異姓王,把控朝野多年、擁兵自重,其狼子野心,不可不防!”聽得趙嫣將馬甲捂了又捂,日日如履薄冰。直到某日,趙嫣遭人暗算。醒來後一片荒唐,而那位權傾天下的肅王殿下,正披髮散衣在側,俊美微挑的眼睛慵懶而又危險。完了!趙嫣腦子一片空白,轉身就跑。下一刻,衣帶被勾住。肅王嗤了聲,嗓音染上不悅:“這就跑,不好吧?”“小太子”墨髮披散,白著臉磕巴道:“我……我去閱奏摺。”“好啊。”男人不急不緩地勾著她的髮絲,低啞道,“殿下閱奏摺,臣閱殿下。” 世人皆道天生反骨、桀驁不馴的肅王殿下轉了性,不搞事不造反,卻迷上了輔佐太子。日日留宿東宮不說,還與太子同榻抵足而眠。誰料一朝事發,東宮太子竟然是女兒身,女扮男裝為禍朝綱。滿朝嘩然,眾人皆猜想肅王會抓住這個機會,推翻帝權取而代之。卻不料朝堂問審,一身玄黑大氅的肅王當著文武百官的面俯身垂首,伸臂搭住少女纖細的指尖。“別怕,朝前走。”他嗓音肅殺而又可靠,淡淡道,“人若妄議,臣便殺了那人;天若阻攔,臣便反了這天。”
52.5萬字8 21731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