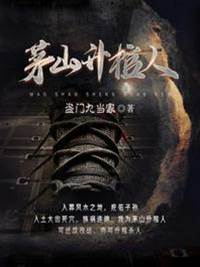《盜墓筆記》 第11章 裘德考的邀請
“裘德考的人已經滿村都是了,他們似乎還是沒有進展,很多支援和後勤的人盤踞在村裡,人多勢衆,他們知道您要來,裘德考已經放出話來了,他要見你一面。”
潘子的隊伍分兩組,一組是下地的,一組是支援的。他說,這一次是救人爲主,深山中的那個妖湖離村子太遠,後勤就顯得尤爲重要,平日裡我們進山都要兩三天時間,現在在進山的路線上設三個點,一個點五個人,二十四小時番候命,這樣可以省去晚上休息的時間,把村子到妖湖的支援短到一天以。
這樣,是支援的夥計就是十五個人,由秀秀負責,剩下的兩個好手跟我們下地。加上小花、潘子和我,一共是五個人。那個三叔的人啞姐,竟然也在五個下地的人。
我問潘子爲何這麼安排,潘子道:“那丫頭我們用得著,我想三爺當初培養,應該是有真本事。當然,三爺有沒有睡我就不知道了。而且,已經對你起了懷疑,這種人帶在邊最保險。”
我道:“那老子不得時時刻刻提心吊膽?”
“進去之後,我們肯定會分開,和花爺一隊就行了,救人要,救上來什麼都好,救不上來,恐怕你也沒心思裝什麼三爺不三爺了。”潘子道。
我點頭,之前覺得是否人有點太多了,可是一想是去救人,而且要在最短的時間把人救出來,這些人還是要的,在那種地方待的時間越長越是危險。
那妖湖湖底的村落,還有太多的謎沒有解開,如果張家古樓正是在湖底的巖層之中。以那邊山的大小裡面必然極其複雜,可以預見我們進張家古樓之後,推進一定非常緩慢。良好的後勤可以彌補我們上一次的尷尬。
Advertisement
一起去下地的人中,只有一個小鬼我不認識他。他極其的瘦小。才十九歲,外號皮包,據說耳朵非常好使,是極好的胚子,在長沙已經小有名氣。這次夾喇嘛把他夾了上來,價碼最高。我想他是個什麼樣的人,得相一下才知道。據潘子說,價碼高的。一定不好相。
至於裘德考,潘子問我要不要去見,我想也不想就拒絕了,這種節骨眼上,各種事混,應酬的事就不要去理了。老子剛覥著臉演了一出大戲給三叔的夥計看,這個老鬼不知道比那些人要明多倍,又沒有必須去的理由,何必這個黴頭?
潘子道:“也未必,白頭老外和三爺之前的關係很複雜。我也搞不清楚當時發生了什麼,他找你,也許你可以去試探一下。”
我心說這倒也是。不過試探這種老狐貍,非神力俱佳才行。我心中想著胖子他們的安危,此刻倒不急於琢磨這些破事了,便對潘子道:“不急,等人救出來,有的是機會試探,現在箭在弦上,不得不發。我們到了之後,先休整一晚。第二天立即出發,到了湖邊再說。讓他反應不及。”
潘子搖頭道:“這種老狐貍,要避開我看難。不過還是按照你說的做。你的思路是對的。”
我們各自打著算盤,又把各種細節討論一遍,便開始閉目養神,顛簸了七個小時之後,我們到達了乃。
下來的一剎那,我看到那些高腳木屋,悉的熱帶大樹,穿著民族服飾的村民,恍惚間就覺,之前去四川去長沙經歷的一切都是夢幻,回到阿貴家裡,就能看到胖子和悶油瓶正在等我。
天氣已經涼爽了,但是比起長沙和四川還是熱很多。我解開服釦子,就發現啞姐在看著我,心裡咯噔了一聲,立即又扣上去找阿貴。
Advertisement
阿貴還是老樣子,這時的夜已經全黑了,我遞煙給阿貴,對他道:“總算回來了,雲彩呢?”
阿貴一邊把我們往他家裡引,一邊很驚訝地看著我:“老闆以前來過?認識我兒?”
我這才反應過來,我已經不是吳邪了,現在對於阿貴是一個陌生人,不由得尷尬地笑笑,說道:“來過,那時候我還很年輕。你兒也雲彩?我上次來,這兒有個有名的導遊也雲彩。”
阿貴點頭,似懂非懂:“哦,這名字得多了,那您算是老行家了。”
我乾笑幾聲,看了一眼啞姐,似乎沒有在看我了,其他人各自下車。阿貴帶來的幾個朋友都拿了行李和裝備往各自的家裡走去,這裡沒有旅館,所有人必須分別住到村民家裡。
“您是這一間。”阿貴指著我和悶油瓶、胖子之前住的木樓子,我嘆了一聲,就往那間高腳屋裡走去,開門簾進去,我愣了。
我悉的屋子裡已經有了一個人,他正坐在地上,面前點了一盞小油燈。
那是一個老外,非常非常老的老外。我認出了他的臉:裘德考。
“請坐,老朋友。”老外看到我進來,做了個作,“我們終於又見面了。”
我吸了口氣,冷汗就下來了,心說果真避不開,來得這麼快。我瞄了一眼外面,看潘子他們在什麼地方。
裘德考立即道:“老朋友見面,就不用這麼見外了,稍微聊聊我就走,不用勞煩你的手下了吧。”
我沒看到潘子,其他夥計全都說說笑笑的。我心中暗罵,轉頭看向裘德考,勉強一笑,幾乎是同時,我看到裘德考的邊放著一個東西。
那是一把刀,我認得它,那是悶油瓶來這裡之前小花給他的那把古刀。
Advertisement
我心裡咯噔一聲,第一個念頭竟然是:這麼快又丟了,真他媽敗家。轉念一想,纔想到不妙,這東西是怎麼發現的?難道裘德考的人已經進到妖樓中去了?
裘德考看我盯著那古刀,就把古刀往我這邊推了一下,單手一攤道:“應該是你們的東西,我的人偶然拾到的,現在歸原主。”
“這是從哪兒弄來的?”我故作鎮定地走過去,坐下拿起一看,知道絕對不會錯,就是悶油瓶的那把刀。
這把刀非常重,不過比起他原來的那把黑刀分量還是差了很多,連我都可以勉強舉起,刀上全是污泥,似乎沒有被拭過。
“何必明知故問呢?”裘德考喝了一口茶,“可惜,我的人負重太多,不能把首一起帶出來,可憐你這些夥計,做那麼危險的工作,連一場葬禮都沒有。不過,你們中國人,似乎並不在意這些,這是優點,我一直學不來。”
“首?”我腦子轟了一聲,“他死了?”
“這把刀是從一上拿下來的,如果你說的就是這把刀的主人,我想,應該是死了。”裘德考看著我的表比較驚訝,“怎麼?這個人很重要嗎?吳先生,以前你很會對死亡出這種表。”
我看著這把刀,彷彿進了恍惚狀態,心說:絕對不可能,悶油瓶啊!
悶油瓶怎麼會死?悶油瓶都死了,那胖子豈不是也好不了?不可能,不可能,悶油瓶和死完全是絕緣的,這個世界上,還有什麼地方能讓他死?!他絕對是不會死的。
恍惚了一下,我立即強迫自己冷靜了下來,仔細去看這把刀,問裘德考:“那,有什麼特徵嗎?”
Advertisement
裘德考被我搞得不得要領,也許他一直以這種高深的姿態來和中國人別苗頭,和三叔之前也可能老是打禪機,可我畢竟不是三叔,沒法配合他,我只想知道問題的答案。
他詫異地看著我,失聲笑了起來,喝了一口茶,忽然道:“你真的是吳先生,還是我記錯了?”
我上去一掌就把他的茶打飛了,揪住他的領子道:“別廢話,回答我的問題。”
裘德考年紀很大了,詫異之後,面就沉了下來,問道:“你怎麼了,你瘋了?你對我這麼無禮,你不怕我公開你的嗎?吳三省,你的敬畏到哪兒去了?”
我!我心說,你的中文他媽的是誰教的,餘秋雨嗎?但我一想,這麼暴,他也不可能很正常地和我說話了。我腦子一轉就放開他道:“你先回答我的問題,這事非同小可,你還記得你在鏢子嶺的遭遇嗎?你還想再來一遍嗎?”
裘德考愣了一下,整理了一下服,問道:“這麼嚴重?”
“回答我,那個人是什麼樣子的?”
裘德考道:“我不清楚,是我手下的人。”
“帶我去見他。我要親口問他。”我道。
裘德考看著我,凝視了幾分鐘,發現我的焦急不是假裝的,立即站了起來:“好,跟我來,不過,他的狀況非常糟糕,你要做好心理準備。”(未完待續)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