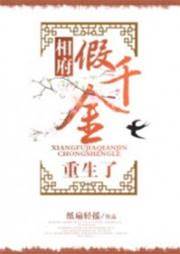《重生之鋼鐵大亨》 第41章 地盤
吃過飯,沈淮也沒有立即回鎮政府,而是在鎮上溜躂起來。
接待站是九零年新建的樓,可以說是除了鋼廠之外,梅溪鎮最爲標誌的建築。
樓臨街高三層,往西逐級擡高到五層,半弧形結構,線條很流暢,外立面滿白間綴藍花的馬賽克,彷彿一道涌來的白海浪。
臨街的半片樓作爲鎮接待站使用,除了餐飲之外,還有客房部。不過梅溪鎮挨著東華市區很近,對住宿要求稍苛刻一些的客人,都會住到東華市區去,接待站的客房部,經營狀況談不上理想,唯有餐飲部依靠政府跟鋼廠的吃喝過得特別的滋潤。
從接待站南面的庭園繞進去,就是跟接待站同一棟樓的文化站。
說是文化站,其實也早承包出去了。
進門底樓的大廳裡就擺放了一圈遊戲機,大中午的,裡面擁了不社會青年以及梅溪中學的學生,在角落裡還有一羣人圍著賭遊戲幣的兩臺老虎機,沒有人在意沈淮走進來。
從轉角扶梯走上去,二樓是鎮上的錄像放映廳。門口掛著一張黑板,用紅*筆寫有今天下午要播放的錄像。
《卿本佳人》的影片名上,還大大的標註著“香港豔、大作”六個字。
三樓是舞廳,裡面線暗暗的,還沒有到營業的時間,看不到有人在。四樓纔是鎮文化站在這棟樓裡唯一保留的設施,鎮圖書室。圖書室的門虛掩著,也看不到有人在。
五樓是辦公室,大中午也看不見有人在,再上就是天臺。
天臺上有對躲在角落裡對吃舌頭,穿著梅溪中學的校服,看到沈淮上天臺來,才分開來,故作鎮定的轉頭看向外面。
Advertisement
除了鋼廠的高爐、自來水廠的水塔,梅溪鎮就沒有比這棟樓還高的建築了。
沈淮站在天臺上,視野開闊,極目遠眺,往南能看到鋼廠的高爐跟空中鋼廊,往西能看到梅溪河粼粼的波,往北、往東則是片的田野。下梅公路、學堂街、梅溪老街、鋼廠路以及一些鄉村土路,將梅溪鎮分割參差不齊的數十片。
遠眺景壯,然而將視線收回來,滿眼則是梅溪的窮困跟破舊。
不要說更遠的鄉村地區,鎮上也皆是鱗次櫛比的青磚瓦房,間或有茅草屋頂,曲曲折折的小巷顯得陳舊、雜。
從文化站大樓以及新鋪柏油路面的學堂街,能看出梅溪鎮在九零年前後財政還比較可觀,只可惜甜期過於短暫,文化站大樓與鎮政府大院之間的梅溪中學,主要還是解放前一直留下來的校舍以及日軍侵華時建造的馬棚。
除蔥蔥郁郁的樹木之外,梅溪中學顯得陳舊不堪,場也是一片土黃。
不要奢什麼塑膠跑道、草皮了,沈淮上午在辦公室看到教育辦遞上來的一張關於梅溪中學跳遠沙坑需用兩噸沙的用款申請單,便略見梅溪中學的教育用款窘迫到什麼程度了。
在文化站的北面,是鎮敬老院,兩排六七十年代建的平房。沈淮居高下,能看到南棟平房的屋頂給大風揭掉一片瓦,臨時用茅草跟地槊料遮在上去。敬老院的大院子,有七八名孤寡老人打瞌睡,還十幾只散養的滿院子的追逐。
學堂街西的鎮菜市場是一片彩鋼棚。去年冬天大雪,彩鋼棚積雪太厚給塌,現在還能看到彩鋼棚屋頂上有塌折的痕跡。
也許是以前從沒有站到這個角度去看梅溪鎮,對梅溪鎮的經濟滯後跟破舊,沒有此時這麼深刻而鮮明的。
Advertisement
遠不要說跟歐的鄉村小鎮相比了,就跟渚江南岸的平江市鄉鎮比,梅溪鎮也落後太多了。
“你在看什麼?”
沈淮轉回頭,見陳丹從另一頭鐵扶梯爬上天臺,側著子依著欄桿,說道:“沒想到站在這裡看梅溪鎮的風景這麼好……”
“你是剛剛走上來巡視自己的地盤呢,那趕是覺得站上來看風景好。要是多上來兩次,你就會看到梅溪落後的地方,南面的鋼廠以及梅溪河污染都很嚴重……”陳丹說道。
這會是自己的地盤嗎?沈淮心裡自問。
他之前決定留在東華,一是要照顧好小黎,再一個想著做一番績,以改變宋家對他的看法,但真正的去審視這片他魂牽夢繞的土地,他心抑不住涌出來的一衝:
唯有讓這片土地變得更好,更富足,才真正是他應該去做的事。
“你跟小黎住哪裡?”沈淮平靜的看著陳丹。
“諾,那片平房就是鎮上的宿舍,”陳丹指著文化站西邊的一條狹窄巷子,說道,“沈書記你要是不住老宅,接待站有客房可以住,也可以跟鎮上要間宿舍住;或許可以直接住進鋼廠的宿舍樓前……”
陳丹指著南面鋼廠背後兩排灰白的小樓。
梅溪鋼廠的年產鋼材量大約不到市鋼廠的十分之一,但擁有近八百名職工,在遠近也算是首屈一指的大廠。
“你過來是找我的?”沈淮又問。
“啊,”陳丹這纔想到上天臺是爲哪般了。
剛纔走上來,看到沈淮著遠出神,給他線條俊朗的側臉以及專注的神所吸引,就把這事給岔開了。
陳丹臉微紅,說道:“趙東過來了,趕巧到接待站借電話要聯繫你。我看著你轉腳進文化站了,想著你會在天臺,就過來喊你了……”
Advertisement
沈淮跟陳丹下樓來,趙東跟楊海鵬就在接待站外等著,也不曉得他們倆從哪裡搞來一輛桑塔那,就停在路邊。
沈淮看著楊海鵬,問道:“趙東從市鋼廠辭職了,現在無所事事,你怎麼也不管你的建材店了?”
“嗨,店裡能有多大的事?今天是沈書記你新上任,怎麼也要過來湊個熱鬧。沈書記你不會不歡迎我過來吧?”楊海鵬著跟刺蝟似的寸頭,笑起來眼睛瞇一條,熱的稱呼著沈淮的新名。
沈淮笑著在楊海鵬肩膀上拍了一掌,說道:“不要喊生分了,我在東華也沒有什麼朋友,願意你跟趙東兩個朋友。”
楊海鵬眼的纏著趙東一起趕到梅溪鎮來,也有自己的小九九,也擔心心思太明瞭,會沈淮不喜歡;這時候他這一掌打得心頭一熱。
“進去找個地說話吧……”沈淮邀著趙東、楊海鵬往接待站裡走。
中午的會餐他攪了局,接待站這時冷冷清清的,也不知何月蓮去了哪裡,陳丹領著他們上二樓的包廂,沏來茶水,還是站在包廂門口,也不進去,也不離開,好像真是隨時聽候吩咐的服務員。
沈淮拿起茶壺,給趙東、楊海鵬分茶,說道,“今天的況有些複雜呢,我上午就跟杜老虎鬧翻了。按說他下午應該帶我直接到鋼廠宣佈任命,不過照眼前來看,他可能躲起來不理會我。”
“任命通過沒有?”趙東問。
“杜老虎也就在梅溪鎮算是頭虎,但還沒有膽子違擰縣裡的意志,任命倒是通過,”沈淮笑道,“既然任命都通過,他們拖著不宣佈任命,也沒有意義,大概是中午給我氣歪了,拿這事消氣呢……”
Advertisement
“你能幫杜老虎氣什麼樣子?”楊海鵬問道。
就在梅溪大橋以南的沿河地區,有一片挨河運碼頭的建材店。河西岸屬於唐閘區,河東岸屬於梅溪鎮,楊海鵬的建材店就在河西岸,但對梅溪鎮的況比較瞭解。
在知道沈淮昨天領老熊去省城所爲何事之後,楊海鵬也就不擔心有新市委書記撐腰的沈淮會吃不下杜建,但也好奇沈淮第一天會怎麼樣跟杜建鬧翻臉。
“諾,這事你們問陳丹……”沈淮笑道。
“又挨著我什麼事?”陳丹站在門口嗔道,“我就管端茶遞水了,別的事可不知道。”
楊海鵬嘿嘿一笑,他也打心眼裡認定沈淮租孫海文留給他妹的老宅,就奔這滴滴的明豔陳丹過去的。因爲跟孫海文的關係好,雖說沒有怎麼跟陳丹見過面,也知道的一些況。
這世界就是男歡,沈淮年權重,風流倜儻,就算邊花花草草一大堆,在楊海鵬眼裡也本就不算什麼缺點。
他看著陳丹跟沈淮眉來眼前,心想著,莫非是勾搭上了?
趙東的心思沒有楊海鵬那麼複雜,還想著沈淮頭一天就跟鎮黨委書記鬧翻的事,說道:“梅溪鋼廠的副總工程師徐溪亭是市鋼廠出去的,跟我、海鵬都認識,本來早就想找機會一起吃個飯,但徐溪亭是個謹慎的子,想著事定下來再見面。要是杜建拖著不帶你去鋼廠宣佈任命,是不是晚上就找徐溪亭出來一起吃頓飯?”
“也行。”沈淮點點頭,杜建上午一系列手段,無非就是想把他架空,而他想掌握實權,無非也就拉到足夠多能聽他話的人。
沈淮對徐溪亭不陌生,他進市鋼廠裡,徐溪亭還指導他技,算是市鋼廠技比較強的人之一。梅溪鋼鐵廠八九年引進英式短流程電爐進行擴張,特意從市鋼廠將徐溪亭聘請過去主持該項目。
徐溪亭工程師出,子又有些,空有一技,到梅溪鋼鐵廠這種地方,也不可能得到發揮的機會。說實話徐溪亭能一直呆在梅溪鋼鐵廠而沒有給踢出來,還要算他子有韌。
猜你喜歡
-
完結1507 章

都市天龍至尊
一代仙尊,被最好的兄弟與最心愛的女人背叛偷襲,在天劫中含恨隕落,卻意外重回少年時期。這一世,且看他如何重回巔峰,手刃仇人,最終登臨蒼穹之巔,執掌一切!
269.1萬字8 287498 -
完結1203 章
重生軍婚:神醫嬌妻寵上癮
前世的顧雲汐,愛他愛的要死,卻一心想著躲著他,以至於生生錯過了那個愛他一生的男人! 重生後的顧雲汐,依舊愛他愛的要死,卻一心想著,撩他!撩他!睡他!睡了他! 前世的學霸女神迴歸,娛樂圈瞬間出了一個超人氣天後,醫學界多了一個天才神醫。 風光無限,光芒萬丈的人生中,顧雲汐滿腦子都在想著,寵夫!實力寵夫! 當他為了掩護戰友撤退而受傷時,她氣的直接衝過去端了人家的老巢,老孃的男人都敢動,不想活了? 要問陸昊霆的人生樂趣是什麼,那一定是寵妻!實力寵妻! 某豪門大少帶著一眾記者“揭穿”她潛規則上位時,一身軍裝身姿高大的他忽然出現,霸道的擁她入懷,“有我在,她用得著潛規則?”豪門大少頓時嚇癱,少……少司令! 顧雲汐抱著陸昊霆,“好多人說我配不上你,貪財好色賴上你了”,陸昊霆大掌摸摸她的腦袋,聲音低沉,性感迷人,“乖!那是他們眼瞎,明明是我貪財好色賴上你了!” 兩人甜甜蜜蜜,狗糧遍地,虐的一眾單身狗遍地哀嚎!
172.7萬字8.71 923696 -
連載136 章

重生旺家小錦鯉,開荒種田成首富
重生回了風沙連天,種什麼都半死不活的戈壁黃土地。 盛姣姣一腳踢開了前世渣夫,決定專心搞事業,恢復生態,讓戈壁荒灘變成綠水青山。 先從種出半畝菜地開始...... 盛姣姣:那個男人,上輩子我倆的緋聞直接讓我死於非命,這輩子,你要不要對我負個責? 譚戟:那是緋聞嗎?
39.8萬字8 7850 -
完結337 章
重生後王妃嬌軟不可欺
京城人人傳說,杏雲伯府被抱錯的五小姐就算回來也是廢了。 還未出嫁就被歹人糟蹋,還鬨得滿城皆知,這樣一個殘花敗柳誰要? 可一不留神的功夫,皇子、玩世不恭的世子、冷若冰霜的公子,全都爭搶著要給她下聘。 最讓人大跌眼鏡的是,這麼多好姻緣這位五小姐竟然一個都不嫁! 她是不是瘋了? 冠絕京華,億萬少女的夢,燕王陸雲缺去下聘:“那些人冇一個能打的,昭昭是在等本王!” 宋昭挑眉,“你個克妻的老男人確定?” 陸雲缺擺出各種妖嬈姿勢,“娘子你記不記得,那晚的人就是本王?” 宋昭瞪眼:原來是這個孫子,坑她一輩子的仇人終於找到了。 這輩子,她得連本帶利討回來了。
60.7萬字8 15044 -
完結25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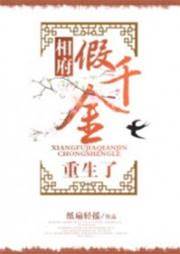
相府假千金重生了
蘇靜雲本是農家女,卻陰差陽錯成了相府千金,身世大白之後,她本欲離開,卻被留在相府當了養女。 奈何,真千金容不下她。 原本寵愛她的長輩們不知不覺疏遠了她,青梅竹馬的未婚夫婿也上門退了親。 到最後,她還被設計送給以殘暴聞名的七皇子,落得個悲慘下場。 重來一世,蘇靜雲在真千金回相府之後果斷辭行,回到那山清水秀之地,安心侍養嫡親的家人,過安穩的小日子。 惹不起,我躲還不行麼? 傳聞六皇子生而不足,體弱多病,冷情冷性,最終惹惱了皇帝,失了寵愛,被打發出了京城。 正在青山綠水中養病的六皇子:這小丫頭略眼熟? 內容標簽: 種田文 重生 甜文 爽文 搜尋關鍵字:主角:蘇靜雲 ┃ 配角: ┃ 其它: 一句話簡介:惹不起,我躲還不行麼? 立意:
39.4萬字8 30734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