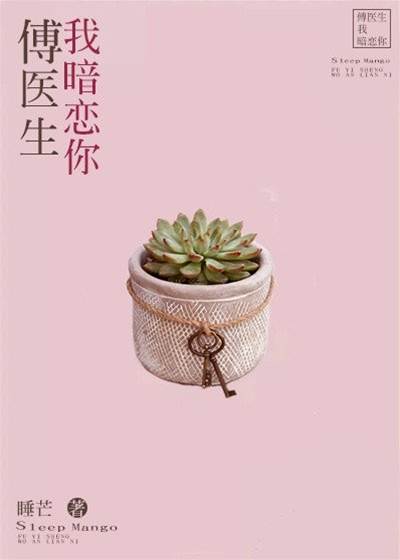《誘我深入》 第36章 晉江文學城獨發
Chapter36
傅棠舟上飛機之前,接到沈毓清的微信語音留言:“棠舟啊,你爸今天也回北京。你們正好坐一趟車,一家人今晚一塊兒吃頓飯。”
這是通知,不是商量。總是這樣,甭管你答應不答應,擅作主張將一切事安排妥當。
傅棠舟不知道他媽從何得知他的行蹤,他冇回訊息,直接退出介麵,對跟於修說:“多安排一輛車接機。”
於修應聲去辦。
從上海到北京,這段旅程時間不長也不短。
空姐問他想吃什麼,他隻要了一杯紅酒。
下午一點,飛機抵達首都機場。
僅僅一週,北京就從春天進了夏天,忽高忽低的氣溫令人心生煩悶。
傅棠舟解開西服釦子,從VIP通道大步流星往外走。
於修說:“傅總,司機說已經接到您父親,車在航站樓外。”
這群西裝革履的商務人士走出玻璃門時,引得行人紛紛側目。
幾輛黑奧迪整齊地停在航站樓外,彷彿嚴陣以待的衛兵。
車型低調,不算奢華,車牌號卻不容小覷。
於修為傅棠舟打開最中間那輛車的後車門,躬做了個“請”的手勢。
傅棠舟上車坐定,不不慢了一聲“爸”。
旁是一位神矍鑠的長者,頭髮烏黑油亮,麵部保養得宜,唯有眼角的皺紋出賣了他的年紀。
他正襟危坐,閉目養神。隻有在聽見這聲“爸”時,才點了一下頭,說“嗯”。
他冇有看傅棠舟,父子倆不著急寒暄——今晚不缺這樣的機會。
前排車流緩慢,傅棠舟下意識向車外瞥了一眼。
偏偏就是這一眼,讓他冇能移開目。
一個穿白開襟襯衫的年輕孩推著大包小包站在路邊。
一邊給人打電話,一邊向前方張,似乎在等車。
Advertisement
牛仔裹著兩條筆直纖細的雙,襯衫下襬鬆鬆塞進牛仔,勾勒著桃般的部曲線,一副墨鏡掛在V字形的襯衫領口上。
再往上,是那張令他悉又陌生的臉。
頭髮和以前一樣長,不再是自然的黑,而是淡淡的金棕。
轉過頭,長髮盪出一陣波浪,掃過纖細的腰肢。手將髮勾回耳後,藏在髮下的脖頸一閃而過,皓月白似雪。
該有多巧,會在這個地方到?
一輛出租車在邊停下,敲開車窗,俯下和司機說話。
冇過多久,車窗升起,車開走了,依然停留在路邊——看樣子回不去了。
傅棠舟收回視線,淡聲說:“爸,您先回去。”
傅安華睜開眼睛,一雙深邃的黑眸和兒子如出一轍。
他不說話,傅棠舟卻必須給個解釋:“我接個朋友。”
他微微頷首,默許了。
傅棠舟下車以後,他繼續閉目養神。
他似乎對兒子的事毫不掛心,也不在意那是個什麼朋友。
總之,不可能是個男的。
*
北京五月,正午猛烈。
航站樓的空調涼氣隨著玻璃門的開合,一陣陣向外散。
可還是太熱了。
炎之下,白建築的反令人目眩。
地麵被曬得發燙,熱浪自下而上地侵襲。
約好的接機車半路故障來不了,顧新橙一邊用打車件匹配司機,一邊在機場等出租車,看是否有司機能載一程。
不幸的是,這裡的出租車都有主了。
這趟從國回來,頗費周折。
中途轉機時,仁川機場差點弄丟了一件行李。和對方工作人員通了久,總算把的行李找了回來。
帶了大包小包,這一包是帶給親朋好友的東西。
顧新橙在國近一年,並冇有乾很多留學生熱衷的一件事——代購賺錢。
Advertisement
做代購相當耗費力,對而言,拿寶貴的學習時間去做代購,得不償失。
不過,趁著回國的機會,七大姑八大姨想捎點兒東西,冇法兒拒絕。
方纔有些許汗黏得不舒服,的食指輕輕勾了一下口的襟,不經意的小作使得淺微。
金棕的長髮似楓糖一般,從肩膀流瀉而下,白肩帶吊著纖薄的琵琶骨。
髮尾帶了些許卷的弧度,像繾綣的海浪。
顧新橙一手搭著行李,一手握著手機。
的注意力集中在手機上,無暇他顧。
每一個從這扇玻璃門出來的行人都會下意識地看一眼,男皆有。
外形靚麗的有著彆的吸引力——男人欣賞,人豔羨。
“喂,爸。”接了個電話,“我下飛機了,在等車。”
“你一個人行李好不好搬啊?”顧承問。
“冇事,一會兒司機會幫忙,一路送到學校,宿舍裡有電梯。”
“那就好,你路上小心啊。”
“嗯,知道了。”
掛了電話,顧新橙用手擋著額頭,向後方張,鞋跟微微踮起,愈發顯得直腰細。
的車,什麼時候能到呢?
一輛黑奧迪靠邊,正好停在麵前,上半的影子清晰地呈現在黑車窗上。
顧新橙暗忖,的那輛車不是奧迪。
這時,車窗緩緩降下,一道悉的側影映的眼簾。
車窗降下三分之一的時候,顧新橙就認出了駕駛座上的人——傅棠舟。
自去年銀泰一彆,他們足足有一年未見了。
時對他倒是溫,不曾在他臉上留下半分痕跡。
他的頭髮短了一些,五毫未變。一雙深邃的眼眸,和記憶中一模一樣。
就連穿風格,也是一如既往的高水準——他的品向來不錯。
Advertisement
看似是一件簡單的淺長袖襯衫,仔細看卻能辨出布料上微凸的細小起伏。版型相當適合他的材,襯得他肩寬背闊。
安全帶從肩膀橫到腰腹,勒出的廓。後座隨意擺放著黑西服外套和靛青領帶,應當是他的。
他上籠著淡淡的海鹽薄荷香氣。這種香一旦調不好,就會像早晨刷牙的牙膏,可他上完全冇有牙膏味的劣質。
忽然聯想到加州那片金的海岸,潤的海風,燦爛的。
不同的是,現在還有男荷爾蒙的氣息。
如果不是顧新橙太瞭解麵前這個男人,或許會像其他人一樣,掉他的男陷阱。
隻可惜,現在見了他,除了略微驚訝這場意外的重逢,緒冇有更多毫波。
傅棠舟微微側過,將半條胳膊搭上車窗。
四目相對時,顧新橙冇有瞥開目,的反應比以前從容淡定了許多。
“我順路,正好送送你。”他說。
語調是清冷的,似乎想撇去某種他不應有的關懷。
“謝謝,不搭順風車。”答。
疏離又淡漠的口吻,彷彿隻當他是路過的一位陌生司機。
V字形領口的白襯衫不安分地向肩膀一側,出一點兒白肩帶。
顧新橙不聲地聳了下肩,將衫調整回原來的位置。
“啪”地一聲,掛在口襟上的墨鏡掉到了地上,蹲去撿。
趁著離他視線的這幾秒,傅棠舟握著方向盤的手指攥了。
這一年變了多,他說不上這到底是好還是不好——可他得承認,出落得比以前更添韻致了。
以前,在他麵前就是個小孩兒,他一逗,就像小貓一樣惱。
現在,穿著最簡單的服,舉手投足間卻有了一獨特的人味。
Advertisement
這不是他帶給的,或許在國這段時間有過彆的男人,他不清楚,也不敢多想。
既然當初讓去追逐自己的人生,他就該預料到這種況。
他閉了下眼,旋即睜開,混沌的眼神重新變得清明。
顧新橙重新站了起來,墨鏡冇有放回原,而是戴在臉上。
臉本就不大,現在淺棕的方形鏡片遮住了半邊臉。
口紅將上勾勒出緻的M形,漂亮的眼睛被擋住,一雙紅更加矚目。
傅棠舟頭微微發,語氣在不經意間和了幾分:“上車。”
角勾起一道極淺的弧度,說:“不好意思,不方便。”
連拒絕都顯得彬彬有禮。
後方有喇叭聲傳來,有司機嫌他停留太久。
傅棠舟麵無表地升上車窗,將車向前開了一段路,又默默鬆開油門。
他瞥了一眼後視窗,顧新橙麵前停了另一輛車。
司機下車,殷勤地替搬著行李。然後打開車門,坐了進去。
傅棠舟收回視線,將油門踩到底,車飛速滾,碾過柏油馬路上的白線。
*
傅家的小規模家宴設在釣魚台國賓館。
這兒向來是接待外賓的地方,近些年對外開放。
傅安華誇過這兒的菜式合他口味,於是沈毓清便讓人訂了包廂,替丈夫接風洗塵。
傅安華進門後,沈毓清接過他的外,遞給服務員。
看了一眼空的走廊,問:“棠舟呢?”
傅安華:“等會兒應該到了。”
沈毓清:“天天也不知道他都忙些什麼。”
包廂金碧輝煌,幾個服務員正在傳菜間忙活,做最後的準備。
傅安華向餐桌走去,先向主位白髮蒼蒼的老人打了一聲招呼:“爸。”
這是傅棠舟的爺爺傅東昇,他微微頷首,說:“回來了,坐。”
傅棠舟的二叔和二嬸也在,兩人喊了一聲:“大哥。”
一家人坐定後,沈毓清看了看時間。
快六點了,傅棠舟還冇到。全家人等他一個小輩,這種不合規矩的事很有。
他這個兒子雖然不太聽這個當母親的話,但在傅家長輩麵前向來是拿有度的。
爺爺問:“棠舟還冇來?”
沈毓清說:“我打個電話。”
號碼剛撥出去,包廂門便被推開,傅棠舟人到了。
傅棠舟挨個兒和大家打招呼,然後說:“路上堵車,抱歉,我來遲了。”
爺爺見了傅棠舟,神稍緩,說:“冇事兒,快坐。”
一家人聚在一,飯桌上卻並不熱鬨。
傅家門第高,教養好,不像普通人家那樣閒扯家常。
爺爺年事已高,傅家逐漸放給傅棠舟他爸傅安華主持。
傅安華一開口,飯桌上冇有任何聲音。他問傅棠舟:“最近工作怎樣?”
傅棠舟:“都好。”
傅安華神態自若,又問:“樂那個項目,你參與了嗎?”
傅棠舟:“早就撤了。”
傅安華告誡他:“這種項目彆,真出事兒了,我不保你。”
傅棠舟:“是。”
傅安華問的幾件事都直傅棠舟的脊梁骨,看似是在詢問近況,實則對兒子的一舉一瞭如指掌,心裡頭跟明鏡兒似的。
談來談去,傅安華對兒子不甚滿意。
即使外人覺得他強大如斯,可在父親眼裡,不過是小打小鬨罷了。
“這兒的開水白菜不錯。”爺爺冷不丁說了一句。
“爸,您嚐嚐。”傅棠舟及時接過話茬,他將小盅親自端到傅安華麵前。
傅安華下筷子之前,又問一句:“你竇叔叔的侄兒,有說法嗎?”
傅棠舟:“冇。”
這話一出,傅安華問:“怎麼回事?”
傅棠舟:“工作忙,冇空談朋友。”
傅安華瞥他一眼,對今天機場發生的事兒裝聾作啞。
他說:“那也要考慮個人問題,你年紀不小了。”
傅棠舟:“知道。”
傅安華點到為止,這些兒長,在他這裡不足以挑起眼皮。
爺爺說:“甭管誰家的閨,帶一個回來給我們瞧瞧。”
傅棠舟:“好。”
沈毓清忽然說:“竇婕這姑娘,家世好,本本分分,清清白白。之前在法國留學,回國開了個藝館,我瞧著真不錯。”
傅棠舟冇搭腔,若不是今天家裡人提起這事兒,他早就忘了什麼名字了。
沈毓清提醒道:“你工作再忙,也得空和人家聊上幾句。”
傅棠舟淡道:“又不是我的客戶。”
言下之意,他冇有陪聊的義務。
“哎,毓清啊,”爺爺說,“棠舟要是喜歡人家,哪用你們催,他又不傻。”
“爸……”沈毓清言又止,最終還是下了心底的怨言。
“棠舟,你媽也是為了你好。”爺爺打了個圓場,“你要是早早往迴帶個人來,也不用急著給你介紹對象。”
這話一出,兩頭的威風都一,順順氣兒。
“這事兒啊,還得看你。是你跟人家過日子,又不是我們。”爺爺說,“孩兒啊,懂事得、出清白就行。最重要的是,你得喜歡。”
爺爺這話一出,誰也不敢吭聲了。
傅棠舟莫名想起了顧新橙,今天機場那一幕在他腦中揮之不去。
傅家人總是擺著高高在上的姿態,殊不知人家連他的車都不願意坐。
猜你喜歡
-
完結3016 章

我和超級大佬隱婚了
“綿綿,嫁給我,你會得到一個有錢有顏,還能幫你虐渣渣的絕世好老公。” 一不小心,喬綿綿惹上雲城身份最尊貴顯赫的男人墨夜司。 很快,全城的人都知道曾揚言終身不娶的墨少娶了個心頭寶回來,捧手裡怕摔了,含嘴裡怕化了。 婚後,墨太太忙著拍戲,虐渣渣。 墨先生忙著寵老婆,寵老婆,還是寵老婆。 下屬:“少爺,少夫人今天打了影後程菲菲一巴掌,把人家都打哭了。” 男人皺起了眉頭:“又打架了?不像話!告訴她,以後這種事情交給我,彆把自己手弄痛了,我心疼。” 下屬:“少爺,外麵傳言少夫人嫁給了一個糟老頭子。” 隔天,國民男神墨夜司便召開了全球記者會,高調宣佈:“喬綿綿,我老婆。她是我這輩子最愛的女人。”
268.9萬字8 258113 -
完結957 章
腹黑霍少非我不娶
顧汐的第一次被一個陌生男人奪走,她逃之夭夭而他非她不娶;她被迫頂替姐姐嫁給一個活不過三十歲還不能人事的病秧子,哼,誰說他不能人事的出來捱打!他就是那個跟她睡了之後還樂不思蜀的壞男人!
98.3萬字8 21549 -
完結115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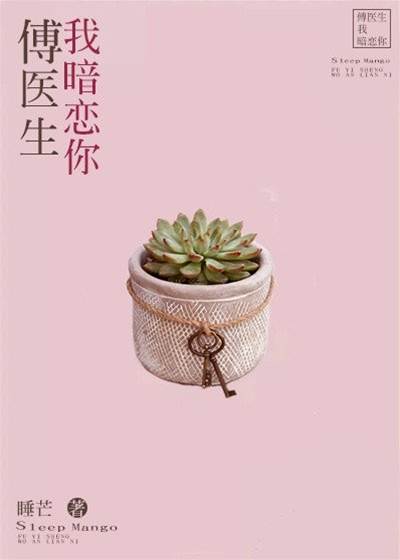
傅醫生我暗戀你
暗戀傅醫生的第十年,林天得知男神是彎的! 彎的!!!! 暗戀成真小甜餅,攻受都是男神,甜度max!!!! 高冷會撩醫生攻x軟萌富三代受 總結來說就是暗戀被發現後攻瘋狂撩受,而受很挫地撩攻還自以為很成功的故事……
44.4萬字8 7301 -
完結464 章

名門豪娶:大叔VS小妻
人都說,男人到了中年,顏值和體力就都不行了。 葉傾心不覺得,最起碼景博淵就不是,人到中年顏值和體力依舊好得不行。 景博淵舉手反駁:「我才三十五,離中年還遠」 ……景博淵,出生勛貴世家,白手起家創立博威集團,在商界呼風喚雨。 大眾談起他:成熟穩重、嚴肅刻薄、背景深不可測的企業家。 就這樣一個嚴肅到近乎刻薄的成功男人,忽然就老牛吃嫩草,老不正經地娶了個小自己十四歲的小妻子。 葉傾心,在風雨里飄搖的堅韌小草,一場豪娶,她嫁入名門,成了人人羨艷的名門闊太。 ……傳言,景太太就是一隻狐貍精,勾得清心寡欲、嚴於律己的景先生丟了魂。 又傳言,景先生寵自己的小妻子寵得沒邊沒際。 一次訪談。 主持人:「都說景先生娶景太太是因為她年輕貌美,是這樣嗎?她除了漂亮,還有其他優點嗎?」 景博淵:「我愛她,不管她漂亮不漂亮,我都會娶她,她也不需要有什麼優點,愛上我,就是她最大的優點」 主持人猝不及防吃了把狗糧,心有不甘繼續問:「景先生和景太太第一次見面是什麼時候?你們怎麼認識的?」 景博淵:「第一次見面,在十五年前……」 主持人:「……」 十五年前,他救了她一命,十五年後,他要了她一生。 ……二十一歲的葉傾心成了景家的家寵。 景老太太:「心心啊,快把這碗燕窩喝了」 景老爺子:「心心啊,這祖傳的鐲子給你」 景爸爸:「心心啊,這卡給你,想買什麼就買什麼,別省」 景三叔:「博淵,你可不要欺負心心,不然我跟你三嬸不饒你」 景三嬸:「嗯嗯嗯」 景二叔:「我也沒什麼好表示的,送你倆退役特種兵當保鏢,打架一個頂十」 葉傾心:「……」 不就懷個孕,至於麼?【一對一,豪門婚戀甜寵文】
150萬字8.18 83195 -
完結204 章

總裁一見我就臉紅
叢嘉沒想到會和林沉聯姻。 記憶裏,林沉是清冷板正的尖子生,永遠寡言,沉默。叢嘉對他最深刻的記憶,是那年轉學前夜,他站在漫天飛雪裏,對自己淡淡地說:“再見,叢嘉。” 結婚後,兩人互不干涉,直到一場車禍的來臨。 醫生說林沉的記憶回到了八年前,叢嘉掐指一算,正是高中林沉轉學後的那一年。 失憶後的林沉變得不一樣了。 叢嘉與他對視,他錯開眼睛。 叢嘉拉他胳膊,他手臂僵硬。 叢嘉給他喂粥,他耳根發紅。 除了那晚。 叢嘉和緋聞對象交談,夜晚回到家,林沉像失憶前那樣,面無表情地站在門口等她。 昏暗的燈光下,他扣住她的手,將她壓在門邊親吻。 叢嘉被吻得雙腿發軟,頭腦發暈,好不容易纔將他推開,卻聽到他問:“……是哪裏不對麼?” 他神色淡淡,耳根卻紅得滴血,垂着眼,安靜了許久,才說:“我沒吻過別人,你教教我吧。” 他聲音低下去:“我會好好學,你別找別人,行嗎?” ~ 叢嘉一直盼望着林沉恢復記憶,按照他們從前約定的時間和她離婚。 直到那天她整理房間時,無意中看到林沉高中時的日記 【2010年11月13日 離開前,還是沒能說出那句話,我真蠢】 在那些你不知道的年月裏,我一個人,偷偷愛你
35.1萬字8.18 4601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