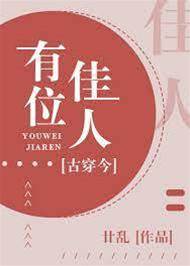《大唐明月》 第69章 暗潮洶涌 情愫盪漾
從丹霄殿往前,便是萬年宮的主殿大寶殿,只在大朝之日纔會用上。和萬年宮其他宮殿一般,這大寶殿規制不大,不過是面闊五間,進深三間,但琉璃碧瓦,牆玉階,又是矗立在天臺山的最高,在日出日落之時看去,當真是“珠壁映,金碧相暉,照灼雲霞,蔽虧日月”。大寶殿前的兩道長廊幽延迴轉,通向幾座東西向的殿宇,便是隨駕的中書、門下兩省的臣工們辦公及居住的所在。
琉璃走在這人字拱頂的秀雅長廊之上,心裡多有些撲騰。這個月以來,再不曾去過丹霄殿,卻也曾聽武則天說過,水災之後諸事千頭萬緒,隨駕員中長於庶務者本就不多,司空李績又著了風寒,高宗便讓曾任刺史的史大夫崔義玄統籌、裴行儉協理,清點善後修葺重整的各種事務,兩人安排得井井有條,高宗曾笑言,這兩人都是有文武之資,實務之才的。
想來這一個月,他大概真的是辛苦。只是,武則天這番安排,卻不會那麼簡單……最近難道還會有什麼大事要發生不?
琉璃正想得出神,就聽走在邊的宦魏安道,“庫狄畫師,往這邊走。”擡頭一看,原來已經到了一小院前。
魏安笑道,“裴舍人就住在裡面,您看是否要小的先去通傳一聲?”
琉璃忙道了聲不敢,這魏安也是咸池殿裡的管事太監,品級與劉康相當,年紀還要略大些,哪裡敢這麼拿大?只能笑道,“咱們都是奉命來送加造的,有什麼通傳不通傳?”
魏安笑著點了點頭,拎著食盒輕車路的走了進去,那院子並不大,屋前種的兩棵合歡樹倒是頗有年頭了,院角的綠苔中臥著幾塊奇石,正面是一間面闊三間的樓閣,兩邊廊下各有廡房,此刻靜悄悄的,只聽得見樹上知了的聲。魏安上了臺階,從廊下轉到南面,在一扇木門前停了下來,擡手輕釦了兩聲。琉璃只覺得心也砰然跳了兩下。
Advertisement
門吱呀的一聲開了,出一張十七八歲的年面孔,看見魏安和琉璃,疑的眨了眨眼睛,隨即似乎想起了什麼,魏安已先笑著開了口,“今日中伏節,我等是來給裴舍人送冷淘的。”
年立時笑了起來,行了個禮,“請與阿監稍待,我家舍人這就來迎。”
魏安忙道,“不敢勞煩舍人。”說話間只聽踢踏聲響,裴行儉含笑的聲音響了起來,“可是魏侍,快請進。”
魏安一怔,隨即臉上綻開了一個大大的笑容,快步走了進去,琉璃默然跟在後面。只見裡面原是外兩進的屋子,裴行儉正站在外屋當中,大概是午睡剛起,形容與平日頗有些不同,上穿了件白短,青下裳,外面披著月白的半袖,頭髮只是用了一支木簪挽住,腳下穿的是雙木屐,不冠不履,容清爽,比往日平添了十分灑隨意。
裴行儉看見魏安後的琉璃,笑容一凝,隨後才慢慢加深,轉頭對魏安道,“如此暑日,勞煩魏侍了。”
魏安正低頭打開食盒,雙手端出一個折枝花紋的帶蓋銀碗和一個裝了幾塊金小餅的牙盤,放在了外屋的案幾上,聽到裴行儉的話,直起笑道,“不敢當,若是沒有裴舍人日夜辛勞,小的哪裡能過上這伏節?是聖上和昭儀惦記著裴舍人近來辛苦,才特意遣了小的過來。”
裴行儉微微欠,“臣多謝聖上與昭儀的賞賜。”
魏安又對琉璃笑道,“庫狄畫師,您看這裡還有一份是要送給崔大夫的,崔大夫住在外朝,畫師卻不好出去了,不如您在這裡等小的一會兒,小的回頭過來再找您?”
琉璃雖然知道這一趟出來,武則天必有此意,但臉上忍不住還是有些發熱,點了點頭,“有勞了。”
Advertisement
眼見魏安笑嘻嘻的走了出去,那個年不知怎的也出溜一下消失在了門外,屋裡突然變得出奇的安靜,窗外的知了聲似乎越發的響亮了。半響,只聽木屐踢踏兩聲,裴行儉走到了琉璃面前,琉璃看著那青裳的角已停在自己面前不到一步,只覺得怎麼也擡不起頭來,又聽見他低低的喚了一聲,“琉璃。”
琉璃心裡突然有些鄙視自己,咬了咬下脣,擡起頭來努力展一笑,裴行儉慢慢的也笑了起來,眼裡閃的芒明亮愉悅,突然道,“琉璃,你不,陪我用一點可好?”
琉璃忙搖頭,“我,吃過了。”
裴行儉卻道,“只用一點好不好?”
琉璃微微奇怪,只見他凝視著自己,目裡有期待之,頓時再也說不出“不好”兩個字,點了點頭。裴行儉的笑容變得更加明亮,走到案幾前坐了下來,讓出半邊位置,擡眼看著琉璃。
琉璃和他並肩跪坐在了坐席的茵褥之上,只覺得覺十分異樣,臉頰已不可抑制的燒了起來,悄悄看了一眼裴行儉,他在正低頭拿開那銀碗上的蓋子,距離這麼近,能看出他的確消瘦了一些,眼睛下面有淡淡的青痕,能看清他的側面廓線極其漂亮,額頭飽滿,鼻樑直,有著雕塑般的流暢,睫又長又,所以顯得眼睛格外深邃。一時幾乎說不出話來。
裴行儉放好碗,側頭看著琉璃,角微揚,把那碟金餅推到了的眼前。琉璃不敢再看他,默默的從袖子裡拿出乾淨的帕子,包住一塊不過半指長的餅,小口吃了起來,金餅裡的餡料大概是酪,涼了之後味道著實有些發膩,琉璃吃在裡,只覺得舌尖都是沉甸甸的。
Advertisement
裴行儉也拿起了筷子。他吃得並不算慢,也有些隨意,一碗冷淘沒過多久就下去了一半,卻安靜得只能聽到銀筷到碗邊時發出的聲音,作裡更是似有一種悠然的韻律,那種骨子裡散發出來的優雅,頓時讓本來想多陪吃一會兒的琉璃有些自慚形穢,嚥下第二塊餅就用帕子了手和,再也不好意思吃第三塊。
裴行儉看了琉璃一眼,夾起了一個金餅,吃了一口,似乎怔了一下,又吃了幾口冷淘,這才放下筷子,自然而然的從琉璃手裡拿過帕子,了角,隨手便收到了自己的懷中。
琉璃一呆,想說你把帕子還給我,又覺得說出來也太傻,想了半日不知道該說什麼,只能手將銀碗碗蓋蓋上,把碗和盤收拾到了案幾的一邊。卻聽裴行儉道,“琉璃,多謝你。”
琉璃有些驚訝轉頭看了裴行儉一眼,他的臉上有一種異常明亮的芒,看見琉璃訝然的眼神,垂眸微笑道,“那餅那般冷膩,你竟然空口吃了兩塊。”
琉璃不由有些茫然,實在不大明白他怎麼會在意這樣的小事。裴行儉也不多說,只雙手一按站了起來,“我適才本是準備煮茶的,你若喜歡,我這就煮給你喝。”
琉璃下意識的就想搖頭,這時候的茶自然喝過,味道絕對只能以古怪來形容,庫狄家煮茶的加的是鹽、姜和棗,安家則喜歡加油和胡椒,讓這個喝了十幾年綠茶的人簡直哭無淚。但看著裴行儉,開口卻變了,“只怕魏侍就快回來了。”
裴行儉笑著搖了搖頭,“你且放心,沒半個時辰,他絕不會回來。”
琉璃想起他還沒看見魏安就出了他的名字,不由有些奇怪,“你怎麼跟他這般?”
Advertisement
裴行儉愣了一下,才笑道,“哪裡?只是他曾替武昭儀來拿過一次文書,我認得他的聲音罷了。”
琉璃只能在心裡翻了個白眼,因爲從小便學了繪畫,因此對長得略有特些的面孔都能過目不忘,但比起這個隨便就能記住路人甲聲音的傢伙來,顯然簡直不值一提。只能也站了起來,“你先別急著煮茶,我,我有話跟你說。”想到要說的話,一時又有些說不出口。
裴行儉低頭凝視著琉璃,輕聲道,“可是武昭儀答應了一回長安就讓你出宮?”
琉璃震驚的看著他,雖然覺得自己或許應該習慣於他的未卜先知,忍不住還是問道,“你又是怎麼知道的?”
裴行儉淡淡的笑了笑,“今日讓你來,自然不是因爲這碗冷淘。”
琉璃看著他的神,只覺得心裡一沉,好在這個月來也打了一篇腹稿,忙道,“你或許覺得武昭儀心機深沉,只是那後宮裡,若是毫無心機的,連自保都不能。昭儀待下人一貫寬厚,我在咸池殿幾個月,不曾見責罰過一個宮;待聖上也深意重,那日大水,等在水裡,見聖上出來了才肯一道離開;這次的事,也多虧了從中周旋。想來便是有些打算,又有什麼要?昭儀不曾薄待過我,我日後即便無從報答,總不能辜負了這份恩義。再說,我得罪的,又是魏國夫人……”
裴行儉低頭凝視著,眼神和裡帶著點無奈,嘆了口氣,“我明白,你放心。有些事原不是做臣子的可以過問,我不會讓你爲難。只是,此次一回長安,宮外也必然是多事之秋,你萬事都要當心一些。”
琉璃心裡也嘆了口氣,他這算勉強答應了麼?只是“多事之秋”,難道說後宮之爭這麼快就已經到了朝堂之上?“爲何這麼說?”
裴行儉沉了片刻,簡簡單單的道,“魏國夫人的兄長柳奭已然上表請辭中書令,若聖上準了,免不了朝廷盪,若是不準,聖上此次一回長安,必然更是暗洶涌。”
柳奭?琉璃只有一個模糊的印象,但作爲王皇后的舅舅,此時還不到勝負已分的時候,他這是……“柳相難不是想看看聖上到底是什麼意思?聖上會準麼?”
裴行儉讚賞的看了琉璃一眼,又寬的笑了笑,“聖上想來也會多加考慮,你也不用太過擔憂,你深居簡出一些,魏國夫人倒也未必記得找你麻煩。”
琉璃點了點頭,就是,魏國夫人原來就是閒的,如今的皇后兒都要被廢了,想來絕沒有時間惦記著自己這個小小畫師。想到此,的心倒是忍不住振了一點。
裴行儉笑道,“如今可有心思吃茶了?”說著手一引,“大娘,這邊請。”
琉璃忍不住笑了起來。
轉過外屋當中的那架六扇墨書屏風,只見裡面靠窗設著坐榻案幾,案幾上是幾個青瓷茶杯,同瓜棱洗口執壺,又有白瓷茶碾、純銀茶盒等,邊上放著一個壺門高圈足的銅風爐,裡面已有炭火,旁邊還有一個長柄的茶釜。
裴行儉讓琉璃在案幾對面的榻上坐下,自己將風爐的幾個壺門打開,又把茶釜放了上去,微笑道,“這萬年宮的泉水雖然比不得惠山寺虎丘寺的泉水,似我這般的俗,只覺得用來煮茶倒也夠了。”
琉璃默默無語,心道,你是俗,我算什麼?
過得片刻,茶釜裡的水冒出了細細的氣泡,裴行儉便回從案幾上的鎏金三足託盒裡用銀勺取出了一些白末撒了進去,琉璃估量著應該是鹽。待到水再次沸起來時,見他用竹勺舀出了一勺水,放旁邊的白瓷碗裡,隨即一邊用竹夾攪拌,一面將早已碾碎末的茶投了茶釜中,那茶釜中的泡沫頓時飛濺起來,此時便將白瓷碗的水重新倒了進去,待到水第三次沸起細細的泡沫時,纔將茶釜移開,慢慢分兩個茶盞之中。
茶湯倒青瓷,細沫浮碧,十分清爽,但琉璃的目卻無法從裴行儉上挪開,眼前之人手指白皙修長,神悠然而專注,一舉一,風儀清雅得難以言表。琉璃覺得自己就像對著一幅名家山水,初看只是颯爽,細看時每一筆裡都有神韻。
猜你喜歡
-
完結568 章

長安風流
貞觀大唐,江山如畫;長安風流,美人傾城。 妖孽與英雄相惜,才子共佳人起舞。 香閨羅帳,金戈鐵馬,聞琵琶驚弦寂動九天。 …… 這其實是一個,哥拐攜整個時代私奔的故事。
207萬字8 20611 -
完結212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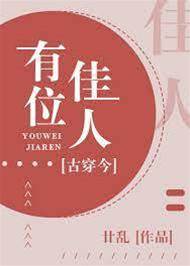
有位佳人[古穿今]
沈嶼晗是忠勇侯府嫡出的哥兒,擁有“京城第一哥兒”的美稱。 從小就按照當家主母的最高標準培養的他是京城哥兒中的最佳典範, 求娶他的男子更是每日都能從京城的東城排到西城,連老皇帝都差點將他納入后宮。 齊國內憂外患,國力逐年衰落,老皇帝一道聖旨派沈嶼晗去和親。 在和親的路上遇到了山匪,沈嶼晗不慎跌落馬車,再一睜開,他來到一個陌生的世界, 且再過幾天,他好像要跟人成親了,終究還是逃不過嫁人的命運。 - 單頎桓出生在復雜的豪門單家,兄弟姐妹眾多,他能力出眾,不到三十歲就是一家上市公司的CEO,是單家年輕一輩中的佼佼者。 因為他爸一個荒誕的夢,他們家必須選定一人娶一位不學無術,抽煙喝酒泡吧,在宴會上跟人爭風吃醋被推下泳池的敗家子,據說這人是他爸已故老友的唯一孫子。 經某神棍掐指一算後,在眾多兄弟中選定了單頎桓。 嗤。 婚後他必定冷落敗家子,不假辭色,讓對方知難而退。 - 新婚之夜,沈嶼晗緊張地站在單頎桓面前,準備替他解下西裝釦子。 十分抗拒他人親近的單頎桓想揮開他的手,但當他輕輕握住對方的手時,後者抬起頭。 沈嶼晗臉色微紅輕聲問他:“老公,要休息嗎?”這裡的人是這麼稱呼自己相公的吧? 被眼神乾淨的美人看著,單頎桓吸了口氣:“休息。”
49.8萬字8 8186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