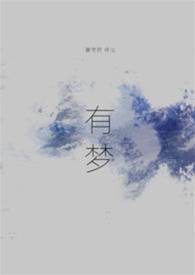《掌中雀》 第26章
第26章癡計(六)
李紹側躲避,李慕儀屈膝跪上案幾,雲羅擺掃得酒壺、白瓷跌了地,軲轆轆轉得滿地水跡,酒了裳,李慕儀也顧不得管,雙手捧住李紹的臉一追再追,與他雙雙跌倒。
好在那下還鋪著絨錦毯,也好在李慕儀的手擱在了李紹的頸下,才不至於讓李紹吃痛——縱然他對這樣的疼痛向來不以為意。
可李紹驚住神,深的瞳孔不由了。他詫異得不是的吻,而是的手,這實在是極侵略的作,讓他明確到了李慕儀的主導。
李慕儀檀口中泛起濃郁的酒香氣,小舌勾引似的舐過他的、他的齒,待他張口吮住的,拆骨腹那般啃咬時,這人又立刻反客為主,乘虛而,纏著他的舌尖細細吮弄。
李慕儀垂落的掃在李紹的掌心,意從那開始,往他骨子裡鑽,渾脈賁張,幾乎都要裂開,可始終都尋不到一個洩的地方。
李紹惱了,掐住李慕儀的腰,避開的親吻,“李慕儀,你活膩了?”
Advertisement
李慕儀略抬了抬頭,教酒意迷了的雙眸迷茫又無辜,“或許王爺殺了我,也是好的。”
的手探進李紹的領裡,這本還算是清爽的天,他又不像李慕儀懼冷,就是在數九隆冬,懷裡都似燒著一團火,故而,輕易地到了他膛渾厚的,在尋著什麼,或是稍稍凸隆的傷疤,或是……
李紹一把按住的手,目危險,“瞧出來了,你既是來尋歡的,也是來找死的。”他扯著李慕儀的腕子將從上拽下來,翻屈膝制住李慕儀想要掙扎的雙,一手將的手腕反按在頭頂,一手攏起的下頜,惡狠狠地盯住的眼睛。
可這雙眼睛著實無辜了些,眼眶紅,彷彿方才那些事都不是做出的。李紹的惱意作不出,自嘲地笑了一聲,低道:“你……你這到底在想什麼啊?”
“王爺。”
“嗯?”他俯下,因著還想聽說話,也未去吻,兩人鼻與鼻,與,若有似無地輕點,挨蹭,耳鬢廝磨。
李慕儀環住他的肩背,手指輕輕劃弄著他袍下隆起的背,相較於他的強韌,李慕儀的手似無骨般。側臉親了親李紹的耳兒,“我在想王爺。”
Advertisement
李紹教這廝三言兩語撥得恣心縱慾,可他堂堂雁南王因個人兒就丟盔卸甲,傳出去未免教人笑話。他放不下那與生俱來的驕矜,而他也著實有比尋常人更好的控制力。
至在李慕儀看來,縱然那下已高高昂起,燒刃一樣抵著的小腹,滿是威脅,可他眸中始終是無的。
男人和人最不相同,於人而言,這場事若無在裡頭,必定痛苦;而於男人而言,縱然沒有,也能行得了一場歡愉事。
“別著急。”李紹挲著的,“以後有你想的時候。”
李慕儀不言,輕輕闔上眼睛,細金的碎落在的臉上,廓纖小溫,“皇上令王爺離京,王爺就當真願意?”
李紹撥了一下額上凌的,手指順著臉廓往下,著的耳垂兒,手游移向下,隔著襟去的,他撥開襟,兩個渾圓的跳出,他垂下頭銜住那嫣紅尖兒輕咬,李慕儀又痛又,忍不住息。
他說:“倘若本王不願,你會怎麼樣?”
Advertisement
李慕儀半睜著眼,似乎在很認真地思考李紹的話,待李紹的吮弄咂愈暴貪婪,李慕儀才回過神回答: “王爺既不喜我假他人之手,我也更想親自與王爺做個了結。”
“了結?”李紹掀起的羅,手指探幽,勾連出一片黏膩銀,有著濃烈的靡味道。
他著李慕儀吮住他的手指,輕嘲道:“教本王欺負了那麼久,也還是這樣。你講講,這要如何了結,恩?”
“王爺那日再倚朱樓與趙大人所說的話,我聽得了一些。”
李紹輕挑了一下眉峰。
李慕儀說:“王爺襟非人能及,行堯有您這樣的兄長,是他的福氣。可他要長大了,王爺在京,他就永遠長不大,所以行堯才恨王爺。這樣的恨不會消失,早晚有一天,他會殺了你。”
靜靜地凝著李紹,“王爺又何不趁此機會,離開京城,去做了真正的逍遙閒人?”
“如此說來,本王難道還要謝你這一遭出京計不?”李紹不可置否地笑了一聲,“可是李慕儀,你怎不問問,什麼才稱得上是真正的逍遙閒人?”
Advertisement
他俯在李慕儀耳旁,開擺,曲起的膝蓋。李慕儀一下咬住,微微合著眼,那碩大滾燙的一寸一寸緩慢又堅定地,那盤亙在腔裡的酒氣燒起來,燒得五臟六腑都快了灰燼,空空的,只剩下李紹。
待送到最深,李紹放緩了呼吸,輕吻著李慕儀綿的耳垂,呼吸往耳朵裡鑽,燙在心上。
他道:“沒有你,如何稱得了逍遙?”
猜你喜歡
-
完結288 章
美豔妖婦
“我不是神仙,我是妖怪。”梅說。我哈哈大笑,說她這麼漂亮,怎麼可能是妖怪。而之後我和梅相處的日子,一直都很平淡,梅做些糖巧點心在村裡售賣給小孩子,來維持生計。我給她跑腿幫忙,還能免費吃糖。
70.2萬字8 25635 -
完結3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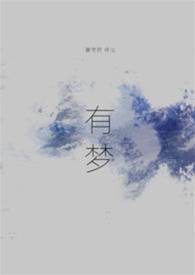
有夢
作品簡介: 她總說他偏執。 是了,他真的很偏執,所以他不會放開她的。 無論是夢裡,還是夢外。 * 1v1 餘皎x鐘霈 超級超級普通的女生x偏執狂社會精英 練筆,短篇:) 【HE】 其他作品:無
5.9萬字8 55327 -
完結0 章

公主為奴
要去和親的長公主與清冷俊美的暗衛的故事。本以為是她掌控了他,卻不想被他玩於股掌……其實這裡已經暗示大家啦,男主不是吃素的啦……開了新文《鯊》,寶貝兒也可以去吃吃肉(*σ´∀`)σ“狗一樣的東西,再忤逆本宮試試?”“本宮的身子很喜歡你。”“被屬下這樣低賤的雜種日逼,公主嬌嫩高貴的穴,可是得到滿足了?”卑微求珠~(每天都有兩顆珠珠,不投浪費啦~( ͡° ͜ʖ ͡°)✧)正文不收費,附有打賞章,請寵愛我吧~珠珠破兩百加更~因為隨時籠罩在有一天可能登不上這個網站的恐懼中,為防哪天突然登不上失聯,我也學其他大大整了個微博,我以前不刷微博,不太會,不過留言我想我肯定還是會看到的,哈哈哈,我叫:來瓶礦泉水hi 點這裡跳轉微博避雷:我理解的1v1 是我愛你,我心裡隻想和你做愛。如果覺得被其他人摸了就不是1v1 了,請回避。
9.6萬字8 48461 -
完結97 章

折月
蔣赫和南月都是江中的風雲人物。一個是校霸,一個是學霸。一個是校草,一個是校花。一個是酷拽帥氣的體育生。 一個是清冷淡漠的小仙女。所有人都以為他們沒什麼交集,沒人知道他們是同住一個小區的鄰居,更是對對方身體了如指掌的青梅竹馬。
8.6萬字8 87068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