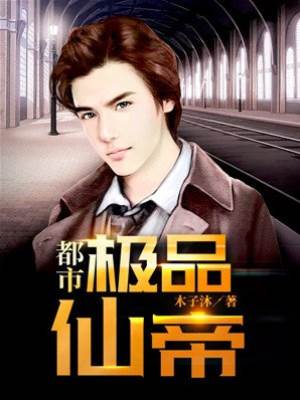《重生之大涅磐》 第兩百零一十章 波瀾
加州總部,在董事會完畢的間歇時間裏,整個國臉譜部於鬧嚷嚷人心不穩的狀態。
詹化和高恒站在明玻璃帷幕之下,沒有去顧忌背後的那些陸陸續續開始嘩然的人群。
原本還要進行投資的下一討論。但是卻不得不因為這樣的局而打了計劃,紮克已經無心再理事務。
高恒拿出手機,摁了號碼,然後撥出了電話。
江南省。
303國道之上,有一隊黑的公務車隊馳行,前麵開路的是兩台警車。一路風馳電掣。
車隊中的省府一號車,剛結束舟山海洋科技調研,舟山連島工程建設考察的江南省省長高浪濤就坐在位,旁邊的是江南省省建設廳廳長王昌厚巍巍在座,不斷的解釋連島工程的建設規劃中剛出現的紕,汗如雨下。
高浪濤一直很平靜得聽著,但他越是平靜,王昌厚心頭就越沒有底,誰都知道這個高老二是笑麵虎,他所擁有的派係力量足以讓他顛覆很多規則來行事,譬如這次著急的上馬舟山連島工程,接二連三的一些籌劃布局。這讓王昌厚不由自主的能想到在西南部省的那個和高浪濤齊名的對手,現在看來,高浪濤是在激進的準備趕超對手的威。今天連島工程的疏,恐怕還要追責下馬一大批人,至於這棒子揮不揮得到王昌厚的頭上,還要看他自己的造化。
有時候讓王昌厚都覺有種悲哀,類似高浪濤這樣人的崛起,總是會用很多白骨來鋪路的。
高浪濤的電話在這時響了起來,一看來電,接起,聲音醇厚的笑道,“小恒,怎麽這個時候想起給二哥電話”
然後就聽到電話裏高恒的聲音如從遠天之上傳來,道,“甕中捉鱉了。”
Advertisement
“那我提前祝賀了。”高浪濤掛了電話,王昌厚看到他臉上溢滿的笑容,頓時心汗倒豎起來。
首都。
在國龍頭央企新源集團於燕京召開的“清理整頓對外投資和多種經營工作會議”上麵,該集團公司黨組書記,總經理高滄海在會上指出,各地分公司必須服從做大、做強主業的戰略目標,堅決從非主業業務中退出。
高滄海在接下來接央視采訪的時候,提及這次清理整頓的難點,說道,“第一,涉及到既得者的利益。通常況下,各分公司的負責人都在對外經營中兼任著重要職務,清理工作一定會搖部分人的利益;第二,涉足公司太多。作為特大型資源企業集團,新源集團現有全資子公司、控和參子公司、分公司等共80餘家。按照最保守估計,每家分公司在5個企業中進行過投資,全國就有數百家民營企業到牽連,退出工作的進度難以估量。”
高滄海最後麵對聞訊而的多家國傳統第一,又道,“要按照國際化的要求,去枝強幹,把有限的人力、財力、力用於主業的發展,真正把新源做強做大,不斷提高發展質量,提高企業核心競爭力。”
講完話到了後台,新源集團在燕京的豪華落腳賓館,高滄海在一幹親信麵前臉立即變得晦暗起來。國開始加強國退民進的聲音中放上傾斜天秤那塊砝碼的,還是那個在西南部擁有極高聲的人。這樣的人發出在中央的意見,再加上派係的推之下,如今這種局勢就了主力聲音,就連國務院都相應的提出相關指導意見。
高滄海在召開這個涉及全國八十家國資背景企業龐大的工作會議之前,就已經有包括中央委員,計委等在的多方夠得上資格的重量級人和他談話做工作。高滄海主持這個工作會議,心憋屈是肯定會有的。這讓他更對王家的那個人甚至憤恨,沒有比較也就沒有落差,前些年高老在位影響力如曰中天的時候,高家那時候的輝煌如何,將王派切切實實踩在腳下,然而現在地位開始逆轉了。
Advertisement
那個人在西南部登高一呼,牽一發而全,導致中央都有人下來讓自己起個帶頭示範作用。
往往覆雨翻雲大度能容的人,就越有偏執執拗的一麵,高滄海即是如此,這種覺到一艘巨型派係艦隊,開始駛向落曰的那種憋屈和悲壯,是無法用言語來闡述的。偏偏大西南部又有他的肋,就連想安一些人手,打擊到那個人都不太可能。
這個時候,他接到了高恒的電話。
詹化一直在旁靜靜地立著,看到高恒一連撥了好些個電話過去布局拉網,他麵對窗戶外那些壯麗流的火燒雲,突然有些萬般,問,“現在結束了?”
“暫時告一個段落了。”高恒收了手機,朝仍然默默坐在淩的桌子麵前的紮克看過去,淡淡道,“你以前一直以為這是紮克和蘇燦聯合為我們下的套但是現在看到了,從事前我們的接安排,再到如今的董事會走向,以及新的權力架構,這都是徹徹底底實際的決裂,兩個人的演技能好到這種程度?如果真是如此,他們不是人,而是神了接下來的事就順理章了。”
隨即詹化高恒來到紮克麵前,高恒端了凳子在他對麵坐下來,道,“作為治理一個現代化公司的總裁,你謹記自己隻是ceo,你今天所做的事,從道義上來說或許有些瑕疵,但是你要明白,你是在為臉譜考慮,你看看這麽多人,你是在為他們考慮,為你一手創立的公司考慮。或許每個人都會遇到這種兩難的事,盡管艱難,但是我們仍要去抉擇,不是嗎。我為那個創始人而惋惜,但這一切為了未來,都是值得的。”
“是啊”紮克抬起頭來,用出的笑容道,“我是ceo”
Advertisement
然後他猛然道,“我隻是一個ceo,婊子!”
詹化然而怒,意蹭站而起,卻被高恒出的一隻手擋住。看到的是高恒沉得有些可怕的笑容,聲音溫和道,“沒關係”
然後對紮克綻放了一朵更大的笑容,道,“一切都將過去,你還是要收拾起心,繼續你的征程。接下來我們討論一下你手中臉譜中文的權出售一部分,怎麽樣?”
“你們過分了”紮克喃喃道。
高恒愣了愣,問,“什麽?”
“我說今天的董事會上,你們過分了原本不用這麽直接的。原本還有很多商量空間的”
“不要天真了。你單純的以為事會好商量的解決?如果事先被他知道我們是打算把他驅逐出局,現在鹿死誰手還都不知道,我們之所以能勝出,是因為轉移了他以及他背後那些人,那些勢力的視線。換一種況,說不定今天會被奪走公司的是你。你會被掃地出局”
盡管紮克不願意承認,但還是不得不從心深乃至骨子裏認同高恒的這句話,因為沒有人甚至連麵前專門對付蘇燦潛心設局的高恒和詹化,都沒有他這樣知道蘇燦的可怕。如果真的讓他事先知道事的原委,或許真如高恒所說的那樣,現在誰出局都不知道。
“但你們還是過分了。”紮克搖搖頭,“我想臉譜擁有四億元的投資已經足夠我們渡過難關了,我們現在還不缺錢,所以沒有後續的計劃。”
“你!”詹化首先坐不住了。
“沒關係。”高恒擺擺手,道,“我能理解你現在的心,也希你能理解我取得臉譜中文之後,對我來說有多重要的心。當然我願意給你時間考慮,等到你改變主意。”
在蘇燦從加州返回上海。國臉譜正式和紅杉idd兩大基金談妥整個融資過程的時候。
Advertisement
又是一天明,線正過臉譜大樓通的玻璃窗,形激起白絮的柱,穿整個大樓。
紮克正在自己的桌子麵前,梳理著麵前要理的一項報審批的網絡方案。抬起頭來,就看到達斯汀站在他的麵前。
紮克的目重新落在屏幕上麵,語速快速的問,“怎麽了?”自上個星期那件事發生之後,他也變得沉默寡言許多。甚至有很多時候在麵對凱瑟琳灰調失眼神的時候,他也沒有說任何辯解的話。
但達斯汀知道,這是他的選擇。他將手中的一封信擱置在紮克的桌子上。
紮克拿起信,仔細看起來,然後抬起頭看著他,半晌之後,才說出口,“你要離職?”
“是的,”達斯汀點點頭,“我很早以前,就一直想開一家自己的網絡件公司,名asana,很早很早以前,我就在琢磨這個想法了”達斯汀的金黃頭發暴在裏,他整個人仿佛都披了一層亮邊。
紮克躊躇了半晌後,道,“如果你是為了蘇燦的事,你可以不用有負擔,因為那是我你做的,而你別無選擇”他再一次的覺到心底的慌和難過了。
“不是蘇燦的事。而是我知道,這是我該離開的時候了”達斯汀語調極為平緩,但是部員工很多人都扭頭朝他看了過去。
紮克那仿佛抑了很久的悲傷,才在這個時候發了,接過達斯汀的辭職信,快速的在上麵簽下了自己的名字,丟在桌子上,道,“走吧。”
達斯汀微微笑了笑,拿起信,返準備離開。
但這個時候紮克開口了,道,“你是不是覺得我是一個混蛋?”
達斯汀轉過頭來,突然緒激烈道,“正相反,直到現在這一刻開始,我才知道,我們以前意圖認為會大家一起改變世界,都太天真了隻有你能掌控臉譜,讓他為帝國。”
“就像是對蘇燦一樣,隻要有任何能為威脅的事,不管意圖是什麽,都必須得到理。因為最終,隻有臉譜這一件事是重要的。你不會讓任何人或事阻礙臉譜的發展。紮克,你是一個徹頭徹尾的混蛋!你也是一個真正的ceo。”
“再見。”
達斯汀莫斯科維茨的離開,再度為自蘇燦離開臉譜過後,掀起矽穀的餘震餘波。
紛呈杳至的是《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經濟觀察》,《杉磯曰報》等諸多全主流,競相報道這個夏天,在矽穀那個地方發生的這場世界最大社網絡創始人的權力紛爭事件。
各種人在這些傳統報紙上麵紛紛對此事件發表激烈評論。
紐約時報人說“知道如何在全世界擁有兩億個朋友嗎?那就是出賣你最好的朋友。”
全最有公信力的《華盛頓郵報》特約評論人發布評論道,“追憶似水流年,我們那年說好一起要改變世界”
《芝加哥太報》知名評論家羅傑說,“發生在矽穀的故事是對現實最刺骨傷的批判,我們是兩名騎士,但我們總會分道揚鑣。”
其中《今曰國報》最直接,評論紮克道,“左腦天才,右腦混蛋。現在國會那些整天囂的議員,終於得逞了。”
對這個事件最後進行總結姓報道的還是紐約時報,雖然臉譜董事會披並不完全,但是紐約時報的記者買通了臉譜諸多員工,講述了整個臉譜網運作的這幾年裏麵,發生的那些激人心的社帝國崛起曆程,再到近期兩位創始人的訌權力之爭。
最後紐約時報在整篇寫到近期蘇燦離開臉譜故事的末尾。後麵附帶了一列清單。
“那些曾經的元老,他們是誰?他們的現狀。
馬克紮克伯格。
2004年7月,紅杉和idd投資以四億元的價格買下了臉譜33的權,使得該公司估值達到了120億元。目前馬克家多不太清楚,但是他肯定是地球上最富有的22歲年輕人之一,也可能是有史以來最年輕的白手起家的億萬富翁。
亞當德安傑。紮克高中時的發小。他開了一家新件公司。
馬特科勒。加了卓有聲的基準投資公司。為了風投人。
克裏斯休斯。似乎近期在涉足公益事務,為政斧的參議員貝拉克侯賽因奧馬工作。
達斯汀莫斯科維茨,他於上個月離開臉譜,去向未知。
蘇燦”
而所有人都不知道那個臉譜的共同締造者,那個引得全諸多神通八麵的特派記者們此時已經在收拾行裝準備各路出擊趕赴中國,深挖底細跟進的神聯合創始人。此刻正渾披著暖洋洋的坐在南大文博院的長椅上麵,一點也不像是那些各路,各方人口中引為談資,擁有龐大家的社網絡第二號締造人的樣子。
他隻是像是這個時候周圍很多捧著英文報紙讀報練習英語的年輕男一樣,靜靜地讀著手中那一份紐約時報。
仿佛注視著那些平地中驚起的雲波詭譎,波瀾滔天。
(未完待續)
猜你喜歡
-
完結3768 章
極品小神醫
一代小神醫勇闖花花都市,各色粉嫩妹紙瘋狂倒貼。手有醫道神術,花都任我行。專治一切病狀,更治各種不服。腳踩花都天驕,坐擁千萬美色。
715萬字7.82 122625 -
完結2737 章

上門龍婿
關於上門龍婿: “徐陽你配不上我!我們離婚吧!”“廢物,滾出我們林家,你配不上我女兒!”暗中幫助妻子,取得神話般事業的徐陽,卻被妻子和丈母娘嫌棄被逼離婚。離婚發現徐陽身份後,二人追悔莫及,丈母娘跪求:好女婿,別離開我女兒成不成。
457.6萬字8 153089 -
完結1070 章

和女友分手后,我的人生平步青云
錯過了國家發計委面試,遭遇女友無情分手;接著是父親鋃鐺入獄,他的人生被徹底改寫。鐘國仁意外重生,轉身進入省委辦公廳,從此開啟開掛人生……
197.1萬字8.18 31031 -
完結3969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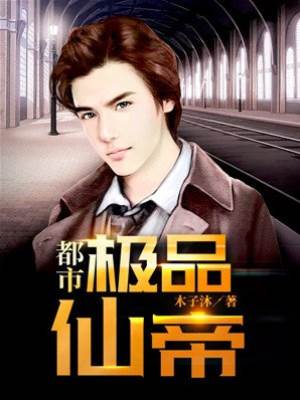
都市極品仙帝
一代仙帝落凡塵,不料竟成了冷艷總裁的上門人,為了保護枕邊人,從此恆顏林被迫開啟了在家吃軟飯,出門暗裝逼的極品生活。
791.1萬字8.18 26592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