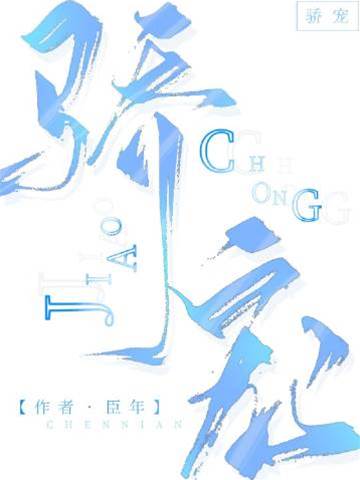《白日夢我》 第34章
第34章
聞紫慧確實是有點不喜歡林語驚了,大家都是一個班級裡面的,之間嘛,從古至今一向如此,要麼為好朋友,要麼就是階級敵人。
聞紫慧本來是很敬佩這個新同學的,開學的時候竟然跟沈倦坐一起了,但是敬佩的同時又有點微妙的小羨慕。
十六七歲的小姑娘,上不說,其實心裡對於帥哥同桌多多都有點小羨慕,雖然這個帥哥有點黑歷史,但這個年紀的孩子,大多喜歡壞男孩,校草的那點黑歷史讓他功變了校霸,反而好像更有吸引力了。
聞紫慧一直是那種很熱各種活的,剛開學的時候競選了文藝委員,去年的歌唱比賽,聖誕節晚會獨舞,運會的舉牌手都是,所以今年劉福江一說運會的事兒,的小姐妹就在說,這次肯定也是。
結果劉福江找了林語驚。
聞紫慧覺得自己被打臉打得太尷尬了。
林語驚最開始還拒絕了,後來不知道怎麼著,又答應了。
想就想,不想就不想,還拿什麼喬。
再看林語驚就怎麼看怎麼不順眼,但是只是想擋一下,再說兩句,沒有想要故意讓摔著。
本來就是,大家都在往上,就一個人往下走。
聞紫慧也沒看見旁邊倒著個瓶子,也沒想到林語驚怎麼就順著臺階往下摔了,就撞了一下而已。
聞紫慧有點慌了,那一下結結實實,離得最近,甚至聽見了「咚」的一聲,聽著都疼。
站在旁邊了一聲,還沒等反應過來,沈倦從後面拽著胳膊把扯到旁邊去,蹲在林語驚面前。
他力氣很大,手臂被拽得生疼,聞紫慧也顧不上了,站在旁邊呆愣又無措地看著還坐在地上的林語驚,看見小上有很長的一條劃傷,滲著,看起來目驚心。
Advertisement
聞紫慧嚇得臉都白了。
劉福江這個時候從另一邊跑過來了:「怎麼了,怎麼了都圍在這兒?」他走過來,「沈倦,你蹲哪兒幹什麼呢?你校服呢?」
沈倦沒回頭,旁邊有同學說了一聲:「江哥!林語驚摔了。」
劉福江趕過來:「摔哪兒了?摔壞了沒?哎喲,趕去校醫室看看。」
運會一般每個班的班主任和副班任都會在,不過這會兒副班任還沒來,就劉福江一個看著,他一時也走不開,場上瞅了一圈兒也沒看見王恐龍在哪兒,趕道:「別自己走了,都這樣了哪能自己走,沈倦,你背下去。」
林語驚抬起眼來,仰著腦袋看著他,旁邊同學都圍著在看,不想表現得太矯。
「不用,」林語驚說,「我自己下去吧。」
沈倦頓了頓,垂眸問:「能站起來嗎?」
他手裡拉著校服兩端,看起來像是從前面環抱住的姿勢。
「能,」抿了抿,抬手搭住他的手臂,子前傾,趴在他耳邊道,「你扶我一下。」
沈倦校服裡面穿了件白服,林語驚剛剛手按在他手臂上的那塊兒留下了一片跡,非常嚇人劉福江看看還在流的,又是「哎喲」了一聲。
沈倦索到背後校服拉鍊,「嘩啦」一下拉上來,扶著站起來,往下看了一眼:「這麼多臺階,你打算單腳蹦下去?」
林語驚額頭靠在他的鎖骨上,緩了緩,聲音疼得發虛,還在笑:「你當我的拐杖唄。」
「我還能當你的椅,」沈倦說,「你自己不要。」
他們倆一邊慢吞吞地往下一階一階走一邊說話,聲音很低,旁邊人聽得不清楚容,跑道那邊男子100米開始檢錄。
Advertisement
各個班級裡的短跑健將們——100米運員選手圍在一起,目送著林語驚和沈倦走過來,又目送著他們走過去,從3號門出了育場。
校醫室從育場走過去有一段路,兩個人一出了育場眾人的視線,沈倦直接拽著林語驚手腕勾在他脖子上,打橫將人抱起來:「你這個速度走過去,明天的運會都結束了。」
林語驚也不矯了,乾脆地抬手環住他,走了一段兒,忽然問道:「誒,你這樣算是椅嗎?我覺得不太準確。」
「那怎麼準確。」沈倦一手著蓋到大上的校服外套下邊兒問。
林語驚想了一會兒:「起重機?」
「……」
沈倦垂眼看。
乖乖地在他懷裡,雖然一直一副若無其事的樣子在跟他說話,但是整個人看起來都蔫的,像只了傷的小狐貍。
「行吧,」沈倦說,「那就起重機。」
校醫室在宿舍旁邊,獨立的一個小房子,門沒鎖,但是沒人,裡面四張床,每張床都隔著白的簾子。
沈倦把人放在最邊上的那張床上,林語驚坐在上面四下了一圈兒:「我們等一會兒?」
沈倦已經把窗邊的醫務車推過來了,看了一眼的,沒由來地想起了幾個月前,何松南的一句話。
——玩年啊倦爺。
林語驚確實好看,白得像細的酪,筆直修長,漂亮得像是人工的,挑不出一點病。
小側後的那一條劃傷顯得更為目驚心。
沈倦坐在床尾,一手握著腳踝,往上抬了抬,另一隻手著鞋跟,把鞋子下來。
大概是下去的時候蹭到臺階,水泥砌的臺階,邊緣鋒利,從腳踝骨到小下半段一掌長的傷口。
Advertisement
傷口上混著細碎的灰塵和砂石半凝固狀態,一直順著往下,染紅了子。
沈倦把子也下來,出白的腳。
林語驚有種說不清的不自在,反了腳,沒。
沈倦打開裝酒棉的玻璃瓶,沒回頭:「別。」
不了。
林語驚覺得耳朵有點燙,雙手撐著醫務室床面,上半往後蹭了蹭,結果到掌心破了的地方,一陣刺痛。
沈倦剛好又著鑷子,夾住酒棉清理上傷口上的灰塵和砂礫。
雙重夾擊,疼得「嘶」了一聲,腳趾頭一顆顆蜷在一起,手臂一,上半倒下去,砸進校醫室的枕頭裡。
他抬了抬眼:「疼?」
「不疼,沒覺。」林語驚側著頭,腦袋扎在枕頭裡,聲音悶悶地,「你作很練啊。」
像個寧折不彎的倔的戰士。
沈倦點點頭,用酒棉掉了一塊有點大的小沙粒。
林語驚痛得用手指不停地揪著枕頭邊兒,連腳背都繃直了。
沈倦哼笑了一聲:「小騙子。」
不服氣:「我這勇敢。抗戰時期我一定是不怕任何嚴刑拷打的英雄。」
「抗戰時期的英雄都像你這樣那沒戲了,你就差平地走路摔一跤,」沈倦抬把垃圾桶勾過來,將沾滿的酒棉丟進去,換了一塊乾淨的,「我就一眼沒看住你。」
「你說得好像我一直在你的視線裡一樣,沈同學,咱們開學才認識。」林語驚提醒他,道,「我之前的十六年也不知道你姓甚名誰。」
沈倦將鑷子放進注盤裡:「現在你知道了。」
他忽然抬起頭來,看著:「以後也得給我記著。」
Advertisement
年說著這話的時候,聲音低沉,平緩而悠長。
林語驚心跳莫名了兩拍,定了定神,側過頭去看他,彎著眼笑問:「這位同學,你好,請問你什麼名字?」
沈倦似笑非笑:「這就不記得我了?開學的時候是誰求著我,讓我給當爸爸?」
林語驚:「……」
-
林語驚也就兩隻手手心和小有點皮外傷,本來以為自己大概崴腳了,結果沒有,緩了一段時間,手腕和腳踝的痛漸散。
沈倦理起傷口來確實很練,十幾分鐘後,校醫回來的時候已經差不多弄完了,林語驚躺了一會兒,套著沈倦的校服當連穿,回寢室去換了套服。
紅子邊緣扯破了一點兒,林語驚換好服,在寢室裡原地跳了兩下,確定沒別的地方不舒服以後,慢吞吞地下樓,往育場走。
以前三天兩頭挨揍,蹭破點兒皮都不怎麼在意了,反正皮比較合,幾天就能結痂。
回到育館的時候是上午十點半,還有一個多小時午休,高二十班鼓聲激昂,加油聲此起彼伏,男子200米運員,拖把二號王一揚選手正在跑道上撒丫子狂奔。
王一揚曾經跟林語驚吹牛皮,有他的200米比賽,他第二沒人敢說自己是第一。
林語驚當時想起年在打群架時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飛撲出去一邊咆哮著「都來打我啊!打死我啊!!」的畫面,就信了,畢竟不是所有人都有那種恐怖的發力的。
結果今天一看王一揚跑步,差點笑出聲來。
年像是一匹小野馬,邁著大步兩個蹄子不停地捯飭,三兩步一個飛躍,特別帥氣地滯留在空中,像是面前有無形的障礙阻擋著他。
非常標準並且專業的110米欄跑法。
林語驚數了數,就這樣,居然還能跑個第三。
八中是真沒有什麼跑得快的選手。
一邊笑一邊往十班位置那邊走,宋志明正敲著鼓,停下了,顛顛跑過去:「哎,林語驚,你沒事兒吧?」
「沒事兒,就蹭破了點兒皮,看著嚇人,」林語驚擺了擺手,往上掃了一圈兒,沒看見沈倦。
也沒看見聞紫慧。
本來沒打算問,結果剛轉過頭,宋志明就一臉「我賊懂事兒」的表湊過來:「剛才沈倦把聞紫慧走了。」
林語驚一頓。
宋志明繼續說:「從大佬的表上來看,聞同學恐怕兇多吉,即將為第二幅被大佬鑲在牆上的油畫像。」
林語驚:「……」
-
沈倦其實現在很無奈。
他覺得他對自己的定位準確的,他只是一個脾氣非常好的、佛系高中生,但是僅僅只是因為他以前差點打死他的傻同桌,他被人傳得腥又暴力,讓人非常無可奈何。
他其實非常講道理,並不主張武力解決問題。
尤其是此時站在他面前的還是一個孩子。
本來小姑娘之間的事,沈倦不想管,林語驚本也不是會欺負的類型,那個戰鬥力和絕對不會於下風的刺兒頭格沒有人比沈倦更清楚了,他知道自己能解決得很好。
但是沈倦想起咬著牙說不疼的時候,在醫務室裡白著張小臉把腦袋埋進枕頭裡的時候,繃直腳背指尖死死地拽著枕頭邊的時候。
都讓他稍微有點兒忍不了。
沈倦本來是想講道理的。
結果聞紫慧跟著他剛走進育館,站在門口就開始哭。
剛開始還是噎噎地,後來變奔放的嚎啕大哭,一邊哭還一邊道歉:「沈同學,對不起,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就想撞一下,我沒想到會摔……哇啊嗚嗚嗚——」
哭得很慘,看起來真心實意,讓人有點不知道怎麼開口。
「……」
沈倦手在口袋裡,倚著牆站,神漠然看著:「你撞幹什麼。」
聞紫慧用校服袖口了臉上的淚,又鼻子,實話實說:「我嫉妒長得好看,本來舉牌的肯定是我的,一來就變了。」
「……?」
就因為這個。
沈倦懷疑這群姑娘是不是腦子都有點兒疾病。
他點點頭,從口袋裡出煙盒,咬了一,淡道:「你們姑娘之間的矛盾我不想摻和,但我見不得我同桌委屈,也見不得疼,你去給道個歉,想怎麼解決,你聽著,在我這兒就算過了。」
他出打火機,微微低頭,點燃,繚繞煙霧裡抬了抬眼,還非常善解人意地詢問對方的意見:「你覺得行嗎?」
猜你喜歡
-
完結96 章
再見及再愛
家道中落,林晞卻仍能幸運嫁入豪門。婚宴之上,昔日戀人顏司明成了她的“舅舅”。新婚之夜,新婚丈夫卻和別的女人在交頸纏綿。身份殊異,她想要離他越遠,他們卻糾纏得越來越近。“你愛他?”他笑,笑容冷厲,突然出手剝開她的浴巾,在她耳朵邊一字一句地說,“林晞,從來沒有人敢這樣欺辱我,你是第一個!”
17.2萬字8.18 20793 -
完結1965 章

盛寵名門佳妻
旁人大婚是進婚房,她和墨靖堯穿著婚服進的是棺材。空間太小,貼的太近,從此墨少習慣了懷裡多隻小寵物。寵物寵物,不寵那就是暴殄天物。於是,墨少決心把這個真理髮揮到極致。她上房,他幫她揭瓦。她說爹不疼媽不愛,他大手一揮,那就換個新爹媽。她說哥哥姐姐欺負她,他直接踩在腳下,我老婆是你們祖宗。小祖宗天天往外跑,墨少滿身飄酸:“我家小妻子膚白貌美,給我盯緊了。”眾吃瓜跟班:“少爺,你眼瞎嗎……”
284.1萬字8 29639 -
完結43 章

我的愛生生不息
雲知新想這輩子就算沒有白耀楠的愛,有一個酷似他的孩子也好。也不枉自己愛了他二十年。來
4.3萬字8 13074 -
完結493 章

甜心玩火:誤惹霸情闊少爺
訂婚宴當天,她竟然被綁架了! 一場綁架,本以為能解除以商業共贏為前提的無愛聯姻,她卻不知自己惹了更大號人物。 他…… 那個綁架她的大BOSS,為什麼看起來那麼眼熟,不會是那晚不小心放縱的對象吧? 完了完了,真是他! 男人逼近,令她無所遁逃,“強上我,這筆賬你要怎麼算?”
90.4萬字8 37776 -
完結77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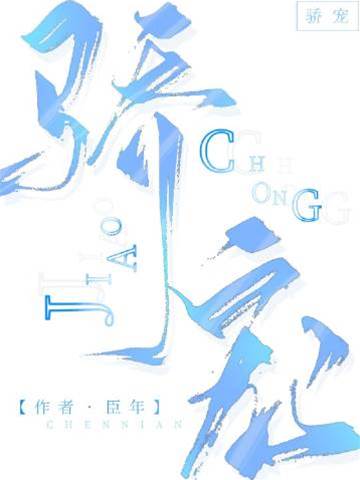
驕寵
作為國家博物館特聘書畫修復師,顧星檀在一次美術展中意外露臉而走紅網絡,她一襲紅裙入鏡,容顏明艷昳麗,慵懶回眸時,神仙美貌顛倒眾生。后來,有媒體采訪到這位神顏女神:擇偶標準是什麼?顧星檀回答:我喜歡桀驁不馴又野又冷小狼狗,最好有紋身,超酷。網…
31.3萬字8 4218 -
完結503 章

沈總別虐了,夫人和新歡約會上熱搜了
結婚三週年紀念日那天,沈澤撂下狠話。 “像你這樣惡毒的女人,根本不配成爲沈太太。” 轉頭就去照顧懷孕的白月光。 三年也沒能暖熱他的心,葉莯心灰意冷,扔下一紙離婚協議,瀟灑離開。 沈澤看着自己的前妻一條又一條的上熱搜,終於忍不住找到她。 將她抵在牆邊,低聲詢問,“當初救我的人是你?” 葉莯嫌棄地推開男人,“沈總讓讓,你擋着我約會了。”
36.8萬字8 3364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