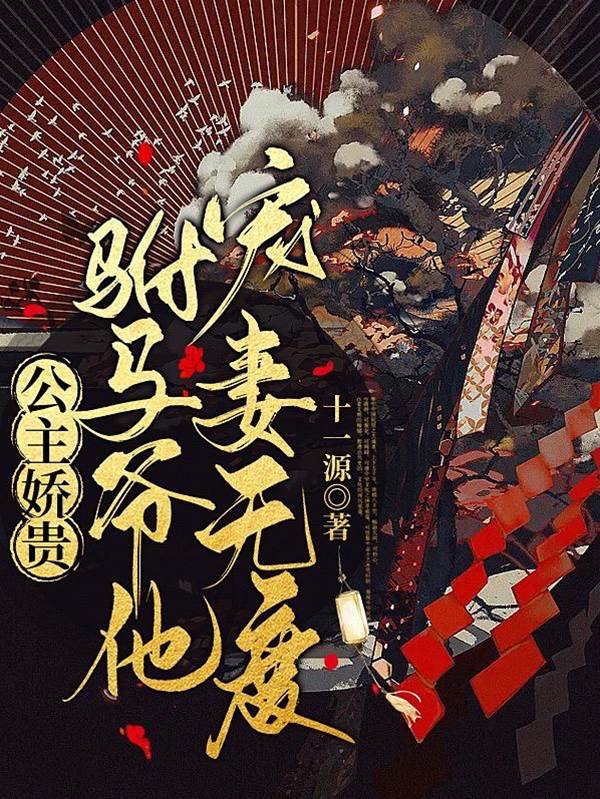《厲爺養大的小可愛要翻天》 番外 叛逆的“小閨女”
司寧從早上起來就一直在為明天出門努力,眼看到晚上了,男人也沒鬆口,心不好,胃口都不好了。
碗往前一推,筷子一放,剩了大半碗的米飯,“我吃飽了。”
“才吃幾口就不吃了?”厲寒霆蹙著眉看著他叛逆的“小閨”。
說他養了個閨真是一點沒說錯,從早上起來就一直反骨到晚上,他哄了一天,作了一天。
每天吃飯也是,心好了多吃點,心不好就跟今晚一樣,嚐幾口就不吃了,也不知道是誰慣的臭病。
“嗯,吃飽了,我去看電視了。”
隻是剛起,男人的大手就握住的手腕,“坐下,再吃點。”
司寧手腕掙紮了一下,沒鬆開,“我吃飽了。”
語氣有點不耐煩了。
“才吃幾口就飽了,這不是你的飯量,坐下,我喂你吃。”低沉的聲音已經染上了幾分厲。
Advertisement
說著已經鬆手開始去端麵前的碗,本來是要喂吃的,但是不讓,所以就由著自己吃了,結果就隻吃了幾口。
一點也不讓人省心。
“我不吃,我走了。”
說著已經抬腳準備走了。
“你要是敢離開這飯桌一步,我立馬把你關起來,我說到做到。”
他淡淡的說著,臉上沒任何表,但語氣中的不容置疑和男人眼神的威懾力,讓人不寒而栗。
司寧有點不敢了。
畢竟以男人的格,也不是沒有可能把永遠關起來,不敢冒險。
司寧怒氣衝衝的瞪著他,要是可以,真想罵人了,但又怕激怒對方,導致更嚴重的後果。
兩個人的視線在空中匯,彷佛有一無形的電流在空氣中劈裏啪啦作響。
Advertisement
片刻後,厲寒霆還是妥協了,“坐下再吃幾口,明天我帶你去。”
司寧先是愣了一下,隨後臉上出不敢置信的表,連忙坐回凳子上,瞪著圓溜溜的大眼睛湊到男人跟前,急切的問:“你真的同意了?”
厲寒霆沒回答,隻是默默的夾了一口菜喂到邊。
這一次司寧乖乖的張吃了,兩邊腮幫子鼓鼓囔囔的,活像一隻可的小倉鼠。
隻是沒得到確切的答案,一雙大眼睛依舊一眨不眨的盯著男人看。
的眼睛很明亮,就像現在一樣,像是
看炸了一天的終於順了不,厲寒霆無奈的在心裏歎了口氣,真是拿毫無辦法。
“有且僅有這一次,再有下次,說什麽我也不會同意,聽明白沒?”
司寧瞬間笑靨如花,抱著男人的胳膊高喊,“老公萬歲!”
Advertisement
厲寒霆沒忍住笑出聲,“怎麽,答應你就老公萬歲,不答應就在心裏罵我是嗎?”
以他的經驗,這小妮子今天可沒罵他。
司寧有覺小心思被穿,不好意思的抓了抓頭發,臉頰微微泛紅,“哪有啊,老公可是全天下最好的人,我才不舍得罵呢!”
“是嗎?那親一下我就暫且信你。”說著男人已經將臉往孩兒跟前湊近了幾分。
“……”
就跟親了一下,就真的會信一樣。
不過還是在男人的上親了一下,“mua……”
厲寒霆直接哪裏滿足這蜻蜓點水的吻,扣著孩兒的腦袋加深了這個吻。
吻完還不忘讚賞了一句,“嗯,表現不錯,晚上給你個福利。”
???
這哪是給福利,分明就是給他自己的福利。
說的倒是冠冕堂皇的。
猜你喜歡
-
完結302 章
一胎三寶:大佬媽咪颯爆了
回國參加叔叔的葬禮,墨曉曉竟然被嬸嬸和妹妹陷害失了身!遭衆人唾棄!被監禁,那一夜她逃生,竟被神秘大佬相救!五年後,她帶三寶強勢迴歸!回來直接一紙合同甩在嬸嬸臉上,讓她掃地出門!五個大佬急不可耐迎接墨曉曉,卻恰好碰到那個一手遮天的程三少!“墨小姐,我看你眼熟……”
53.3萬字8 19833 -
完結12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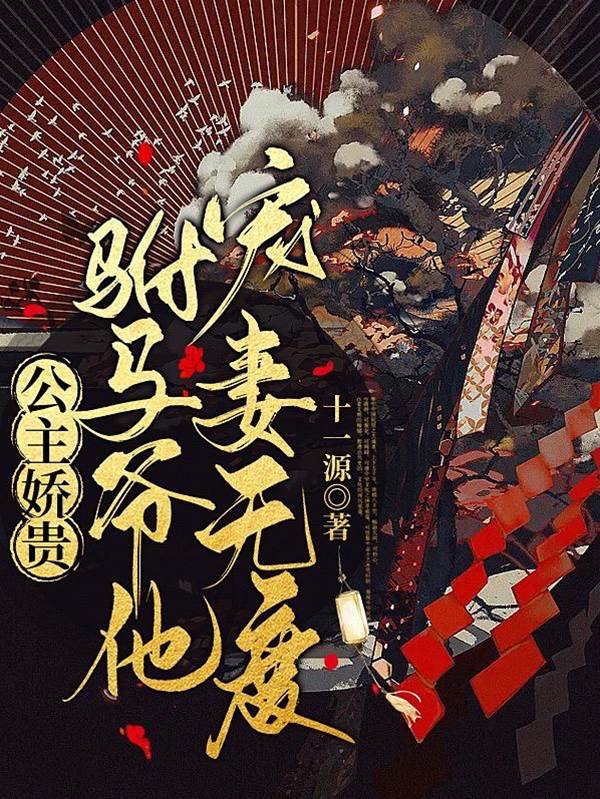
公主嬌貴,駙馬爺他寵妻無度
【1v1 、甜寵、雙潔、寵妻】她是眾星捧月的小公主,他是被父拋棄的世子爺。幼時的他,寡言少語,活在無邊無際的黑暗中,是小公主一點一點將他拉出了那個萬丈深淵!日子一天天過,他成了溫文儒雅的翩翩公子,成了眾貴女眼中可望不可及的鎮北王世子。可是無人知曉,他所有的改變隻是為了心中的那個小祖宗!一開始,他隻是單純的想要好好保護那個小太陽,再後來,他無意知曉小公主心中有了心儀之人,他再也裝不下去了!把人緊緊擁在懷裏,克製又討好道:南南,不要喜歡別人好不好?小公主震驚!原來他也心悅自己!小公主心想:還等什麼?不能讓自己的駙馬跑了,趕緊請父皇下旨賜婚!……話說,小公主從小就有一個煩惱:要怎麼讓湛哥哥喜歡自己?(甜寵文,很寵很寵,宮鬥宅鬥少,女主嬌貴可愛,非女強!全文走輕鬆甜寵路線!)
21.6萬字8 12884 -
連載1055 章

捉jian當天,豪門繼承人拉我去領證
《甜寵+先婚后愛+男主扮豬吃老虎》 婚禮前一日,蘇錦初親眼目睹未婚夫出軌,和陌生女人在婚房里滾床單! “你未婚夫do的是我女朋友。” 同來捉奸的男人俊臉靠近,輕聲在她耳邊提醒。 蘇錦初又委屈又難過,偏偏第二天的婚禮不能取消。 “我可以和你結婚。” 在渣男的冷嘲熱諷下,才一面之緣的男人拉她去民政局。 其實從一開始蘇錦初就猜到,和她閃婚的顧明琛不是一般人。 他氣質矜貴、出手闊綽、住著豪宅、開著豪車,還能養得起女模特! 可是卻怎麼都沒想到,公司年會上,期待一向神秘的繼承人出場,卻看到昨天晚上跟她睡一張床的男人出現! “我們未來老板長得真好看,可惜,就是不近女色。” 女員工們露出花癡地表情,閃著星星眼望著臺上的男人感嘆。 蘇錦初:“……” 想到昨天晚上纏著她要了又要,害她早晨差點上班遲到的男人……果然傳聞不能信! ...
209.7萬字8.18 44162 -
完結616 章

慕爺,團寵夫人又掉馬了
人人都以為她是鄉下福利院出來的野丫頭,卻不知她是馬甲遍布全球的大佬,翻手為云覆手為雨。當馬甲一個個掉落。眾人驚掉下巴。“餐飲帝國老板。”“頂級設計師”“逆天醫術
92.2萬字8 47394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