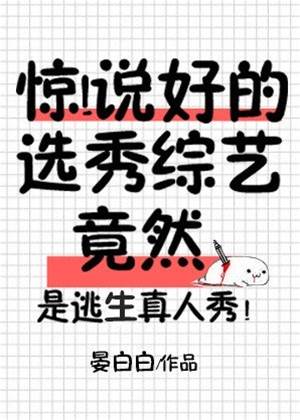《《飛鷗不下》》 第3章 離我遠點
魏獅的當鋪“興旺當鋪”,有生意興旺之意。
真到上工時,我發現自己管的人要比魏獅說的多那麽一點,有三個——財務柳悅,夥計沈小石,還有個給我們專門做飯打掃的老嬸,姓王。
當鋪這行當,聽著好像怪嚇人的,總覺進去了就要失去點什麽。上到你媽給你的金項鏈,下到一生限量倆的寶腎,沒有它不要的。
其實是妖魔化了。
當鋪也不過線下以錢易、公平易的平臺,只要要得起的,其余的半點不會。
電子聲機械地吐出“歡迎臨”四個字,我從正看得津津有味的《知音》上抬起頭,見一打扮時、長相英俊的花襯衫男推門而,知道是生意來了。
魏獅這選址很講究,店面就在一家夜總會和大型購商場的接。公主爺們收到了禮,可以來這邊快速套現,逛膩了商場的遊人,也可進來看一眼稀奇。
眼前這人一臉風流,襯衫扣子恨不得開到肚臍眼,墨鏡一摘,首先就給柳悅飛眼,顯然是前者之列。
“老板,給估一下這隻表多錢。”他將手中的紅皮盒過當口遞給我。
“哎呦,名表啊。”沈小石本在門口沙發上當門神刷手機,見有生意上門,也過來湊個熱鬧。
我將手裡雜志丟到一邊,戴上白手套,取過高倍鏡開始工作。
金屬表盤和表帶沒有明顯劃痕,logo清晰,指針漆面正常,針尖尖銳,翻到反面,大小齒嚴合地運轉著,工藝完。
“這表很新啊。”像這樣的一支全新男表,說也要二十萬。
花襯衫臉上浮現一抹得意:“最近新認識的一位送的,我一次都沒戴過,全新的。”
Advertisement
我將表放回盒子裡,向他說了這邊的估價:“你要是死當就是十二萬,活當一個月十萬,三個月八萬。”
花襯衫笑臉凝滯,不敢置信地瞪我:“你砍得也太厲害了吧,這表全新的我一次沒戴過的。二十萬你不願出,好歹給個十五萬吧?”
我扣上蓋子將皮盒推回去,不不慢跟他討價還價。
“十三萬,辦妥手續可以立刻到帳。”
他低頭糾結地思索片刻,一咬牙,終還是疼地將那隻紅皮盒推給了我。
“。”
沈小石暗暗給我比了比大拇指,我給花襯衫寫單據時,他過來拍了好幾張高清照,又悄悄問我出價多。
當鋪有個微信號,好友足有三四千,沈小石是皮下營運兼客服兼銷售,一有死當的新貨,他會第一時間拍下標明價格發去朋友圈。
“十五。”我衝他小聲報了個數。
當鋪賺得都是快錢,以盡快手為佳,價格開得過高讓人而卻步是下下策。我們一直秉持著“賺得也比東西爛手上強”的原則,願賺,也不能賠錢。
魏獅總說我做這行有天賦,是好苗子,我知道他這大多是場面話。要是會殺價也算天賦,那我媽一定是骨骼清奇的天縱奇材。
“薩沙?”我看著單據上瀟灑的花簽名,直接皺了又給了花襯衫一張,“要填真名。”
他撇撇,這次接過老實地寫上“方磊”兩個字。
“,有空找我玩啊,酒水給你打八折。”
收好單據,檢查了銀行進帳,花襯衫與柳悅搭了幾句話,遞給一張香噴噴的名片。
柳悅笑笑接過了,將那隻十三萬的表鎖進了保險箱。
花襯衫走後,沈小石重新躺回那張舒適的皮沙發裡,高舉著手機,裡發出一聲慨的歎息。
Advertisement
“長得帥真好啊,什麽都不做就能得十三萬。十三萬呢,我兩年的底薪。”
柳悅將電腦桌面切回之前看的狗韓劇,隨意地接著話:“長得也不算很帥,沒我豆耐看,就是材好的,那賊大……”低頭看了眼自己口,憾地搖了搖頭,“反正要是我有二十萬,絕對不會買表送他。那表他一次沒戴,轉手就當了,顯然沒有幾分真心。哎,不如追星。”
“有二十萬給牛郎買表的會只有二十萬嗎?九牛一罷了。”我拿起桌上雜志,翻到之前正看的那篇《墮落的救贖》,十分自然地加了他們的對話。
“這倒也是。我每天下班都要路過那個‘金年華’,六點門口就開始來客人了,開的都是好車,賓利法拉利拉博基尼,跟大型車展會一樣。”柳悅道,“之前經常來的那個珍妮還有珠珠就是裡面的公主。每隔一段時間都要把客人送的包拿過來當,一當都是七八個名牌包一起,看得我目瞪口呆的。”
“你怎麽知道們是公主?”那兩個人我倒是記得,的確每次來都很多包,但因為來的時候都是素,皮糟糕,臉憔悴,活似打了三天三夜的通宵麻將,我隻以為們是開中古店的。
“我加了們好友呀。”柳悅擺了擺手機,“們每天真的,不是在謝這個老板送的鑽,就是在謝那個老板送的包,看得我都要仇富了。”
沈小石忽然從沙發上跳起來:“哇,有人要了!”
我同柳悅被他嚇了一跳,齊齊看向他。
他吹了聲口哨:“十五萬的表,手了。”
花襯衫的表剛上朋友圈展示不足半小時就有人吃下。鑒於是的貴重品,容不得磕磕,又問明客戶正在清灣市出差,住在市中心一家五星級酒店,於我回家正好順路,便約定晚上親自給他送去。
Advertisement
到底十幾萬,我也不敢坐地鐵,怕有閃失,就了輛出租車直達酒店,打算回頭再找魏獅報銷。
酒店是座高聳的天大樓,外牆玻璃盡顯夜晚的璀璨霓虹,大堂通典雅,熏染著沁人的香氣。
許是今天有什麽酒會活,不人自門口下車,穿著正裝晚禮服步酒店,香鬢影,一派上流氣象。
只是等我一進去,大概我這一邋遢的穿著實在不像這裡的客人,便有門問我需不需要幫助。
“我找人。”
與客戶說了我已到達,客戶回的很快,讓我等等,說他馬上下來。我衝門笑笑,走去一旁的沙發會客區。
還沒等我落座,門口停下一輛線條流暢的銀跑車,讓我不由多看了兩眼。
從副駕駛座下來一位材婀娜的年輕,裹的紅將的腰肢收得極細,微涼的天氣下,在肩頭披了條黑羽的披肩,卷發紅,十分豔。
扭繞到駕駛座,等到駕車的男人開門下車,便嫻地勾住對方的臂彎,如王一般踩著高跟進酒店的旋轉門。
我站在那裡,目一錯不錯落在旁的男人上。
幾天而已,想不到咱們又見面了。
他與之前大多男士一樣,穿著正式的禮服三件套,戴著黑領結,口出一角雪白的帕巾。
不一樣的是,他材很好,扣了腰間的一粒扣子,更顯猿臂蜂腰,高長。
他們要進電梯,就要經過我,經過我,盛珉鷗便不可能對我視而不見。而這時盛珉鷗也的確看到了我,並且下意識停下了腳步。
他眼裡一剎那湧現出讓人膽怯的寒意與狠毒,仿佛一位無人敢忤逆的暴君,驟然發現自己床上竟然躺著一隻骯髒的虱子。
Advertisement
拂去就好?不,虱子縱然渺小不值一提,也不意味著它能隨意冒犯。過眼神,我便明了他有多想將我這隻“虱子”以極刑,碾死在當下。
但也只是一剎那,眨眼功夫,裹著冰霜的惡意褪去,他又人模人樣起來。
“這是……”紅視線在我和盛珉鷗間來回移,目疑。
盛珉鷗垂首朝勾起抹得的微笑,啟正要說什麽,我先一步截住了他的話頭。
“哥,這是誰?”我笑著問他,“不會是你朋友吧。”
盛珉鷗邊的笑意一僵,斜睨過來的眼眸,冰冷比方才更甚。
他緩緩開口:“他是我弟弟。”
有些錯愕:“你還有弟弟?怎麽沒聽你提過?”
我無畏地直面他刀鋒一樣的目,又是一笑:“因為我這十年都在坐牢。”
臉一白,驚疑地打量我。
盛珉鷗徹底沉下臉,扯出被挽住的胳膊,道:“沫雨,你先上去,我和……我弟說兩句話就來。”
那似乎還想問什麽,但此時外面又來了幾位打扮隆重的男,像是怕被人注意到,一下閉了,整理好表,朝盛珉鷗微一頷首,刮著香風離去。
走後,盛珉鷗看也不看我,沒有說一個字便往外走去,似乎篤定我一定會跟上他。
我扯了扯角,等他走出一段,拖著腳步跟了過去。
盛珉鷗倚靠著酒店外牆,低頭攏住火,點燃了上的煙。
深吸一口氣,再緩緩吐出,橘紅的火在暗夜裡閃爍,他夾住煙,眉眼因朦朧的煙霧顯得有幾分頹然。
我走向他,試圖活躍氣氛:“怎麽,真的是你朋友嗎?”
“陸楓……”他低沉的嗓音過夜風傳過來,我微微愣神。
十年了,這還是十年來我第一次聽他我的名字。
他住我,再不掩飾自己的涼薄兇狠。
“離我遠點。”
猜你喜歡
-
完結270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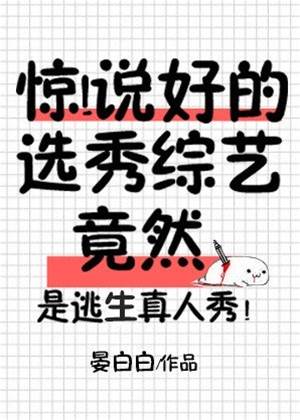
驚!說好的選秀綜藝竟然
某娛樂公司練習生巫瑾,長了一張絕世美人臉,就算坐著不動都能C位出道。 在報名某選秀綜藝後,閃亮的星途正在向他招手—— 巫瑾:等等,這節目怎麼跟說好的不一樣?不是蹦蹦跳跳唱唱歌嗎?為什麼要送我去荒郊野外…… 節目PD:百年難得一遇的顏值型選手啊,節目組的收視率就靠你拯救了! 巫瑾:……我好像走錯節目了。等等,這不是偶像選秀,這是搏殺逃生真人秀啊啊啊! 十個月後,被扔進節目組的小可愛—— 變成了人間兇器。 副本升級流,輕微娛樂圈,秒天秒地攻 X 小可愛進化秒天秒地受,主受。
89.5萬字8 8616 -
完結135 章

原來我老公才是真少爺
池亦真穿成了一本娛樂圈甜爽文的悲慘白月光。不僅被原作攻強取豪奪導致家破人亡,還被主角受當做整容模板,最后險些身敗名裂黯然退圈……看文的池亦真想:是我就瘋了。結果他一覺醒來發現自己身處酒店邊上還躺了陌生男人……池亦真:絕對是陷阱,快逃!!!…
43.8萬字8 886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