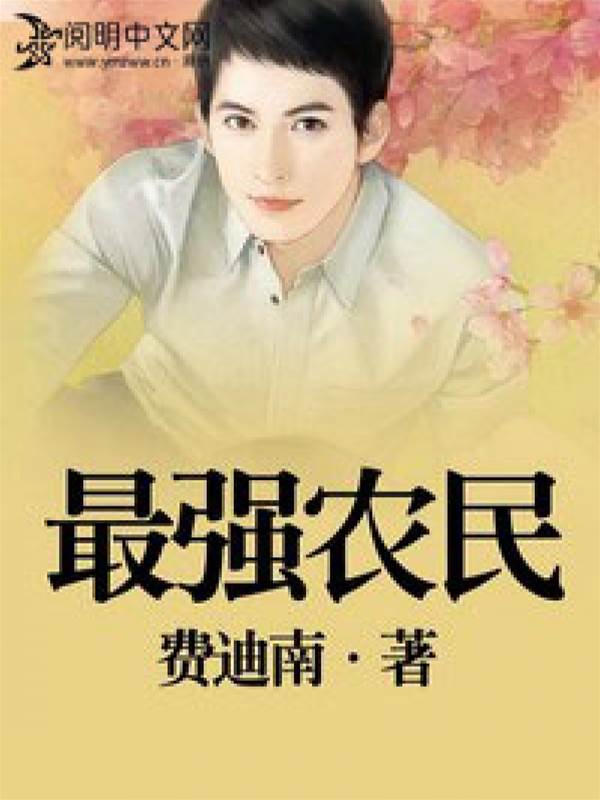《如影隨形》 ……帶我去哪兒?
駱寒東松開手裡那顆腦袋,轉過問,“誰開的門?”
這下不用誰說,其中一個就跪在地上磕頭了,“我,但是我……我沒別的意思,我……啊啊啊——”
他的手臂直接被駱寒東以反方向擰著直直卸了。
他趴在地上哭嚎不止,駱寒東嫌他吵,衝邊上羅鑫的男朋友趙河說,“把子下來,堵住他的。”
趙河戰戰兢兢地照做了。
駱寒東渾還淌著水,他嘲弄地看著趙河,角扯了扯,“不是你兄弟麼?見死不救?”
趙河猜不面前的男人什麼想法,只是害怕地搖頭,“……不,我本沒參與,我就是……住我朋友這兒,然後他們看到你朋友回來,覺得長得好看,然後他們就想……不關我的事啊……”
“不關你事?”駱寒東目森冷地睨著他,“你就是禍源,沒有你的存在,也不會有他倆。”
他說完話,照著男人的臉一腳踢了過去。
直接把趙河踢暈。
盛夏在房間裡聽完兩首歌之後,駱寒東開門進來了,他上噠噠的,頭髮還在往下滴水,黑襯衫在上,子都把他間的某勾勒得十分清晰。
Advertisement
盛夏垂著眼睛找巾,找到一條乾淨白巾,遞了過去。
駱寒東卻是接了巾給了腦袋,隨後把巾丟在一旁,拿了的手機,又把人抱著往外走。
出來時,盛夏才看見外面三個男人的慘樣。
一個滿臉是趴在地上,一個裡塞著子,胳膊以扭曲的姿勢反擰在後,另一個暈在一邊。
地板上還有一顆帶的牙齒。
看得心驚,男人卻抱著目不斜視地往外走。
直到走出去,盛夏才想起來問,“……帶我去哪兒?”
駱寒東不答反問,“你還要回去住?”
盛夏咬了咬,“……不是。”
駱寒東服雖然,但卻十分熱燙,盛夏被他抱在懷裡,隔著服,被他滾燙的幾乎灼傷。
還有……他平穩有力的心跳。
隔著服像一面鼓,一下,又一下地敲在心頭。
盛夏有些不自在地扭了扭,“……我可以自己走。”
駱寒東沒理,徑直找到自己胡停在路邊的車,把人塞進去就往前開。
Advertisement
他雖然是開車來的,卻渾都了。
意味著,他起碼在雨地裡跑了……五分鍾。
盛夏不敢猜他在雨地裡奔跑的心,但此刻的心……已經忐忑不安了。
東哥……要帶去哪兒?
下了車,看見是公司樓下,松了口氣。
男人要來抱,盛夏拒絕了。
駱寒東卻是強地抱住,聲音很冷,“走太慢了你。”
盛夏對上他漆黑的眸子,陡地就沒了聲音。
男人……分明就是找借口想抱。
盛夏偏頭不去看他,可進電梯時,四面八方的金屬門映照著男人的臉,他眉間的疏冷淡了些,眸子裡映出些許意。
盛夏低著頭不敢再看。
擔心……自己會忍不住淪陷。
他是壞人。
不要跟他再有任何接了。
盛夏在心裡說。
猜你喜歡
-
完結288 章
美豔妖婦
“我不是神仙,我是妖怪。”梅說。我哈哈大笑,說她這麼漂亮,怎麼可能是妖怪。而之後我和梅相處的日子,一直都很平淡,梅做些糖巧點心在村裡售賣給小孩子,來維持生計。我給她跑腿幫忙,還能免費吃糖。
70.2萬字8 25379 -
完結105 章
蘇桃的性福生活
蘇桃本是京城商戶之女,年方十六,為了求得一個好姻緣隨娘親去音源寺廟上香,不想被個色和尚盯上破了身。 失貞女子如何能嫁人,不想男人一個接一個的來了。
19.2萬字8.09 238492 -
完結34 章
帳中香
千百年后,丝绸古道之上仅余朔风阵阵、驼铃伶仃。 繁华旧事被掩埋在黄沙之下,化作史书上三言两语。 甘露三年,豆蔻年华的华阳公主和亲西域,此后一生先后嫁予两位楼兰君王,为故国筹谋斡旋,终除赵国百年之患,令匈奴远遁,漠南无王庭,成为一人抵千军万马的传奇。 *西域主要架空汉,部分架空唐,找不到史料参考的地方私设众多 (雙性,NP)
9.1萬字8 11660 -
完結50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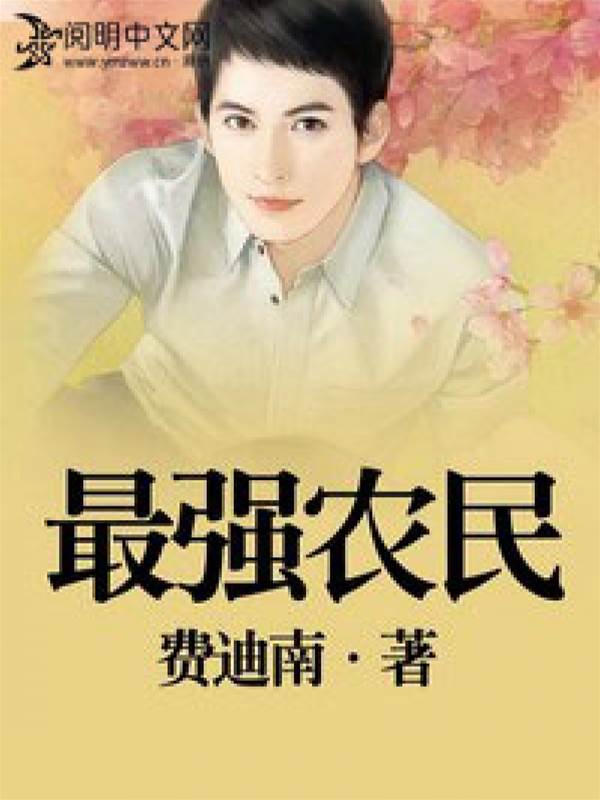
最強農民
作為世界上最牛逼的農民,他發誓,要征服天下所有美女!
14.3萬字8 10786 -
完結58 章

完美愛戀
歐陽雨強忍著將要掉下的眼淚,勉強的露出一個笑容,“媽,你放心,我一定會讓咱們家里過上好日子的,你們一定要好好照顧爸爸,知道嗎?”歐陽雨依依不舍的跟媽媽緊緊抱著。
13.8萬字8 8762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