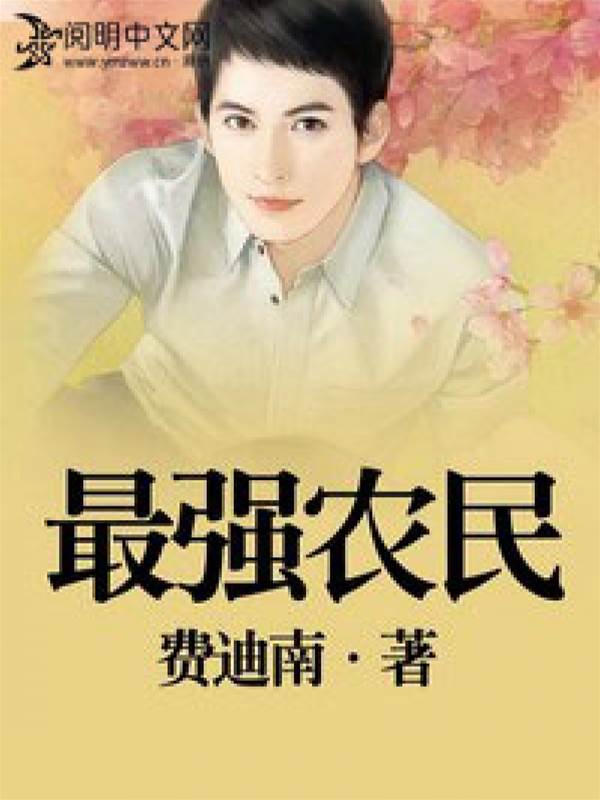《龍神是個騙炮狂》 第二十九章 失蹤
鳥鳴啁啾,晨熹微。
不知在黑暗中坐了多久,直到窗欞上飄來一線霧天,夏天才驚覺已是清晨。
手邊的茶已經涼了。潤的瓷甌上留下一圈水霧,淋淋漓漓地躺著些水珠,像淚。
昨夜發生的一切,於皆如大夢一場。
除了最後,墨離那個無聲離去的背影。
他什麼都沒有說,只是輕輕解開了夏天圈著他的手臂。
話已經問到了這種地步,饒是夏天知曉自己愚笨,也不可能再裝糊塗了。
墨離果然是不喜歡的。
不喜歡到,連一個拒絕的理由都懶得去想。
再是沒臉沒皮,夏天也知道自己不能一直糾纏下去。
於是只是坐著,目送那一方素白的人影,默聲行遠,融與他一樣清冷的月之中。
側不遠有一方水鏡。裡面的子墨發披散,面蒼白,不見了原先的明,眉宇間只剩下化不開的愁緒。
是呀,只是一隻平凡又卑微的小妖,竟然會妄想能夠得到墨離的喜歡?
終究是太貪心了。
有了擁抱想要一個吻,有了吻,卻又奢一張床。
夏天覺得腔裡有一蒸騰的氣息在上升,衝得鼻眼酸。
癟了癟,翻趴在了地上。
不行!不能讓它上來!
要將這惱人的酸下去,下去。
當晨間的一縷破窗而的時候,小屋空了。
一切的什都是原樣,夏天什麼都沒帶走,隻穿走一件墨離的大白袍。
Advertisement
那盞涼的茶甌下了一張紙條,上面歪歪扭扭地留下了幾個難以辨認的字跡。
離開墟歌浮島的時候,夏天隻拎了的小靈囊,揣上了幾日的吃食。
師父還傷著,不能跟一起走。大魔頭雖然不喜歡自己,可是已經這樣表了決心,不會再多糾纏。多收留師父幾天,想必也不算為難他。
只是現下沒了師父在邊,食也已經消耗得七七八八,百妖嶺又不能回去,夏天一時也不知該去哪裡好。
之前本是打算去人界的。
雖然法力低微,可原的皮囊也算是上品之相。盤算著若是到了人界,運氣好的話,便能在王公貴胄的宅院混個生慣養的寵當當。
雖然沒什麼尊嚴,但好歹是不會肚子的。
可是從未去過人界。如今這麼一走起來才知道,人界原來這麼遠。
六日已過,卻是連人界的口都還未有看到。
真是愁得掉。
天上不知什麼時候下起了雨。
秋日的雨總是著一涼氣,饒是不起什麼風,也能凍到人的骨子裡去。
“阿嚏!!”
一個驚天地的噴嚏從口鼻跳出,夏天摟住自己的袍子,躲進了一破廟。
那小廟的屋頂已經塌了一半,只剩下一個柱子,勉力支撐著搖搖墜的屋簷。
四周的牆壁都是破的,冷雨從四面八方嘩嘩地灌進來。夏天覺得,若是風再大幾分,就能要了的命。
Advertisement
找來一堆草,又從牆角搜羅來幾木。待費盡九牛二虎之力才將草點燃之時才發現,草和木頭都不夠乾。燃了也不出火,只是絮絮地往外冒著黑煙。
夏天隻得作罷。
腸轆轆,手腳僵冷,困倦難忍。將自己蜷起來,到牆角,冷到發白的小手抱住膝蓋,將頭也埋了進去。
曾經也流浪過的。挨過,過凍,這樣的景也時常會遇見。
沒關系的,司空見慣,家常便飯。
練地安自己,卻在埋頭的那一刻嗅到了屬於墨離的那一清冷疏淡的松木香氣。
饒是現下冷得骨,夏天也覺得那袍上還留著獨屬於他的溫暖。
只是從今往後,關於他的所有記憶,也只剩下這件袍子了。
夏天的角不自覺癟了癟,卻被以一個哈欠搪塞了過去。
將沾了雨水的袍角擰乾,小心翼翼地攏進自己懷裡。
哈欠打完了,順理章地帶出了眼淚。
風雨嗚咽之中,在那個屋簷下泣不聲。
打在破廟的冷雨,此刻也打在室的窗欞上,淅瀝瀝的,像一條小溪被挪到了屋側。
簷下一隻的青鸞被忽然的狂風一吹,驚著飛遠了。
墨離就在這一聲驚中醒了過來。
自那一晚從寢屋裡出來,墨離就一直將自己鎖在室。
他這幾日一直渾渾噩噩,不諳天日。什麼時候醒,什麼時候睡,自己也不知曉。
只是無論睡或醒,這幾日的墟歌浮島都很是安靜。
Advertisement
大約是因為妖月和昊悅了重傷,還睡著,幾人沒有辦法再夥同小傻貓喝酒行樂了吧。
他抬眼了窗外的秋風冷雨,思緒飄到了山腰的那小屋。
上似乎還留著夏天溫的余香。
那日,纖細的手臂巍巍地圈住墨離,怯生生地問他,可不可以也喜歡。
心跳忽然了一拍,有些異樣的陌生滋味。墨離不自覺地捂住心口,將晦暗的視線從窗外收回。
一些事,於他人而言或許只是船到橋頭。於墨離,卻偏生是終極難題。
畢竟,本能教給他的只有殺戮,天道留給他的也只是冷漠。
小傻貓要的那樣東西,於他而言,實屬陌生。
墨離覺得實在不該問一隻折了翅的鳥兒,飛起來是何覺。
就像是不該問他這個缺了魄的人,可不可以分出一點喜歡。
一陣狂風,帶細雨,梨花木的地板上,很快就是跡一片。
墨離起要去關窗的時候,才察覺到的異樣。
站起來的一剎那,他隻覺兩眼發白,頭腦一熱,險些摔了下去。
他手了自己的額頭,那裡是滾燙的溫度。
墨離心下一凜,即刻念了個訣,製住幾炸裂的頭,然後徑直往夏天的小院奔去。
敞開的門扉之後,是妖月和昊悅同樣焦急的影。
昊悅甫一見到墨離,便不可自製地暴怒起來,他猛然上前一步,作勢要去揪墨離的襟口。卻礙於這將將複原的,又險些吐出一口來。
Advertisement
妖月見到墨離,隻泫然泣地遞給他一張紙條。
有些昏暗的燭火下,他看見上面畫著一隻小貓,背著小小的包袱,出了一座島。
那島上站著個著白袍的小龍,小龍邊有一堆魚。
墨離笑了,轉而又了眼眶。
因為小傻貓走了,走的時候,還希他能有吃不完的魚。
紙條上只寫了兩個字,一筆一畫甚是認真,可還是醜到幾乎難以辨認。
墨離。
他的名字。
他都要忘了,夏天是一隻貓,不會寫什麼字。
這歪歪扭扭的幾個字,也許已經用盡了所有的努力。
正如那晚,那句躊躇良久才敢問出口的話。
——————
墨渣渣,就問你現在慌不慌?
猜你喜歡
-
完結48 章

霸上嫂子
小說的主人公是楊浩和沈思慧,此書主要講述的是在哥哥不在家的時候,楊浩與自己的美豔嫂子沈思慧之間發生的那些事,楊浩對沈思慧早就有著非分之想了,恰巧碰上這一次千載難逢的好機會,他會如何呢?
4.3萬字7 374334 -
完結265 章
穿進肉文被操翻了怎麼辦
(全文終,結局1v1。本文各種天雷滾滾、瑪麗蘇、肉到吐請自帶粗長避雷針)女大學生薛知曉有個小秘密,就是夜深人靜的時候躲宿舍被窩裡如饑似渴的看肉文,並把自己代入女主。。結果自己掉進看過的肉文各種各樣的play裡。。。 ========================================================= 人前知性賢慧、聰明能幹的大學學生會主席薛知曉,內心卻極度悶騷極度性饑渴。 走在路上,視線會瞄向男人下體,想像這個強壯帥氣的男生被自己的美色誘惑,雙眼泛綠光的把她就地撲倒,撕爛她的衣服並把大雞巴捅進她滴水饑渴的淫穴裡頭。。。 因緣際會,她終於得償所願被投進了一部又一部她無數個深夜裡擼過的肉文裡頭,過上她渴求的沒日沒夜和各類帥哥型男各種啪啪啪、幹得她淫水直流爽上天的日子。。。 然而,這些日子她只想存在於她的性幻想裡頭,並不想成為其中的女主角被這樣那樣的狠狠操翻啊親~~~~~~~ =================================
26.7萬字5 329650 -
完結614 章
快穿之【枕玉嘗朱】
此為快穿之[玉體橫陳]第二部,單看並不影響閱讀,大家也可以選擇補一,也可選擇直接看二哦~要看第一部在下方連結 黎莘作為一個被砸進快穿系統的OL, 執行的任務就是破壞原著劇情,勾搭男配男主。 經歷了系統1.0的折磨(誤),黎莘自認已經養成了百毒不侵的體質。 然而一次解密世界,卻將她置於兩難境地。 為了解開最後的謎團,她躊躇滿志的面對全新的挑戰,然而係統無情的告知,這一次,她不僅要得到攻略人物們的身,還要得到他們的心…… 已完成CP: 正在進行時CP:【穿書•現代篇】心有明月 (偽白蓮腹黑大小姐×面癱呆萌鬼畜殺手by萬俟月醴) 預告: 黎莘是紹澤煬心中的白月光,是他可望而不可及的夢中情人。 當她因黎家人的過失意外故去後,紹澤煬瘋魔了。 他囚禁了與黎莘有七分相似的黎妤,親手毀去黎家家業,並從此走上與黎妤相愛相殺,虐心虐身,你追我趕的道路。 ——對此,黎莘只想表示。 (豎中指) 沒錯,她穿書了。 穿到了一本
48.5萬字8.43 210360 -
完結50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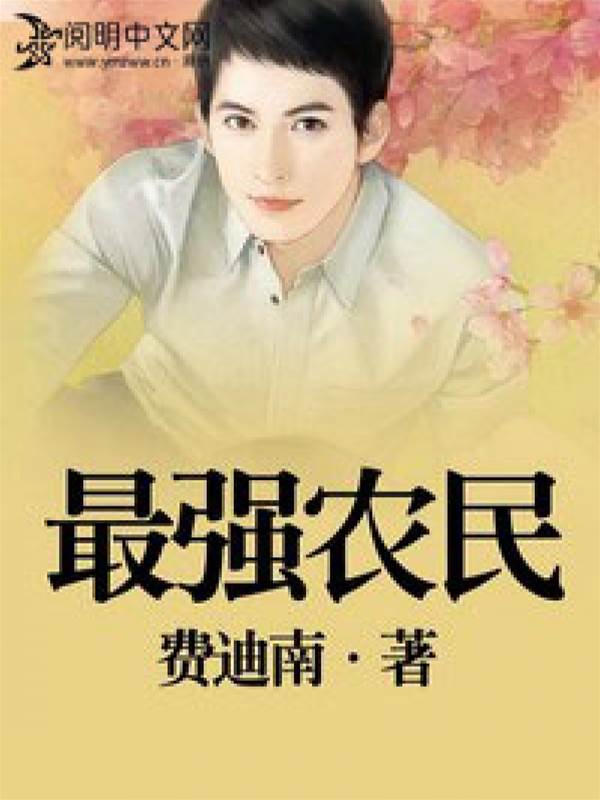
最強農民
作為世界上最牛逼的農民,他發誓,要征服天下所有美女!
14.3萬字8 12613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