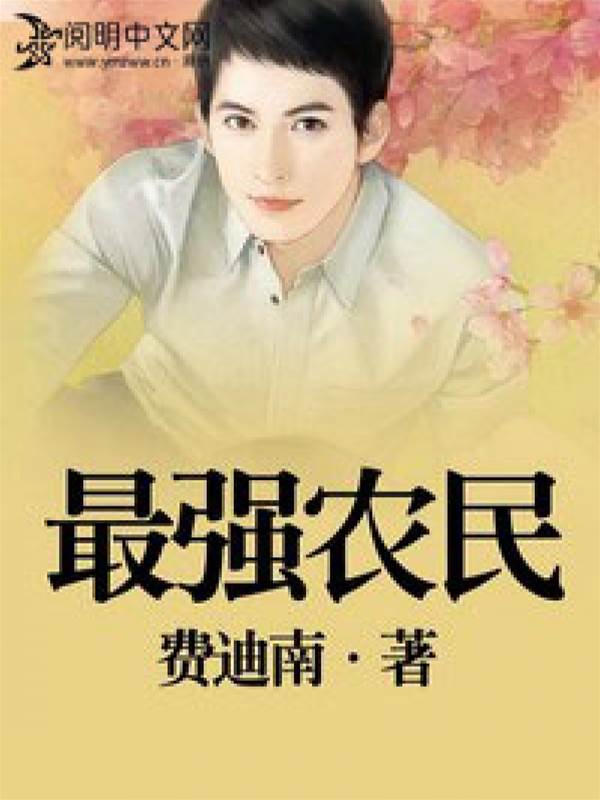《大理寺.卿》 第九章 新人
梁未平下一,隻覺站也站不住了。
是呀,他曾經也不止一次的懷疑過的份——秋水眼,芙蓉面,凝脂皮,楊柳腰……
眼前的這個人,怎麼看都應該是一個子。
可是百年以來,南朝不許子參加科舉,更別說為。
梁未平之所以無數次懷疑,卻次次都輕巧揭過,就是因為他不相信竟然會有子甘願冒著欺君的罪名,如此想不開。
說到這欺君,梁未平咽了咽口水……那如今他也知曉了此事,是不是也算包庇欺君了?
許是從他時青時白的臉裡猜到了什麼,林晚卿補充道:“梁兄不必擔憂。此事只有你一人知曉,若是真有東窗事發之日,你只需假裝不知,我定然不會供出梁兄。”
“嗯,”梁未平點頭。
反正不想知道也知道了,他還能真的給忘了不。
只是這接下來……
他低頭,目落在林晚卿破碎的袍上,一時有些無措。
順著他的目,林晚卿也轉頭,看了看自己的後背。
淺灰的袍滲,微有些裂口。但好在最近天氣不熱,中也穿得不算單薄,倒是沒出裡面的裹來。
便對著梁未平道:“如今我也沒有可信之人,還煩請梁兄幫忙清理一下傷口。”
梁未平一怔,兩隻手都快攪在一起,可糾結半晌之後,還是行到了牆側的矮櫃前,來一把剪刀。
喀嚓喀嚓的清脆聲音響起,林晚卿覺得自己背上涼了一片。
服倒還好說,只是裡面用於裹的布條沾了汙,乾涸之後早已和翻出的皮混在了一起,只要稍微扯一下就是眼冒金星的疼。
梁未平了兩下,見林晚卿咬牙氣的模樣,又不敢再下手了。
Advertisement
許是傷口拉扯得太疼,林晚卿趴在床上氣的時候,眼鼻一酸,幾滴淚水就順著鼻尖落了下來。
眼淚很鹹,像從十二年前穿越來的鹽。
一說不清是委屈,還是不甘的緒倏然翻湧,乾脆起,發狠地將背後的布條扯一通。
傷口才止,被這麼一扯,又涔涔地冒出來。
梁未平在一邊看得心驚跳,想上前阻止,卻礙於男大防,不知該如何下手。
正在這時,門外響起了篤篤地敲門聲。
兩人一驚,林晚卿趕快用棉被將自己裹住,退到了床榻裡側。
“誰啊?”
梁未平並不健壯的軀擋在床榻前,張開微微抖的雙臂,對著外面強打神問了一句。
“是我,大理寺卿蘇大人的侍衛,葉青。”
屋裡的兩人呼吸都快停止了。
梁未平驚恐地瞪著眼睛,轉頭看林晚卿,卻見林晚卿正一樣驚恐地向他。
“篤篤篤……”
單薄的木門又晃了起來,連帶著床榻都抖了幾抖。
林晚卿覺得,若是葉青拍門的力道再大幾分,那扇小破門就能被拍飛了。
所以現在他們在這裡糾結開不開門,似乎意義不大……
於是,當房門被打開的時候,葉青看到的就是梁未平滿頭大汗,腳步虛浮地守在林晚卿床榻前。而床榻上的林晚卿,用棉被將自己裹了個粽子,不留一隙。
兩人看他的眼神都有些閃躲。林晚卿的眼中,甚至還帶上了點防備。
葉青是個人,一向搞不明白人心裡的這些彎彎繞繞,也就懶得去細問。隻將背上的兩大包草藥放在小間的矮桌上道:“這是蘇大人讓我送來的。”
林晚卿怔了怔,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他讓我給你帶句話,”葉青又手去懷裡了一通,拿出一個小瓷瓶放在桌上道:“治好傷,去大理寺報道。”
Advertisement
*
這些日子以來,林晚卿一直恍恍惚惚,不敢相信這是真的。
直到端端正正地站在了蘇陌憶的書房之外,抬頭看向那塊賜燙金牌匾之時,才覺得好像真是那麼回事。
門口的衙役聽報了姓名,便將一路領到了這裡。甚至毫不見外地替開了門,讓進去裡面等。
這是一間古雅質樸的書室。
窗側有一張黃花梨木桌,一把太師椅,旁邊是一架山水青鸞的大屏風,把房間裡另一側的高木架都隔開來。
林晚卿來到一個木架前,只見上面整整齊齊地排列著一些標著名字和編號的卷宗,一眼不到頭,宛如城牆上的磚塊,細而整潔。
洪武六年揚州王氏滅門案,青州無頭案,荊州知府賄案,冀州……
林晚卿跟著這些卷宗走了一遍,被他們的數量也著實驚了一跳。
這些都是蘇陌憶在大理寺的四年間辦下的案子,其案之多,之重,令人瞠目。
只是……
腳步一頓,似乎察覺出什麼不對勁,於是退回到最開頭,又把這些卷宗理了一遍。
這人,是按照年份,州縣,兇犯姓名給這些卷宗都編了號嗎?!
心頭一跳,林晚卿的手停在了案卷底部的一行小字上──“天地玄黃,宇宙洪荒……甲乙丙丁,戊己庚辛……”
“……”這得多別扭才會乾出這麼擰的事來?
林晚卿了角,突然對自己的這個新上司有點害怕。
後的門在這個時候被推開了。
松木夾雜著青草的味道,帶了點四月裡的綠櫻香,是乾淨清爽的味道。
林晚卿後背一凜,轉正拜見,卻見蘇陌憶沉著個臉徑直向行來,二話不說地幾乎快將抵到後的木架上。
Advertisement
饒是設想過千百次的見面場景,林晚卿當下也只剩手足無措。
方才門時的清幽味道此刻將全然包圍,霎時濃烈了數倍,甚至帶上了些凜冽的殺氣。
書頁的氣混雜著新鮮的墨香——這人應當是從審訊堂直接過來的。
強住要跳出嚨的心臟,抬頭想看看蘇陌憶的表。
無奈兩人量差距太大,林晚卿哪怕踮起腳也只能看見蘇陌憶線條凜冽的結。
“我……小人……只是……”
眼前的人本沒聽解釋,往旁邊一側,長臂拂過的耳邊冷聲道:“往旁邊去。”
林晚卿一怔,順著木架挪了挪腳步。
蘇陌憶微蹙劍眉,長指落在方才過的一卷案宗上,側平視半晌,將它往外了一毫的距離。
所有卷宗又恢復了一條直線的完狀態,蘇陌憶滿足地歎出一口氣,這才起看向林晚卿。
“……”林晚卿眼皮狂跳,無言以對。
“品茗,一道?”
“哈??”
*
正盛,斑駁陸離。
林晚卿沒有想到,這個看起來冷冷的大理寺卿,竟然在自己書室後面的綠櫻林裡弄了個頗調的小涼臺。
涼臺不高,除了輕輕擺拂的素白紗幔,四周都沒有遮蔽,正是欣賞落櫻暖的好去。
林晚卿懷著忐忑的心,跟隨蘇陌憶上了榻。
他一直沉默不語,低頭整理袍裾,似乎在思忖什麼。
旁邊一個小廝搬了些卷宗過來,正要退下,被林晚卿喚住了。
“一壺西湖龍井,謝謝。”
小廝一愣,看著林晚卿不屑道:“這裡是大理寺,不是酒樓茶館。”
林晚卿一噎,剛要說話,卻聽見對面的人緩聲道:“一壺西湖龍井,兩盞茶甌。”
Advertisement
“是。”小廝頷首,放下卷宗走了。
林晚卿:“……”
“你對王虎的死怎麼看?”
一卷案宗被遞到了眼前,林晚卿回神接過來,緩緩展開。
是王虎涉的殺案不錯,但已經和前年的那樁案子撇清了關系,這卷案宗也是新寫的,上面還落下了大理寺卿的印。
“大人……”林晚卿心中一凜,詫異地抬頭看向蘇陌憶。
記得蘇陌憶之前說過,不想管這案子的。
茶香氤氳,面前的人不疾不徐地為斟茶,緩聲道:“現在這兩樁案子都是大理寺的。”
兩樁案子?
意思就是,他不僅提審了王虎的案子,就連那樁連環殺案也一並帶走了。
林晚卿握著卷宗的手抖了抖,又聽蘇陌憶問道:“你覺得王虎之死是誰做的?”
“當然是真兇。”
“哦?”蘇陌憶波瀾不驚,隻將一盞熱茶推到的跟前。
“大約在王虎獄之時,真兇就已經想到了這一步。”
蘇陌憶聞言神微舒,角浮起一微不可察的笑意,“可若是真兇做的,那不應當做畏罪自殺的模樣麼?”
林晚卿低頭嘬了一口茶,思忖道:“照如此一說,那為何真兇不在一開始就直接殺了王虎,要讓他來這獄裡走一遭?在外面殺人不是比在獄裡殺人容易許多麼?”
蘇陌憶沉默不語,默默添茶。
“所以王虎,是真兇一開始就沒有考慮到的變數。”
林晚卿看著蘇陌憶,繼續道:“真兇想殺的人原本只有趙姨娘,他是想把此案推給殺案的兇手。對於那樣一個窮兇極惡的人,害者多一個一個,沒有人會深究,是最好的嫁禍對象。”
“可是京兆尹去的時候,卻巧在案發現場遇見了王虎。”
林晚卿點頭,“對,一定是這樣。所以,是李京兆自己錯把王虎當了兇手,然後貪功冒進屈打招。兇手害怕事敗,才想要殺人滅口。”
蘇陌憶不置可否,骨節分明的食指在白玉杯沿上有一搭沒一搭地輕叩著,“那便又回到那個問題,為何不做畏罪自殺?”
林晚卿沉默。
是的,若是要殺人滅口,真兇斷不會作出這樣的陣仗,擺明了要引起各方關注,道理上著實說不通。
從現場的死者來看,手的人顯然是經過專業訓練。若是要神不知鬼不覺地潛大牢,也不會做不到。
思路陷了僵局,兩人間只剩下和風落英。
蘇陌憶撣了撣袍裾上的飛絮道:“也不急這一時,待你悉了大理寺,一切可以從長計議。”
說到大理寺,林晚卿起了其他心思,追著蘇陌憶袍起的作站了起來,雙眸晶亮亮地試探到,“聽說大理寺存有建朝以來,所有的重案要案的卷宗?”
蘇陌憶一頓,轉回問:“所以呢?”
林晚卿倒是不客氣,直言道:“那我休沐的時候可以去看看麼?”
“休沐?”蘇陌憶狀似不解,“你又不是大理寺編制,何來的休沐?”
“……”林晚卿怔忡,張了張,沒發出一個音節。
也就是說,蘇陌憶讓來大理寺,卻不打算給名份?
這真的是掌管天下刑獄的大理寺,而不是什麼街邊的黑心作坊嗎?!
而眼前的人卻一臉正氣,理直氣壯道:“你是本單獨邀來的,自然是跟隨本的行程。”
“那……”林晚卿穩住快要崩壞的表,“那我若要查詢一些資料文獻該怎麼辦?”
蘇大人依舊是一派凜然道:“你負責的案子就只有連環殺案這一樁,要查資料也應當去京兆府。”
“……”林晚卿已經有些傷,卻仍不死心道:“我天資愚鈍,有時需要前人的經驗來打開思路,故而……”
沒等林晚卿說完,蘇陌憶仿佛失了耐心,轉留下一句,“天資愚鈍,剛好用這樁殺案來正一正名,反正我大理寺也不養閑人。”
林晚卿:“……”
——————
蘇直男:走開,你弄我的書了。
林晚卿:以後每天都是996被迫營業的日子。
猜你喜歡
-
完結248 章
少爺們的小女僕
李依依進入樊家做大少爺的貼身女僕,真正目的卻是打算偷走樊家大少的精子。 然而,很快她嬌媚的身體就被樊家的男人看上,淪爲樊家四位少爺的公用女僕。 至於精子? 她要多少有多少。
24.6萬字7.7 856080 -
完結518 章
女配逆襲
為了環遊世界,寧宛選擇了難度係數最高的快穿任務。 誰知竟是——穿越到肉文改變淒慘女配的命運~ 注:劇情亂湊、為肉而肉 主溫水煮青蛙的曖昧溫馨向H,1V1,甜,要非常甜,要甜到牙酸 -------------------------------------------------- --------------------------- 第一對CP:禁慾書生VS媚惑狐妖(已完成) 第二對CP:威猛將軍VS侯府遺孤(已完成) 第三對CP:得道高僧VS相府死士(已完成) 第四對CP:總裁大叔VS花季少女(已完成) 第五對CP:山中獵戶VS毒舌寡婦(已完成) 第六對CP:異世龍君VS獵龍族女(已完成) 第七對CP:最佳新人VS金牌影后(已完成) 第八對CP:忠犬機器人VS偽白花少女(已完成) 第九對CP:偽病嬌首席VS治愈系青梅(已完成) 第十對CP:風流王爺VS傾世艷妓(已完成) 第十一對CP:海上
53.9萬字8.38 300915 -
完結50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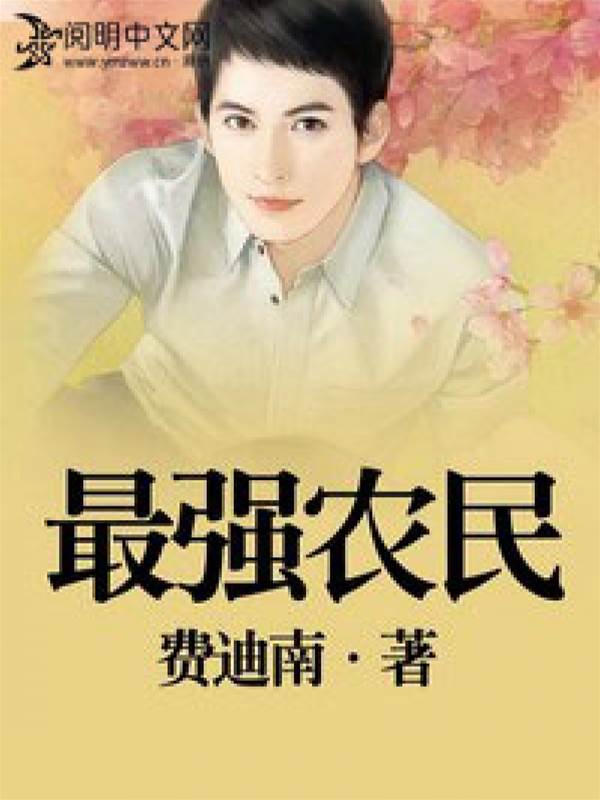
最強農民
作為世界上最牛逼的農民,他發誓,要征服天下所有美女!
14.3萬字8 12613 -
完結101 章

《我在天庭和神君偷情的日子(1V1)》
赤瑛神君在九重天一個荒僻的藏書閣看見書架後一個趴著看書的偷懶小仙姬,被她那翹起搖晃的白嫩裸足晃得刺眼。後來,東梧殿的仙侍一個月內總有幾日找不到他們的神君。其實赤瑛神君都窩在了藏書閣裡和那個小仙姬整日整夜的纏綿不休。小鳴在九重天裡是一個隨處可見,毫無存在感的小仙姬,五百年前從一個破落門派得道成仙,卻只能在九重天一個殘破藏書閣當個掃灑仙侍。但小鳴很喜歡這份工作,不用跟人打交道又清閑,每日都只需掃掃灰曬曬書,就能躺著看書吃瓜。後來她被赤瑛神君勾引上了床,想著神君袍子下寬厚有力的身軀和歡愛時的喘息聲,就更喜歡這份工作了。--------------不是小甜文,先肉後劇情,先甜後虐,隻想吃肉或看甜文部分的朋友們請按需求自行服用。正文已完結,現代番外已完結,IF線小日常已完結。喜歡寫黏糊糊的肉(形容得有點模糊,可是大家應該能意會到正文免費,現代番外免費,部分小日常收費,五章空白打賞章已開,歡迎打賞。----------------隔壁完結文,歡迎關注~《犯上》都市1V1隔壁新文,歡迎關注~啞炮小姐(西幻 NP)
27.4萬字8 13518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