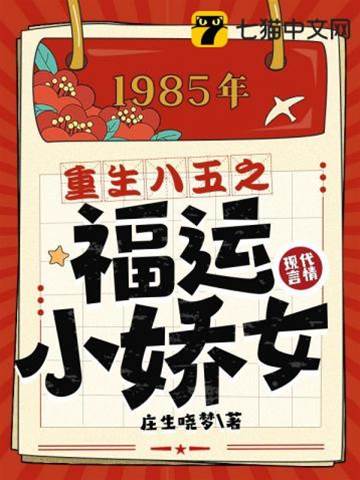《媽咪輕點虐,渣爹又被你氣哭啦》 第759章 撕下他的偽裝
範博輕咳了一聲,“硯清喜歡你,你知道為什麽嗎?”
宴遲皺了皺眉,宮硯清喜歡他?
他並不這樣覺得。
雖然宮硯清上也是這樣說的,看他的眼神也很真摯熱烈,就如同竇初開的小姑娘看自己喜歡的人。
可他能覺到看他的眼神裏出來的東西很空虛。
喜歡談不上,說不喜歡,好像也不對,總之是一種說不上來的。
他對沒有那種心思,最多隻有激之,所以也沒有多想。
但......
宴遲突然想到早上見到的人。
他瞇了瞇眸子。
早上那個人看他的眼神中有太多緒,那些緒織在一起,他看不懂,可看到掉眼淚時,他心裏偏偏有說不清道不明的緒湧上來。
一種很奇怪的覺。
宴遲沒說話。
見他發愣,範博敲了敲桌子,“喂,我在問你問題呢,你不好奇嗎?”
“不好奇。”他嗓音低沉,“也不喜歡我。”
範博笑了笑,坐沒坐相的將搭在桌上,歎著氣往後靠,“硯清這個人啊在上經曆了很多,你的出現對於的算是上天的一種......”彌補。
後麵兩個字範博沒說出來。
怕說多了宮硯清之後知道他在宴遲麵前說這些,又得跟他急。
“算了,不聊這些,聊聊你。”
“沒什麽好聊的。”
範博好奇問,“你真的什麽都不記得了?”
“不然我會待在這?”
範博挑了下眉,“也是,不過失憶是什麽覺?”
範博很好奇,失憶是什麽覺啊,大腦的記憶全部消失,連自己名字都忘記了,估計也是一件痛苦的事。
Advertisement
“說不上來。”
宴遲擰了擰眉。
他說不上來什麽覺,隻覺得想去想點什麽,在腦中努力地思索一番,卻發現什麽都找不到,那種覺無助的。
“估計也不好,聽硯清說你之前傷嚴重,你估計仇家多的吧,不然也不會負重傷墜海。嘖,你這有點麻煩啊。”
範博了下,宮硯清的父母是一定不會同意這樣一個份背景太複雜,也許還有一堆仇家的男人跟宮硯清在一起的。
宮家家大業大雖不怕麻煩,但沒人喜歡輕易樹敵,也沒人喜歡跟一個本帶著麻煩的人在一起。
也就宮硯清跟著了魔一樣的要跟他在一起。
範博連連歎氣。
宴遲抿了。
墜海,傷,仇家,帝都,宴遲......
“宴遲!”
他突然想到早上蔣黎和沈寧苒對他的稱呼。
宴遲......
很悉的名字,雖然沒有一點記憶。
他之前宴遲嗎?
“你在說什麽?”範博見他突然喃喃,於是問。
宴遲眸深了深,細想著什麽,突然捂住頭,麵痛苦。
有些東西他想想起來,可努力的去想時,頭卻傳來一陣劇烈的疼痛。
“你怎麽了?”範博連忙站起,“喂?你沒事吧?你可千萬不要有事兒啊,你待在我這裏,你要是有點事,宮硯清那個人非撕了我不可。”
宴遲捂著頭,久久沒有緩過來。
範博看了著急,連忙想要打電話去醫生來,聽宮硯清說他當時傷的不輕,這怕是舊傷發作了吧。
Advertisement
那可不得了。
“我給你個醫生過來吧。”
宴遲晃了下頭,眼睛裏一片猩紅,過了一會兒,他又好了很多,抬了下手,“不用麻煩了,我沒事。”
“你確定沒事吧?你要是真有點事,宮硯清真會不放過我的。”
範博覺得這差事難辦,費力費神還得挨罵。
“沒事。”
宴遲的臉依舊很難看。
範博正要繼續出聲,玄關的門被打開,範博見走進來的人問,“你怎麽又來了?”
宮硯清走進來,“你還不讓我來了。”
“你這大晚上的老往我這趕,合適?”
宮硯清看向宴遲,見他臉發白,宮硯清當即皺眉,“你怎麽了?”
“我剛剛跟他正聊著天呢,他好像突然就頭疼了,我正想著給他去個醫生呢,你就來了。”
宮硯清張地盯著他。
頭痛?
無緣無故的怎麽會頭痛呢。
是給他檢查過傷勢的,他頭部的傷已經好了,一般是不會複發的,突然頭痛肯定是不正常的。
宮硯清臉了,生怕他因為這次的頭痛而想起什麽。
“阿綏?”
宮硯清抬起頭,看向站在一旁的範博問,“你跟他聊了什麽?”
“我也沒跟他聊什麽啊,就隨便聊了聊,哦,對了,他剛剛自己裏念叨著自己的名字,宴遲。”
宮硯清聽著更是心下一驚。
“阿綏,你沒事吧?”
宴遲抬起手,突然握住了宮硯清的手臂,抬起猩紅的眸子看著,“早上那兩個人說的話到底是不是真的?”
Advertisement
“什麽是不是真的?我都已經跟你解釋過了,那都是假的!假的!們兩個就是跟我不合,所以想挑撥我們的關係,你為什麽就不相信呢?你當時自己也看到了們是怎麽對我的,我就是一個不小心弄灑了咖啡,們就直接拿水潑我,難道這些還不夠證明嗎?還是說你不相信我的話,要相信們兩個陌生人的話?
或者是你覺得我要害你?我若是要害你的話,我為什麽要救你呢?你這樣懷疑我真的讓我很傷心。”
宴遲擰了擰眉。
範博不得不稱讚宮硯清胡說八道的能力還是不錯的,這些話聽著多真實啊,他都差點信以為真了。
隻是隻要仔細聽細節,他就能聽出宮硯清在撒謊。
了解的人都知道的子,是半分都不願意吃虧的,若真有人敢拿水潑,是絕對不可能善罷甘休的。
也沒有人能欺負得了。
範博聽著這些話,忍不住默默搖頭。
宴遲不知道信了這些話沒有。
宴遲回想起早上見麵時的場景,忍不住頭疼起來。
見宴遲皺眉,宮硯清立刻道:“你看你又頭疼了吧,你別去想早上那些事了,我說了我會幫你去查你失憶前的事,等找到你的家人了再說這些話。”
宴遲抿了,沉默良久,“我想重新見見你那個表姐,和的那個朋友。”
宮硯清心中一突。
當即變了臉。
“你見們做什麽?”
“有些話我想要當麵問問們。”
宮硯清深吸一口氣,“說白了你就是不相信我說的那些話,覺得我是在騙你。”
Advertisement
“我更相信我自己聽到的看到的,更相信我自己的直覺。”
“那你覺得是什麽呢?你覺得們說的是真的嗎?阿綏,別可笑了,都說了們跟我不合,你還要見們,還相信們說的話,你是誠心想要讓們笑話我嗎?”宮硯清一下子紅了眼眶。
宴遲蹙眉,臉不好看,“我沒有這個意思。”
“你要見們是什麽意思呢?不就是不相信我說的話嗎?”宮硯清苦笑了一聲,“我也是想不到我救了你的命,還照顧了你兩個月,竟然比不上兩個剛見麵的陌生人跟你說的話,我在你眼裏是這麽的不堪嗎?”
宮硯清上了緒,聲音聽起來帶著哽咽,更帶著幾分質問。
像是傷心了,一雙漂亮的眸子裏滿是眼淚。
宴遲抿了抿,也不想惹哭。
“我沒有別的意思,就是有些話我沒有弄清楚。”
“這事已經再清楚不過了,就是們聽說了你是我男朋友,又聽說了你失憶的事,們見不得我過得好,想要挑撥你我的關係。”
宴遲看著宮硯清這副樣子,也不好再說什麽。
不願意讓他見們,他自然也有辦法能見到。
“那就不說了。”
宮硯清吸了吸鼻子。
“你也別哭了,我沒有不相信你的意思。”
宮硯清止不住眼淚,“阿綏,你知道嗎,你剛剛說的那幾句話就是不相信我,我真的沒有想到你寧願去相信兩個陌生人,也不願意相信我,這話真的很傷人。”
說完,宮硯清直接跑了出去。
範博見狀,無奈地歎了口氣,“就是這子,心思比較敏脆弱,你非說你不相信幹什麽。”
說完,範博追著宮硯清離開的方向去了。
宴遲沒說話,深思這什麽。
範博追上宮硯清,見宮硯清一個人坐在外麵吹冷風,他走過去在的邊坐下,“你騙他的那些話他已經起疑了,他也不是個傻子。”
“我真是後悔,我今天就不應該讓他們見麵。”宮硯清狠狠咬牙。
“現在他們都見到麵了,你說這些話也沒用,接下來你還想騙他什麽就困難了。”
宮硯清抬起頭,“我這個人最不怕的就是困難,我想要留下來的人必須是我的,誰都不要跟我搶。”
“你這有點自私啊,畢竟人家有孩子了,你這是讓他們一家分離呀。”
範博知道這些話說了宮硯清聽了一定不會開心,但是他還是得說。
“我自私嗎?”宮硯清冷笑了一聲,視線盯著範博問,“我哪裏自私了?若不是我在海上救了他的命,他早就死在海上了,要是他已經死了,們今天有資格坐在我麵前跟我談論這些嗎?們有資格再見到他嗎?
我才是救了他的人,是我給了他第二次的生命,而們呢?們做了什麽?們什麽都沒有做,就因為看到他了,所以就要從我邊搶走他,憑什麽?
到底是誰自私啊?
我說了但凡他們早點找到他,我都不會說什麽,而現在我把他治好了,們就跳出來說要帶走他,憑什麽啊?真當我是聖母啊?救苦救難,大公無私,救完了人還要乖乖聽話將人送回去。”
範博聽著這些話像是沒有什麽問題的。
可救的是個人,並不是什麽小貓小狗。
就算是小貓小狗,它也有主人,救了它,可以要求它的主人報答,卻不能將這隻小貓小狗占為己有。
範博想將這些道理講給宮硯清聽,可按照宮硯清這個格,估計是本聽不進去的,他說了也是白說。
“別說了,說得我煩。”宮硯清揮了揮手,歎了口氣,“對了,我大伯今天中午走了。”
範博瞳孔了,“真去世了?”
“嗯。”
“天哪,我一直以為是能救回來的,沒想到真的......那宮晚音不恨死沈寧苒了?”
宮硯清扯了下角,不屑道:“要是真的聰明的話隻恨沈寧苒就好,若是不聰明,還想來跟我們鬥,那隻有死路一條。”
範博多知道他們宮家這件事的原委,歎息著搖搖頭,“這件事非同小可,你們自己也小心點吧,宮晚音也不是一個好欺負的主。”
猜你喜歡
-
完結437 章

禁愛冷婚:噬心總裁請走開
十歲那年,她被帶回顧家,從此成了他的專屬標籤.性子頑劣的他習慣了每天欺負她,想盡各種辦法試圖把她趕出這個家.在她眼中,他是惡魔,長大後想盡辦法逃離…孰不知,傲嬌的他的背後是他滿滿的深情!在他眼中,她是自己的,只能被他欺負…
79.8萬字8 51621 -
連載1508 章
媽咪爹地要抱抱
豪門陸家走失18年的女兒找回來了,眾人都以為流落在外的陸細辛會住在平民窟,冇有良好的教養,是一個土包子。結果驚呆眾人眼球,陸細辛不僅手握國際品牌妍媚大量股份,居然還是沈家那個千億萌寶的親生母親!
127.1萬字8 107896 -
完結518 章

六歲妹妹包郵包甜
【團寵、高甜、前世今生】農村小野丫頭樂萱,靠吃百家飯續命,家家戶戶嫌棄她。 某天城里來了個謫仙似的小哥哥沈易,把她領了回家。 噩夢中驚醒,覺醒了萱寶某項技能,六歲女娃琴棋書畫樣樣精通,徹底虜獲了沈家長輩們和哥哥們的心,她被寵成了金貴的小寶貝。 每天爺爺奶奶、爸爸媽媽、叔叔嬸嬸、還有哥哥們爭著搶著寵,鄉下野生親戚也突然多了起來,自此萱寶每天都很忙,忙著長大,忙著可愛,忙著被寵、忙著虐渣…… 標簽:現代言情 團寵 甜寵 豪門總裁
109.9萬字8 94533 -
完結872 章

婚華正茂
蘇念恩被查出不孕,婆婆立馬張羅,四處宣揚她有病。丈夫出軌,婆婆惡毒,當蘇念恩看清一切,凈身出戶時,丈夫和婆婆雙雙跪求她留下。她瀟灑走人:“我有病,別惹我。”愛轉角某個牛逼轟轟的大佬張開雙臂說:“你有病,我有藥,天生一對。”
138.1萬字8 69942 -
完結38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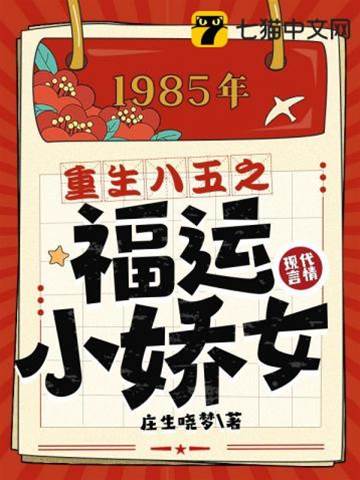
重生八五之福運小嬌女
前世,喬金靈臨死前才知道爸爸死在閨蜜王曉嬌之手! 玉石俱焚,她一朝重生在85年,那年她6歲,還來得及救爸爸...... 這一次,她不再輕信,該打的打,該懟的懟。 福星錦鯉體質,接觸她的人都幸運起來。 而且一個不留神,她就幫著全家走向人生巔峰,當富二代不香嘛? 只是小時候認識的小男孩,長大后老是纏著她。 清泠儒雅的外交官宋益善,指著額頭的疤,輕聲對她說道:“你小時候打的,毀容了,你得負責。 ”
70.5萬字8 19150 -
連載285 章
相親對象是富豪總裁
她著急把自己嫁了,不求此人大富大貴,只要沒有不良嗜好,工作穩定,愿意與她結婚就成。沒想到教授變總裁,還是首富謝氏家的總裁。……當身份被揭穿,他差點追妻火葬場。老婆,我不想離婚,我在家帶孩子,你去做總裁,謝氏千億都是你的,你想怎麼霍霍就怎麼霍霍。其實,她也是富豪。
50.8萬字8 14491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