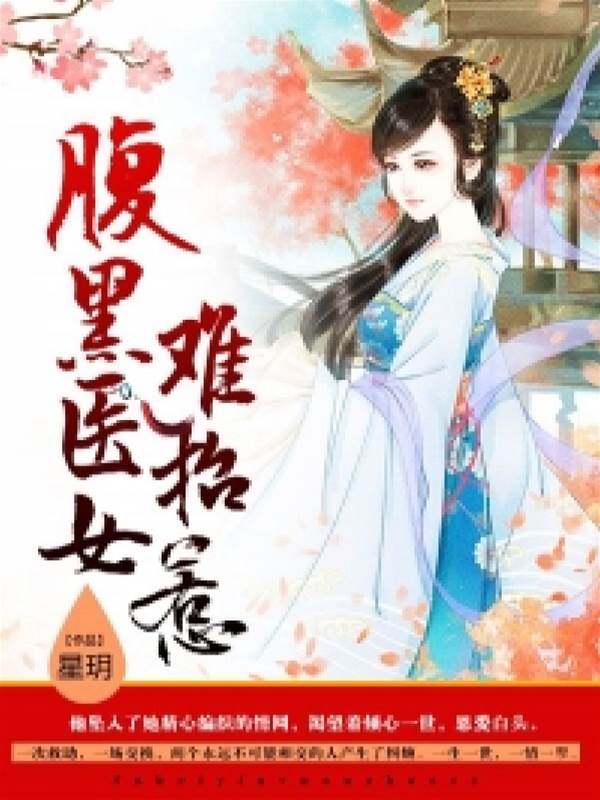《惡毒姐姐重生了》 第170章
(4, 0);
「怎麼回事!」
徐氏變了臉,不等似月答話,率先轉大步離開。
似月跟在旁,邊走邊說,「荷香過來傳的話,說是小姐回去路上和二小姐撞上,兩人不知道起了什麼衝突,跟著小姐就掉進了湖裡,也是打掃的婆子正好瞧見忙喊了人過去,及時把小姐救了上來。」
要再晚些,只怕真要出大事。
原先是跑著過來的,這會氣還有些,卻不敢耽擱,「現在小姐已經被人送回了房間,也已著人請了大夫,盛嬤嬤也已經趕過去了。」
聽到盛嬤嬤已經過去,徐氏懸著的心稍稍鬆了一些,但臉還是很難看,又聽這事居然和阮微月有關,更是冷笑一聲,「這些年我好吃好喝供著們母,沒想到如今們的膽子是越來越大了!」
「去!」 𝕊тO.ℂ𝓸м提醒您查看最新容
雍容華貴的臉在月的照映下沉得像奪命的閻羅,一大紅牡丹錦服裹著風霜帶著戾氣,扯寒聲,「把那兩個賤人給我綁過來!」(5,0);
似月雖然不清楚湖邊發生了什麼,但料想二小姐也沒這麼大的膽子敢推大小姐,估著是那邊黑燈瞎火,大小姐不小心絆進了湖裡。
但這話,知道卻不能說。
原本夫人今日心就不爽,剛才就是要去和老爺吵架。
要怪就怪二小姐生了一張壞,又偏在這個時候鬧出事,一頓罰是免不了了……心裡一嘆,輕輕應一聲,見徐氏已轉進小道,自己也朝柳氏母所在的屋子過去。
……
柳氏住在阮府的西院,距離主院有很長一段距離,剛才一出事,阮微月就跌跌撞撞跑到了柳氏這邊。
Advertisement
這會正抱著柳氏哭著。
阮微月平時掐尖要強,除了在老爺夫人老夫人那邊伏小做低些,見了誰都是一副氣勢凌然的模樣,這會卻不知是不是太過害怕,整個人都一團,哭得久了,聲音都啞了,眼睛紅彤彤的說道:「姨娘,你信我,我真沒推,是自己掉下去的!」
「我想抓的,你看,我手上還有抓痕,只是那邊沒有憑欄,我抓不住,才掉下去的!」(5,0);
柳氏哪裡聽解釋,最主要的是解釋有什麼用!
「我與你說了多次,讓你離遠點,你做什麼非要湊到跟前和找不痛快!」柳氏的聲音也是又急又怕,夾雜著一子埋怨和不知道怎麼應對的慌張,從前唱曲跳舞,聲音本就比旁人亮一些,這會拔高了音調,更顯尖銳。
阮微月見這般,一怔,大概是沒想到從小疼自己的姨娘會吼自己,一癟,沒忍住又哭了起來,「我就是看不慣!」
這次卻是怨憤大於害怕。
徐氏雖然不喜歡們母,但也只是眼不見為淨,從來也沒怎麼苛責過們,也因此阮微月雖是庶,卻也有個驕縱脾氣。
這會撒開手,背對柳氏坐著,一邊死死絞著帕子,一邊咬牙說,「世子來了,爹爹特地喊了過去作陪,卻不喊我,憑什麼?以前阮妤和世子好也就罷了,現在換了阮雲舒,難不就因為是嫡,我是庶?!」
說著轉過臉,高高仰起頭,一臉不服氣的模樣。(5,0);
「你!」
柳氏沒想到居然是因為徐之恆,更是氣得不行,抬手想打,見神倔強,眼睛卻紅得滴,又下不去手,手僵在半空,整個人繃著,卻是一句話都說不出。
Advertisement
阮微月到底還小,倔了一會又沒忍住,哇的一聲,抬手抱住的腰,埋進懷裡,繼續哭道:「姨娘,你可是我親娘,你不能不管我!」
「我能怎麼管?」
柳氏的聲音疲憊又無力,「我這些年偏居一隅,話都不敢多說一句,就是想讓夫人消氣,不要因為我的緣故恨上你。你倒好,哪裡有事往哪裡鑽,如今生出這樣的事,我護不住你,你爹那樣的涼薄子,必定也不會管我們娘倆。」
說到這,忽然有些難過的扯了下,自嘲一笑後癱坐在椅子上,低著頭,手無力垂著。
從前也是艷絕八方的人,那些富紳公子哪個不對青眼有加?要是就那樣待在青樓誰也不也就罷了,等錢賺得多了,自己隨便找個地方開間小店,或是只買個宅子,請一兩丫鬟照顧,了卻此生也不錯。(5,0);
偏偏不死心,覺得總有男人是真的,便這麼跟了那會死了青梅又和徐氏鬧僵的阮東山。
也是傻,明知男人的話不可信,還是一腳踩進了這個淤泥坑裡,覺得徐氏不得寵又只有一個兒,脾又烈,保不準日後就被阮東山休棄了,面對的時候自然也就不那麼恭敬。
可忘了。
徐氏除了是阮夫人,還是徐家。
與最不同的就是後還有一個可以讓支撐的娘家,還是一個連阮東山都得畏懼的強大岳家。
等徐氏對阮東山了卻意,知道要什麼後,的那點好日子也就徹底到了頭,好在及時醒悟,伏小做低,可這麼活了十幾年,從前上人追捧的那點也是一都不剩了。
這會耷拉著眼皮,沉默著,仿佛突然老了許多歲。
Advertisement
「老夫人……」忽然喃喃一句。
「對,去找老夫人!」柳氏說著就站了起來,眼中也重新盛起芒,正要抬腳出去,便瞧見似月掀簾走了進來。(5,0);
臉霎時變得慘白起來,柳氏抱著阮微月,一步步往後退,等想到什麼又突然鬆開阮微月的手衝上前,抓著似月的胳膊祈求道:「姑娘,您是夫人面前的紅人,求您和夫人說說好話,二小姐是不懂事但真的沒有要加害大小姐的意思,求您讓夫人開開恩,放過二小姐吧!」
曾經家喻戶曉的花魁,現在為了保護自己的兒,舍下一臉面,跪下給丫鬟磕頭。
砰、砰、砰——
沉重的磕頭聲在屋中響起。
柳氏潔白的額頭沒幾下就被磕出了紅印,襯得那張如秋水般的臉越顯弱可憐。
似月被嚇了一跳。
阮微月也是目瞪口呆,等反應過來,手捂著抖不已的,卻是哭得更加厲害了。
「您別這樣,先起來。」似月彎腰去扶,柳氏卻不肯,只繼續磕著頭,似月無法,只能蹙眉道:「夫人請您和二小姐過去,若再耽擱,惹了夫人生氣,您便是連求饒的機會都沒了。」
聽得這話,柳氏臉一白,倒是真的不敢再耽擱了。撐著地站起來,還沒站穩就趔趄一下,差點沒摔倒,阮微月忙跑過來扶住,淚眼朦朧地喊,「姨娘。」(5,0);
似月收回出去的手,看了們母一眼,輕輕嘆了口氣,跟們前後腳出去,察覺到有人在們走後向榮壽堂方向跑去也沒有阻攔。
都是可憐人。
可能做的也就只有這些。
……
徐氏坐在拔步床邊親自照顧昏迷不醒的阮雲舒,大夫已經給看過,道是沒什麼大礙,只是要好好靜養幾天。便把人都趕了出去,餘瞥見打簾進來的盛嬤嬤,掃了一眼,收回帕子,語氣淡淡地問道:「來了?」
Advertisement
「是,母倆都來了,這會正在外頭跪著。」盛嬤嬤輕聲答。
「嗯。」
徐氏點了點頭,神依舊淡淡的,不見喜怒,只是把手中帕子遞了過去,叮囑一句,「你看著些。」聽應是,又替人掖了下被子,這才起往外走去。
盛嬤嬤看著傲然如寒梅的影,知今日心裡邪火橫生,也不敢勸,目送出去便坐到了床邊的圓凳上。不想這一回頭卻撞進一雙幽潭般的眼眸里,許是那雙眼睛太過漆黑,足足愣了有一會才驚喜著撲過去,「小姐,您醒了!」(5,0);
床上的卻沒有立刻回答。
那個穿著一白,躺在萬事如意錦被下的雙眼漆黑如深潭,靜靜地看著,目有些陌生,微張,遲疑了好一會,才出聲喊,「盛……嬤嬤?」
盛嬤嬤一怔,「小姐,您怎麼了?」
怎麼說話和目這麼陌生,心下一,連忙拿手去探,不想手還沒到的額頭,便偏了頭……這一個舉,兩人都愣住了,尤其是盛嬤嬤,更是目奇怪地看著。
阮雲舒藏在被子裡的手輕輕握了一握,很快,又出一個靦腆的笑,啞著嗓音說,「嬤嬤,我嚨疼,你幫我倒盞熱茶。」
「好。」
盛嬤嬤雖覺得奇怪,但聽說不舒服,立刻轉去倒了一盞熱茶。剛剛轉,原本躺在床上的便輕輕蹙了眉,抬眼看著頭頂的帷帳和屋中的布置,而後又從被子裡拿出手細細看著……聽到腳步聲,又若無其事地收回目,接過茶,不不慢地喝了一口。
「外頭怎麼了?」聽到有人在哭,有些悉又有些陌生。(5,0);
「柳姨娘和二小姐在外頭跪著。」盛嬤嬤低聲和解釋,說話的時候不聲地看著床上的,從前遇到這樣的況,小姐便是再不喜歡二小姐也會出聲勸阻,但今日只是靜靜地捧著那盞茶,低著頭慢慢喝著,聞言也只是輕輕哦了一聲。
不對勁。
卻又說不出哪裡不對勁。
阮雲舒餘瞥見皺起的眉,喝茶的作一頓,等抬頭的時候又是那副順模樣,「二妹也不是故意的,嬤嬤出去和母親說聲,饒了們吧。」
盛嬤嬤蹙的眉心這才鬆了下來,抿了個笑,卻沒有立刻出去,而是先服侍人用了藥,等阮雲舒重新躺到床上,這才熄滅燭火走了出去。
外頭慘聲依舊還在,而昏暗閨房中原本閉雙目的阮雲舒卻重新睜開了眼。
就這樣看著頭頂的帷帳,聽著那慘聲,一點點扯開,用近乎呢喃的嗓音嗤聲笑道:「原來,是這樣。」
另一頭,徐家父子一路驅馬回到了家。(5,0);
偌大的忠義王府差不多占了小半條街,大紅燈籠高掛,照得府門外的兩座石獅子越發雄偉,像個沉默守護這方安寧的將軍,看著兇狠卻讓人覺得安全。
門外一直有人候著。
徐家將門世家,就連府中伺候人的小廝也一個個站得筆直,看到他們回來連忙上前請安,父子倆皆是寡言的人,這會便微微頜首進了府。
「你母親估計還在等你,去給報個平安便早些回去歇息,你這陣子也累了。」進了府後,徐長咎這般待徐之恆。
往日徐之恆必定應喏,今日卻沉默了一會,看著他說,「我有話要問父親。」
他有太多的話要問。
軍營里的那個阿常將軍究竟是怎麼回事?印象中只記得他很小的時候就待在父親邊了,甚至在他還沒進軍營的時候就已經進軍營了,人緣好,武功高,整日戴著一副面,不打仗的時候就穿一白,背著手大街小巷各走,會說話也笑,即使從不容也能引得邊境為他著迷。
(5,0);
徐之恆從前就覺得軍營困不住那個瀟灑不羈的男人。
所以那次從父親口中知曉他離開,徐之恆並不意外,可這樣一個人,如今卻出現在了霍青行的邊,心甘願了他的侍衛。
這簡直匪夷所思。
猜你喜歡
-
完結1139 章

皇後有旨:暴君,速侍寢!
夏梵音一度覺得當公主是件很爽的事,隻需要負責貌美如花,可是真的穿越後,她發現事情好像不太對勁??那一年,權傾天下的九千歲看上當朝最受寵的小公主,強勢掠奪,整個皇室反抗無效。“本尊要的女人,誰敢說不?”“……”沒人敢!經年流轉,九千歲榮登帝位,強勢立她為後,“朕會對你負責的。”“你不舉!”“舉不舉,你昨晚還沒嚐夠嗎?”梵音老臉一紅,“丫給我滾!”男人似笑非笑,“看來確實沒滿足你。”那一晚,梵音的腰差點折了。………………梵音曾一度不解,這該死的男人明明是個太監,為什麼總纏著她要要要?直到後來每天每夜都下不了床,她才明白這貨根本就是個假太監!【男女雙潔】
98.2萬字8 25227 -
完結130 章

猶記驚鴻照影
傷心橋下春波綠,曾是驚鴻照影來。 妹妹出人意料的逃婚,讓她無從選擇的嫁入天家。 從大婚之夜的獨守空閨,到知曉夫婿刻骨銘心的曾經,她一直淡然處之。 嫁與皇子,本就注定了與愛無關。她所在意的,不過是護得家人安寧。 她伴著他,一步一步,問鼎天下。她看著他,越是微笑就越是冷漠的眼睛。 從未想到會有一天,自己所信仰的一切,被他親手,毀滅得支離破碎。
29.7萬字8 6755 -
完結25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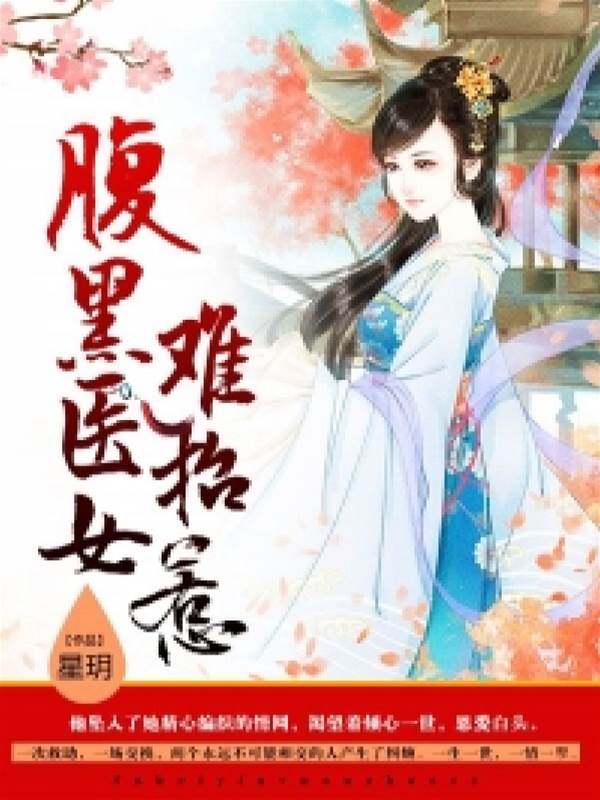
腹黑醫女難招惹
她本是現代世界的醫學天才,一場意外將她帶至異世,變成了位“名醫圣手”。 他是眾人皆羨的天之驕子,一次救助,一場交換,兩個永遠不可能相交的人產生了糾纏。 一生一世,一情一孼。 他墜入了她精心編織的情網,渴望著傾心一世,恩愛白頭。 已變身高手的某女卻一聲冷哼,“先追得上我再說!”
42.7萬字8 12262 -
完結397 章

嫁給權臣後,女配被嬌寵了
《嫁給權臣後,女配被嬌寵了》在魏國賤民唯一一次前往上界,經受鑑鏡鑑相時,鑑鏡中出現了天地始成以來,傳說中才有的那隻絕色傾城的獨鳳,所有人都在為魏相府的三小姐歡呼,樣貌平凡的我納悶地看著手,如果沒有看錯的話,在鑑鏡從我身上掃過的那一息間,鑑鏡中的鳳凰,與我做著同一個動作……
72.5萬字8 255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