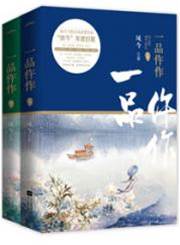《四歲小奶團:探案娘親拽翻了》 第54章 狗眼看人低
楚南梔見著戚墨琛的影,心中立時生出了幾分警惕。
二寶、三寶也有些懼怕的躲到了楚南梔後。
「喲喲喲,這不是嫁給皇親國戚的我家堂妹嘛,怎的又跑到縣裡來撒野了,是你那位瘸的皇室後裔不能再寬你了,還是又想著來縣裡找那位眉清目秀的小道士啊。」
戚墨琛上前來也不理睬一臉熱忱的韓川,先是對楚南梔一頓冷嘲熱諷:
「我倒是忘了,那西門道人是親自被你送上絕路了的,你要是覺著寂寞難耐,做堂兄的倒是樂意再為你引薦幾位小郎君。」
也不等楚南梔答話,韓川就搶先湊到戚墨琛跟前,堅定的表明立場:
「戚兄,這瘋婆娘你可別跟一般見識,呀就是個不識好歹又沒頭腦的蠢貨,在下與並非一路人,戚兄切莫因為這瘋婦的瘋言瘋語傷了我們兄弟之間的。」
「二郎也在呀。」
戚墨琛裝作才發現韓川,見他灰頭土臉的樣子,很是同的問道:
「多日不見,二郎怎生如此狼狽呀?」
「一言難盡啊戚兄。」
韓川哭喪著臉,沒好氣的瞥了眼楚南梔,滿腹幽怨的答道:
「這些日子館那群老豬狗都堵到我家門口去要銀子,家裡能典當的都典當了仍是不足以勸退那群老豬狗,本想來你家酒樓喝點小酒圖個清靜,可這狗東西竟然管在下要銀子。」
說罷,他又滿目兇的瞪向酒博士。
酒博士無言以對,直接埋下頭去。
戚墨琛冷聲笑了笑,裝作很吃驚的樣子:「竟有這回事?」
「的確如此。」
韓川又道:「藝館的老豬狗說都是戚兄你的意思,我是斷斷不信的,戚兄當初結在下,可是承諾過,這蘆堰港之所到之一切花銷都可以報貴府名頭,戚兄可不能言而無信啊。」
Advertisement
「韓二郎,你真是沒皮沒臉慣了,簡直有辱讀書人的名聲。」
聽到這話,楚南梔面上慍漸濃,指著韓川罵道:
「你以為你這些年真是靠著戚家的名聲能夠安穩度日的,你在那些勾欄瓦舍欠下的銀子哪一筆不是我母親最後給你填的窟窿,真當戚家人如此善心,拿著銀子由著你驕奢Yin逸,你是將自己當戚家人親爹還是親孫子了?」
「你、你、你這潑婦,我懶得與你理論,真是有辱斯文得很。」
韓川咬牙切齒一番,向戚墨琛卑躬屈膝道:「戚兄,你別聽這惡婦下作之言,與我家中那賤婦都是沒見地的蠢貨,我今日回家就休棄了那***,從此與楚家一刀兩斷。」
「好啊,難得二郎有此魄力。」
戚墨琛指著楚南梔險的笑道:
「這婦人前些日子將我母親推倒在地,還敢頂撞我這做兄長的,實在是不敬得很啦,二郎你不是想要繼續過逍遙的日子嘛,那你這便過去替我教訓教訓,給我戚家出了這口惡氣。」
「什麼,你竟然連大伯母都敢不敬。」
韓川兇神惡煞的瞪向楚南梔,躍躍試的卻遲遲不敢上前來。
楚南梔護著二寶、三寶,橫眉冷對,眸直勾勾的視向戚墨琛:
「戚小郎,我那日為何不敬你們母子你自己心裡沒數嗎,你們一家若是識得禮數,我自然會對你和你母親敬意有加,可你和你母親仗著家裡有幾個臭銀子就出來顯擺,仗勢欺人,惡語相向,那我一家也不會由著你欺凌。」
在楚南梔的染下,二寶林瑞希這時也全然沒了懼,冒出頭來大聲辯解道:
Advertisement
「是你母親先罵我們一家是***,還罵我姥姥是老豬狗,罵的可難聽了,我們為什麼要由著你們罵,我姥姥家欠你們的銀子已經還清了,你們憑什麼再去為難姥姥。」
「還清了?」
戚墨琛意味深長的打量著楚南梔,搖頭道:
「我看,不見得吧,前幾日我母親可是細細算過,去年你們家那贅婿在賭場里輸了一百兩銀子,我阿爹用自己積攢多年的私房錢替你們家還了虧空,那也是我戚家的銀子,再說這麼些年我戚家沒幫你們二房,怎麼著也得算些利息。」
他此言一出,旁邊圍觀的人都紛紛不平的議論起來:
「那戚家主母可真不是個東西,當年貪圖楚家大郎風雅之姿,以勢人,巧言令的將他強騙進戚家贅,還當著不鄉紳的面承諾要不餘力的幫助楚家興盛門楣,給了縣衙和鄉紳們一個代,如此才勉強息事寧人,結果進了門沒幾年就變了臉。」
「是呀,文煜兄的事在下是最清楚不過了,他被強贅戚家這些年向來不問世事,深居簡出的吃齋念佛,所用銀錢據說都是他那二弟發達後送過去的。」
「不錯,不錯,這韓二郎與楚家那位贅婿據我所知以前也是踏實上進的本分人,自打這幾年結識了戚家小郎君之後就跟變了個人似的,整日里遊手好閒,不是眠花宿柳,就是沉溺於賭場酒肆,生生將當初戚家贈與楚家的那三十畝良田給敗了回去。」
「如此說來,戚家恐怕是故意心積慮的要奪回自家家產吧。」
聽到眾人的議論,楚南梔也漸漸記起些事來。
Advertisement
原主伯父楚文煜在被贅到戚家后,戚家給了楚家幾十畝田地安一家老小。
楚家人萬般無奈之下,只好借著這幾十畝田地苦心經營,後來竟然發了家。
致富后,原主父親楚文畢聽說兄長在戚家過得不好,從不與戚家人打道,擔心他委屈,便送了不銀子過去,還按著最高市價將三十畝良田折算一兩紋銀還於戚家。
如此,也好讓兄長心安。
去年替柳舒還賭債的錢便是楚文畢發達時送給兄長的銀子。
也不想讓楚文煜在戚家為難,楚南梔當著眾人的面認下了這筆債:
「行,戚小郎,你想怎麼算,今日當著鄉鄰的面我們算清楚,從此以後我們互不相欠。」
戚墨琛倒也聽說破獲稅銀案縣令獎賞了兩銀子的事,但這點銀子還清那一百兩都不夠,更別說是利息了。
他放心的比劃了個手勢,爽朗的笑了笑:「連同利息,二百兩。」
「好,我認這筆債。」
楚南梔回答得也很果決,從懷中掏出二百兩銀票,直接遞到他手上:
「今日請各位鄉鄰們做個見證,今日我替家中父母還了戚家的銀子,從此我楚家與他戚家的債兩清了,戚小郎,也請你們母子以後見著我楚家人放尊重些。」
隨後又拿銀子出來,憤憤的瞪了眼一旁的韓川,繼續道:
「這斯文敗類如今還是我楚家的婿,今日這飯錢我也替我母親和二妹認下,但我有言在先,從今往後他在外欠下的所有銀子一概與我楚家無關,如若你們膽敢再賒賬與他,又別有用心的跑到我楚家要銀子,休怪我翻臉不認人。」
Advertisement
說罷,領著二寶三寶就要離去。
「慢著。」
戚墨琛靜靜注視手裡的銀票,冷著臉將攔下。
這婦人能拿出二百兩銀票,完全出乎他的意料。
他可不信銀子是自己的。
楚南梔微微擰眉,眸隨之變得深沉:「怎麼,戚小郎還有何見教?」
「你哪來的這麼多銀子?」
戚墨琛一臉懊惱:「是不是我那該死的父親又給你們家送銀子了?」
「你還真是狗眼看人低,真當整個蘆堰港只有你戚家才配有銀子?」
「那你哪來的這些銀子,不說清楚休想走。」
戚墨琛不依不饒的,立刻吩咐邊的家奴們圍攏過來。
猜你喜歡
-
完結46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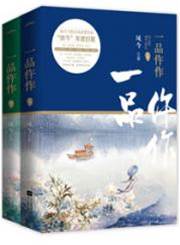
一品仵作
這是一個法醫學家兼微表情心理學家,在為父報仇、尋找真兇的道路上,最後找到了真愛的故事。聽起來有點簡單,但其實有點曲折。好吧,還是看正經簡介吧開棺驗屍、查內情、慰亡靈、讓死人開口說話——這是仵作該乾的事。暮青乾了。西北從軍、救主帥、殺敵首、翻朝堂、覆盛京、傾權謀——這不是仵作該乾的事。暮青也乾了。但是,她覺得,這些都不是她想乾的。她這輩子最想乾的事,是剖活人。剖一剖世間欺她負她的小人。剖一剖嘴皮子一張就想翻覆公理的貴人大佬。剖一剖禦座之上的千麵帝君,步惜歡。可是,她剖得了死人,剖得了活人,剖得了這鐵血王朝,卻如何剖解此生真情?待山河裂,烽煙起,她一襲烈衣捲入千軍萬馬,“我求一生完整的感情,不欺,不棄。欺我者,我永棄!”風雷動,四海驚,天下傾,屬於她一生的傳奇,此刻,開啟——【懸疑版簡介】大興元隆年間,帝君昏聵,五胡犯邊。暮青南下汴河,尋殺父元兇,選行宮男妃,刺大興帝君!男妃行事成迷,帝君身手奇詭,殺父元兇究竟何人?行軍途中內奸暗藏,大漠地宮機關深詭,議和使節半路身亡,盛京驚現真假勒丹王……是誰以天下為局譜一手亂世的棋,是誰以刀刃為弦奏一首盛世的曲?自邊關至盛京,自民間至朝堂,且看一出撲朔迷離的大戲,且聽一曲女仵作的盛世傳奇。
203萬字8 27668 -
完結757 章

鎮陰棺
我一直跟在爺爺身後幫別人遷墳。遷墳中有著一種特殊的葬法,名二次葬,需開棺槨,撿屍骨,整新衣。而我第一次遇到二次葬,就挖出一具栩栩如生的女屍……
142.7萬字8 67363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