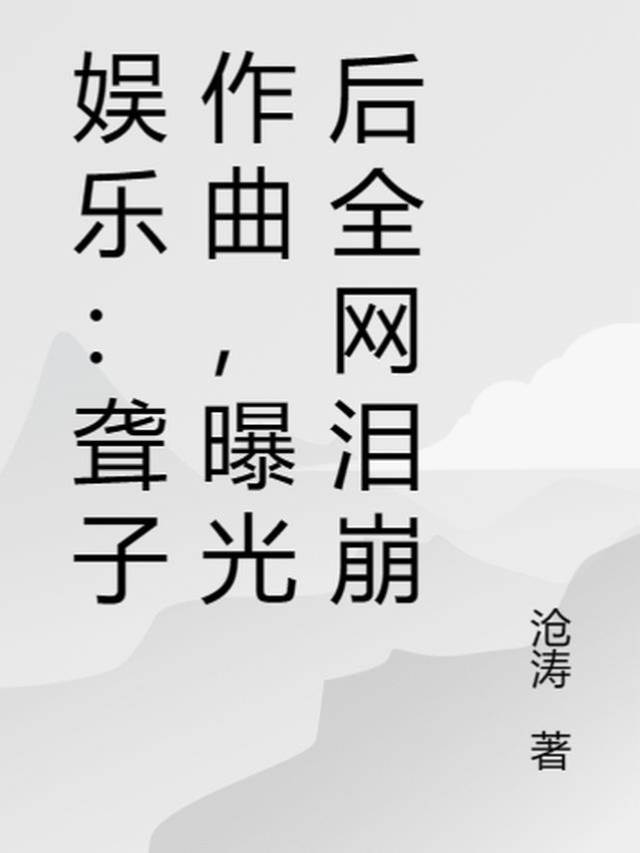《薄總還虐嗎?夫人她不會回頭了》 第31章 真的是為了她?他不是最恨她的嗎?
這個衝擊足夠大。
大到,秦玥要再不信薄宴淮對安凝了真就是自欺欺人了。
安與母親對視,顯然兩人想法相同。
安父沒察覺到這母兩人眼角的暗湧,在旁邊急得團團轉,他還沒在薄宴淮這裏撈到好呢!
安這個不爭氣的家夥!
“安凝呢?”安含著某種期待問。
“隻是暈倒了,嗆了幾口煙。”秦玥沒好氣地翻了個白眼,也不知道那個喪門星的運氣怎麽那麽好。
安的臉冷了下來,目就像一把鋒利的刀刃時刻要刺安凝的心髒:“可真是好命,白白讓宴淮哥哥苦!”
“你說的是什麽混賬話!”一道銳利的聲音猶如炸彈在前方響起。
手室外的所有人都不約而同地看了過去。
秦玥眼皮狠狠跳了一下,萬萬沒想到這件事會驚薄老爺子,薄宴淮的親爺爺,也是他們得罪不起的一個大人。
這下可真是糟糕了!
“爺爺……”安瞬間收斂氣焰,熱地朝老爺子走去。
薄老爺子在眼裏,不怒自威,氣勢像天神,一見他就自帶怯弱,總覺得在這人的麵前,所有的偽裝原形畢得特別淒慘。
“怎麽會有這麽多無關人員在這裏。”薄老爺子看向守在一旁的保鏢,“你們都是吃白飯的嗎?”
保鏢聽見這話,立馬過來趕人。
安母肯定是不樂意的。
安不敢自己站出來,隻能一個勁地朝著秦玥使眼,畢竟老媽輩分比高,多比有說服力。
秦玥著頭皮:“宴淮是因為我們家安凝的傷,我們守在這裏也是想看看他的況。”
Advertisement
“話要說清楚。”薄老爺子用看跳梁小醜的眼神盯著這一家三口,“火災的原因我會派人調查,安凝是我薄家的媳婦,自有我薄家照顧,你們也是傷員,不用杵在這兒,回去吧。”
秦玥臉一黑,難堪地真想這趟沒來過。
“老爺子,原因已經很清楚了,就是因為我家這個不爭氣的大兒啊。”安父做賊心虛,立馬說道。
薄老爺子冷笑一聲,擺了擺手。
周圍的保鏢會意,連忙上前拉走三人,還能給醫院騰個清淨。
安預不妙,抓了個空檔悄悄問秦玥:“媽,這到底是怎麽回事?”
秦玥心慌意,簡單說了經過。
安更是恨得麵部繃:“安凝怎麽就沒死在裏麵呢!”
可惜,太可惜了:“不過那傭人會不會把我們供出來?”
如果其他人來調查,他們還可以將這個黑鍋甩給傭人。
可現在薄老爺子親自調查,安不認為這老不死的家夥會覺得他們是無辜的。
“怪就怪安凝實在是太會討好人了!”秦玥咬牙切齒,“不就是會製香嘛!真搞不懂那老爺子為什麽會這麽喜歡!”
安聽見這話,靈一閃:“我們趁著這次的機會再查查安凝的嗅覺,可不能讓東山再起。”
“你的意思是?”秦玥瞬間明白們不能僅僅是查,“但現在手腳太容易被發現了。”
“難道你要眼睜睜看著安凝又憑著製香在那老不死的麵前賣乖嗎?”安攥住拳頭,目鷙,“我就是要弄得失去依仗!”
當初有意把安凝當做擋箭牌推出來與薄宴淮結婚,但過程並沒有那麽順利,是因為薄老爺子力排眾議,強著薄宴淮點頭同意的。
Advertisement
安當時還慶幸過這老頭也算是幫了自己的忙,可現在看來,薄老爺子就是回到薄宴淮邊最大的阻礙。
秦玥卻有些犯難,和自己兒當然是同一戰線,但現在這時機不好,非常不好,一不小心會反遭個碎骨。
“媽,我們如果不能趁安凝病要命,怕是隻有被死死住的命了。”安勸道。
好吧。
秦玥是不起兒的磨泡的,下定決定間,心中已有定奪:“做是得做,但不能我們親自做,要換一個人來做。”
安抬眸:“誰?”
“媽、妹妹,你們還好吧?”大哥安胤匆匆趕來,滿麵擔憂,“聽說你們遭遇火災了?怎麽樣啊,有沒有哪裏傷?”
“我們還好。”安瞬間明白了秦玥所指之人是誰了,安胤這可是來得正好,趕換上一副又憂愁又悲慘的樣子,“隻是宴淮哥哥的況不太好。”
“他怎麽了?”安胤聽到這兒,緒就淡了許多。
他其實不太喜歡薄宴淮,那人平日裏對他們就一副冷冰冰的模樣,好像他生來就是天,他們是地。
就這尊卑之分,關係能好起來才怪。
“我和你爸去找安凝,故意躲在房間裏不出來,那傭人又笨手笨腳地打翻了蠟燭,一下就著火了。”秦玥練地顛倒黑白,“我們大聲安凝出來,還是賴著不走,最後薄宴淮衝進去救,倒好,推人出來擋火,自己先逃出來了!”
“豈有此理!”安胤氣得臉大變。
他早知他這妹妹自私自利,但也沒料到對方已經到了這般不把人命當人命的發指地步。
Advertisement
怎麽能將救命恩人往外推呢!
“姐姐估計也是害怕吧。”安在旁邊假模假樣道,“畢竟當時的火勢那麽大。”
“心知火勢大,別人就不害怕了嗎?”安胤氣不過,“簡直是丟安家人家的臉!”
“唉,別說了。”安拉拉他的手腕,故作通達理,“哥,姐姐還在昏迷中呢,不如這次由你去照顧吧?”
“我去?”安胤反指自己,“我才不想照顧那個白眼狼!”
“我和媽媽本來是想去照顧的,可是薄老爺子把我們趕出來了。”安可憐,“我和媽媽又實在放心不下……”
“他為什麽把你們趕出來?”安胤蹙眉。
“薄老爺子對我們印象不太好,可能是平日裏姐姐……”安恰到好地言又止,“算了,不說這些了,姐姐的最重要。”
說著,扭頭看向旁邊的秦玥:“媽,不然我們再去試試?”
秦玥在旁邊迎合得相當無奈:“走吧,就算是再被趕出來也得試試!”
兩人一副關心心切的樣子,晾得一旁的安胤抿糾結:“算了,還是我去吧,正好也替你們解釋解釋。”
“哥,謝謝你!”安雙眸亮晶晶的,充滿了激。
安胤被安托付信任般地盯著,忽然升起一保護。
他直腰背,邁步上樓。
秦玥和安見他的背影逐漸消失在樓梯間,臉上原有的激瞬間消失不見。
兩人都沉著臉,眼裏迸發出惡狠狠的,如同寒針,恨不得悉數紮在安凝上。
霍垣趕來,正好將這一幕看在眼裏。
Advertisement
他的腳步一頓,心中的警鈴大作。
安的餘注意到他的影,角連忙上揚:“你也是來看姐姐的嗎?”
霍垣不想理,直接繞過兩人上樓。
秦玥見兒到如此冷待,直接開口嘲笑:“你管他做什麽?有的人就是喜歡在毒婦邊打轉,等他為下一個薄宴淮,被害了就老實了。”
“放幹淨點!”霍垣剛上了幾步臺階的腳步一頓,他不想跟們廢話,但這母倆實在太能挑釁人了,他沉下臉,轉頭,“別以為誰都不知道你們做的骯髒事!”
“你這話什麽意思?”安無辜反問,“我媽媽也是被姐姐自私的行為氣到了才會這樣說,不過,事實的確如此啊。”
“是嗎?”霍垣直視兩人,帶著若有若無的暗譏,“那就等真相大白吧,我聽說薄老爺子已經介調查了,是真相都不會被埋沒,能夠埋沒隻是調查真相的人心,我很想看看誰才是最險小人!”
話落,他轉就走。
“可惡!”安死死地咬住瓣。
“放心,現在的當務之急可不是對付這種人。”秦玥給順順氣,“你先按我說的去做,我去找那個傭人。”
套房。
約約的吵鬧聲在安凝的耳邊響起。
睫微著緩緩睜開眼睛。
醫院特有的消毒水味縈繞鼻尖,現在對這個味道沒有從前那麽排斥了,隻是,這回這味道有點重,讓沒來得及消化地想作嘔。
安凝朦朧的眼裏閃過一抹意外。
怎麽回事?
這消毒水的味道怎麽這麽濃?
“我是哥哥!我怎麽不能進去了?”安胤揪著保鏢的領子,眼神像要吃人。
“抱歉,這是薄老的吩咐。”保鏢不為所,由著男人手,堅持主見,半寸都不讓。
安胤試圖推開兩人,奈何在兩個彪形大漢麵前他就跟個小仔一樣:“我看應該是安凝吩咐你們這麽做的吧!”
“讓他進來吧。”安凝聲音嘶啞,嗓子幹到不行。
保鏢聽到聲音後,立馬了醫生護士過來。
一群人魚貫而,安胤也趁著這個機會了進去。
他在看到病床上安凝狼狽的模樣後,本能地嚇了一大跳。
不是說隻是暈倒嗎?
怎麽看上去這麽慘?比秦玥的臉看上去慘多了。
醫生仔細地給安凝做檢查,安凝的目反倒過隙,落到了自家這位哥哥上。
著實是沒料到這人會來看。
未出嫁之前,和兩個哥哥關係都不親,更別說現在。
“薄宴淮在哪裏?”安凝率先開口。
醫生的手一頓,沒回答。
“你還好意思問薄宴淮?”安胤一聽這話,那心裏生出來的同瞬間消散不。
“他怎麽樣?”安凝下顎繃,指尖抖。
醫生發現狀態不對,連忙回頭給了安胤一個警告的眼神。
隻可惜對方本就沒看懂他的暗示,鋪天蓋地當著一屋子醫務人員和保鏢麵力指責:“你這個白眼狼!你自己自私自利也就算了,現在居然連老公都要害!你還有沒有良心?”
“我問你他現在什麽況!”安凝就算不在乎麵子,也不想聽到多年不關心自己的哥哥,頭一句就是指責的話,他有什麽資格?從而頭一次發了飆。
眼眸裏似乎醞釀著滔天怒意,聲音冷得讓幾個護士不由了手臂。
安胤被這突如其來的彪悍所震懾,梗了梗,不敢再嘲。
“說話。”安凝直直盯著他。
“現在還在手室。”安胤渾一抖地口。
安凝的心在這一刻悄然停滯。
看向旁邊的醫生,強忍著的不適起:“請你們現在帶我過去。”
“這……”醫生想勸休息,可在對上淩冽的眼神後,識趣地讓護士推了把椅過來。
安凝被護士帶到手室門前,一眼就看到了坐在跟前的老者:“爺爺?你回來了!”
“孩子,你苦了。”薄老爺子輕輕握著安凝的肩,臉上的關心樣與剛才的冷漠完全不同,“怎麽不好好休息?上還痛不痛?”
安凝聽見這話,鼻尖一酸:“是我的錯,薄宴淮就這次是為了救我。”
“這隻是意外。”薄老爺子毫沒有要責怪的意思。
一向嚴厲的雙眸也在此刻溫和下來,帶著幾分顯而易見的慈。
“你無需自責,如果他沒有救你,我才要找他算賬。”
安凝眼眶紅紅,自責心更甚。
手室的門忽地傳來聲響。
醫生走出門來:“病人已經沒有生命危險了,現在要轉加護病房繼續觀察。”
“謝天謝地。”安凝狠狠鬆了口氣,忍了半天的眼淚悄悄自眼角落。
薄老爺子看上去並不意外,哼了一聲:“我就知道這臭小子福大命大,肯定會沒事的。”
安凝醒了醒鼻尖的酸,抱著老人道:“爺爺說得對,有您鎮著,他一定不會有事。”
此時,薄宴淮被幾名護士推了出來,推向病房。
兩人隨其後。
安凝看到病床上雙目閉的男人,忍不住又想哭了,當著爺爺麵,還是強行忍了下去。
從病房到手室的一路上,保鏢已將火災發生過程說了一遍。
安凝的口脹脹的,一酸痛的緒彌漫全。
從來沒有想過,薄宴淮竟然會在那樣的危急況下,僅僅是為了而不顧衝進火場。
為了。
真的是為了嗎。
他不是最恨的嗎?
安凝死死地攥著拳頭,但是眼淚就是止不住地往下掉。
薄老爺子的餘注意到這一幕,示意旁邊的管家。
管家適時遞上紙巾:“夫人您放心吧,爺已經沒事了,接下來好好養著便是。”
猜你喜歡
-
完結2195 章
首席的獨寵新娘
一場別有用心的陰謀,讓她誤入他的禁地,一夜之後卻被他抓回去生孩子!父親隻為一筆生意將她推入地獄,絕望之際他救她於水火。他是邪魅冷情的豪門總裁,傳聞他麵冷心冷卻獨獨對她寵愛有佳,可一切卻在他為了保護另一個女人而將她推向槍口時灰飛煙滅,她選擇帶著秘密毅然離開。三年後,他指著某個萌到爆的小姑娘對她說,“帶著女兒跟我回家!”小姑娘傲嬌了,“媽咪,我們不理他!”
431.7萬字8.33 195062 -
連載2623 章

閃婚夫妻寵娃日常
顧時暮是顧家俊美無儔、驚才絕艷的太子爺兒,人稱“行走荷爾蒙”“人形印鈔機”,令無數名門千金趨之若鶩。唐夜溪是唐家不受寵的大小姐,天生練武奇才,武力值爆表。唐夜溪原以為,不管遇到誰,她都能女王在上,打遍天下無敵手,哪知,遇到顧時暮她慘遭滑鐵盧…
448.4萬字8.18 139421 -
完結1277 章

偏執小舅,不許掐我桃花!
整個海城的人都以為,姜家二爺不近女色。只有姜酒知道,夜里的他有多野,有多壞。人前他們是互不相熟的塑料親戚。人后他們是抵死纏綿的地下情人。直至姜澤言的白月光回國,姜酒幡然醒悟,“我們分手吧。”“理由?”“舅舅,外甥女,有悖人倫。”男人冷笑,將人禁錮在懷里,“姜酒,四年前你可不是這麼說的。”一夜是他的女人,一輩子都是。
173.8萬字8.46 39115 -
連載12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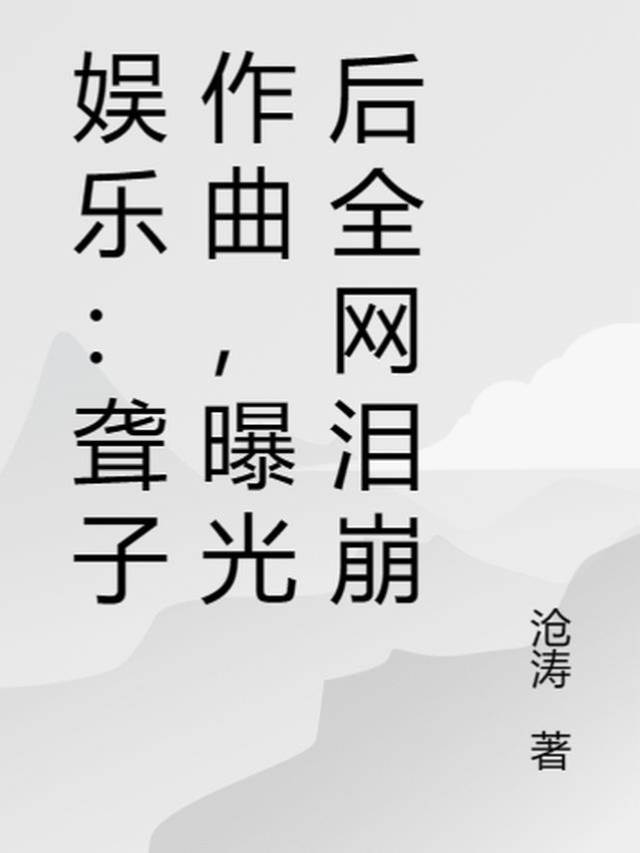
娛樂:聾子作曲,曝光後全網淚崩
微風小說網提供娛樂:聾子作曲,曝光後全網淚崩在線閱讀,娛樂:聾子作曲,曝光後全網淚崩由滄濤創作,娛樂:聾子作曲,曝光後全網淚崩最新章節及娛樂:聾子作曲,曝光後全網淚崩目錄在線無彈窗閱讀,看娛樂:聾子作曲,曝光後全網淚崩就上微風小說網。
23.8萬字8.18 5622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