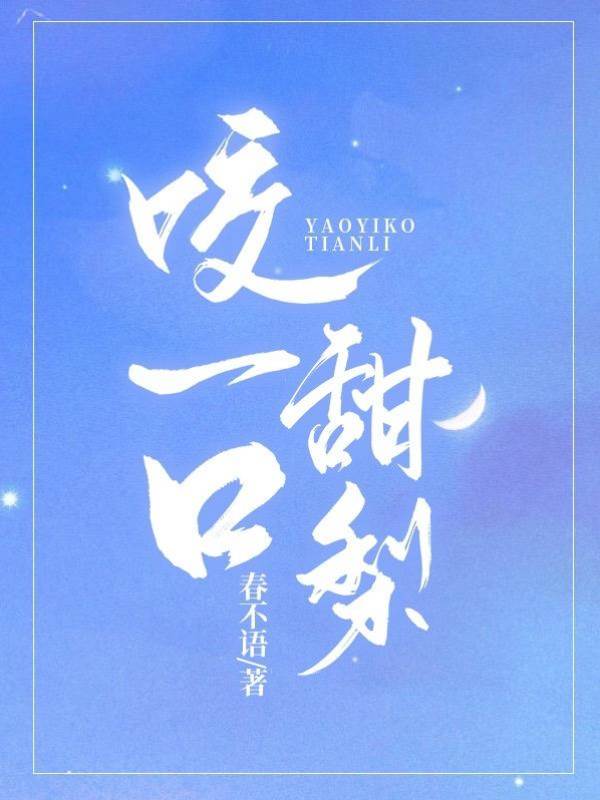《此夜長情》 第90章 按理說,她才是真正的孟景寒
孟晉州斜睨他一眼:“沒事不能來?”
“……”
孟鶴行覺得自己忍耐一個就夠了,這兩人子有時候真類似的,湊一塊簡直無敵了,比孟景寒一個姑娘還要矯。
好在,孟晉州并沒有想把他氣死,主開口:“路過,聞京銘非要拉著我上來嘲笑你一聲,我一想,也行,就來了唄。”
孟鶴行:“……”
在他被這兩人氣死之前,辦公室的門又開了。
這次,是司北泊。
后面跟著余珊和書辦的一個小助理,手上端著茶水,小心翼翼進來。
辦公室里莫名彌漫出一耐人尋味的氛圍,幾人暫時都沒出聲音,等茶水擺上桌,余珊和小助理退出去之后,才重新開始活絡。
孟鶴行斂了眉,著無端出現的司北泊,冷聲開口:“別告訴我你也是來加他們的。”
本來只想來問問晴山居項目的司北泊一臉懵,愣了會兒才緩過神來,像是窺破了新大陸,坐在沙發另一頭,笑問:“怎麼?還有我沒參與的樂子?”
話里的揶揄,任誰都聽得出來。
孟鶴行起,遠離這個是非之地,臨走前睨了聞京銘一眼,將他添油加醋的聲音拋在后。
——
抵達會面地點時,已經過了十二點。
一行人風塵仆仆,即使才坐了幾個小時的車,但空間有限,又沒有活筋骨,疲憊也油然而生。
Advertisement
行李件太多,直接暫時先放在車里,只提了輕便的裝備上了樓。
下榻酒店是提前安排好的,汪奪去詢問前臺,報上信息,不久就拿著幾張房卡回來。
催促著先上去放行李,等會兒下來吃飯。
樂隊見面時間定在兩點,時間倒是充裕。
司和譚希住一間。
簡單環顧了一圈,關上房門出來時,隔壁房間的人正好也出門。
是個高高瘦瘦的男生,銀白頭發,右耳上綴著銀耳鉆,最簡單的白T黑工裝,腳上踩著白運鞋,聞聲,看過來,又看了眼們的門牌號,角勾起淡淡弧度。
問:“你們是哪個樂隊?”
司正關上門鎖,鴨舌帽還扣在頭上,聽著譚希和那人對話:“你怎麼知道我們是樂隊的?”
男生回:“這一層都是,還有上一層,兩層房間都包下來了,供匯演的樂隊使用,你們不知道?”
們還真不知道。
但譚希也沒明說,只含糊其辭,三言兩語將話題揭過去。
沒聊幾句,譚希就套出了對方的基本信息,說了再見之后,跟司并排走,里還在細數:“凌空樂隊,張蘊免,天哪,子,這不就是前段時間很火的那個歌的團隊嗎,什麼來著……”
司淡淡開口:“化鯨。”
Advertisement
“對對對,沒錯。”譚希勾,“沒想到第一眼就見到帥哥了,福氣不淺。”
司摁下電梯鍵,看著飛快閃過的數字。
他們的房間在十二樓,坐電梯下去也得一會兒,數字跳到七時,電梯停了,門開,又有幾人上來。
這下,中途倒是沒在停過,直接下了一樓。
汪奪他們已經找好位置了,一樓的餐食是自取模式,也許是過了飯點,來吃飯的人并不多,空位很足。
司端了個盤子跟著譚希緩慢移著,要了些青菜,玉米,還有兩塊牛,最后又拿了碗魚片粥。
汪奪選了大型桌子,圍七個人還綽綽有余。
幾人一邊吃,一邊說著話。
司喝著魚片粥,勺子有一搭沒一搭地攪著,靜靜地聽他們說話,左邊是譚希,右邊是商余行。
譚希正在和他們說剛才遇見的那個人,嗓音清脆,商余行倒是安靜,只專注著吃著飯,偶爾說幾句話。
手機就在手邊,司喝著粥,翻看著實時新聞,微博熱搜榜上,登頂的又是紀疏雨,是一組走秀的路。
心下微凜,腦海里仔細搜尋著。
霍城以前從沒有對一個新人這麼大方過,就連喬淇念跟他這麼些年,也沒得過這樣的待遇,剛出頭就花大價錢捧,明擺著是要造勢。
Advertisement
又想起之前一閃而過的猜想,心里糾結許久,還是將紀疏雨的活照片順手轉給了孟鶴行。
指尖在屏幕上飛快地摁著。
還沒發送出去,對面就回復了。
【孟鶴行】:?
司將沒打完的字打完,然后發了過去。
又補充了一句:我只是覺得兩人有點像,就問一下。
那邊顯示正在輸中,很久都沒有發消息過來。
商余行略微傾著子往這邊看,司放下手機,聽他說話。
對方不知什麼時候取了碟糖醋排骨過來,放在面前,笑著說:“你最喜歡的菜,我記得上大學的時候你經常吃。”
澤人的排骨勾勒出糖,在潔白的碟子里安穩放著,旁邊放了薄荷葉作點綴,濃墨重彩,配合的相得益彰。
旁邊說話的幾人一時間也停了,都暗往這邊看。
譚希見司神淡淡,手將那碟子排骨拿了過來,放到桌子中間,笑道:“子保持材,不吃這麼多,排骨早就不是天天吃了,商師兄,我們分了你不介意吧?”
商余行雙手一攤,溫和地笑:“當然不介意。”
淡藍襯衫下是冷白的,他看了司一眼,又問:“你還想吃什麼嗎,我給你拿。”
“師兄。”司抬眸,角輕扯,“不用了,我已經差不多飽了,需要的話我自己會去拿的。”
Advertisement
商余行點點頭,沒再詢問。
那碟子排骨都進了丁暮他們的肚子,很快便一干二凈,底部只剩下些醬,淺褐又著紅,濃稠黏膩。
旁邊傳來一陣響,另一隊人也進了餐廳,都穿著統一的服,白上黑子,格外醒目。
司一眼就看見方才在房間門口遇見的那個男生。
張蘊免。
掃一眼,便垂下視線。
那人似乎也看見們,隔空勾,沖這邊揮了揮手。
手機屏幕又亮了。
是孟鶴行發來的一則消息。
司放下筷子,左手翻開對話框,那幾行文字,看得心頭一跳——
【孟鶴行】:確實像的,按理說,才是真正的孟景寒。
猜你喜歡
-
完結4816 章

帝少追緝令,天才萌寶億萬妻
第一次見面,她在20歲那晚遭受雙胞胎親姐姐算計,失去清白,而她,連他的臉都未曾看清。三年后她攜萌寶歸來,斗心機婊白蓮花,才發現姐姐的兒子竟和她的兒子長的一模一樣!“弟弟,有人欺負媽咪。”大寶氣紅了臉。“敢欺負媽咪?那就整到她破產!”二寶雙手…
868萬字8 39279 -
完結548 章

分手后和前任哥哥領證了
凌西顧,一個作風之狂妄霸道,權勢已膨脹到最高峰的男人!在他光鮮亮麗的外表下,卻有著不為人知的悲痛往事--與她離婚后,凌西顧坐不住了,驟然站起身:“哼,她丟了我這麼完美的男人,肯定會對人生喪失信心,頹廢度日,搞不好還會報復世界!為了世界和平,我就再給她一次機會……”“是哪個狗答應,兩年就離婚絕不糾纏的?”離開他后活得風生水起的夏雨墨,反問。瞧吧,他腹黑狠辣,可是他的小妻子卻敢罵他是狗、還虐狗……
93.9萬字8 9955 -
完結105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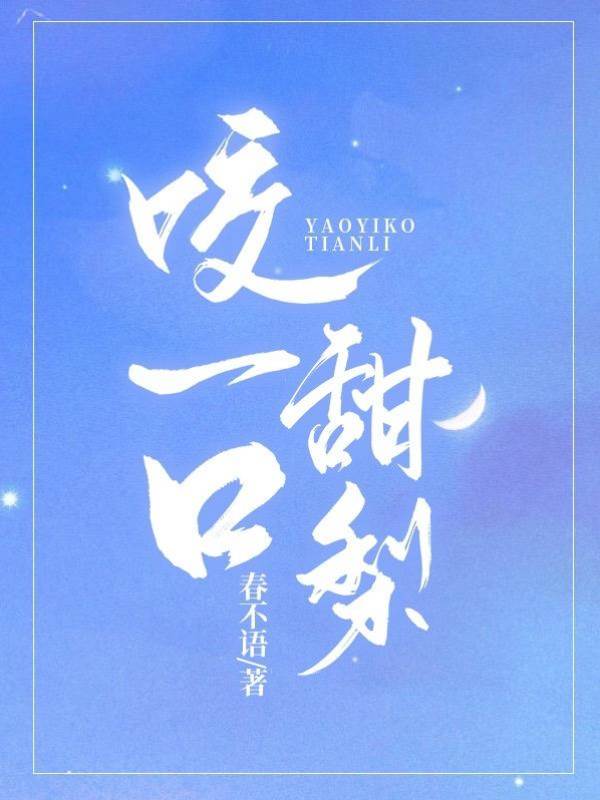
咬一口甜梨
白切黑清冷醫生vs小心機甜妹,很甜無虐。楚淵第一次見寄養在他家的阮梨是在醫院,弱柳扶風的病美人,豔若桃李,驚為天人。她眸裏水光盈盈,蔥蔥玉指拽著他的衣服,“楚醫生,我怕痛,你輕點。”第二次是在楚家桃園裏,桃花樹下,他被一隻貓抓傷了脖子。阮梨一身旗袍,黛眉朱唇,身段玲瓏,她手輕碰他的脖子,“哥哥,你疼不疼?”楚淵眉目深深沉,不見情緒,對她的接近毫無反應,近乎冷漠。-人人皆知,楚淵這位醫學界天才素有天仙之稱,他溫潤如玉,君子如蘭,多少女人愛慕,卻從不敢靠近,在他眼裏亦隻有病人,沒有女人。阮梨煞費苦心抱上大佬大腿,成為他的寶貝‘妹妹’。不料,男人溫潤如玉的皮囊下是一頭腹黑狡猾的狼。楚淵抱住她,薄唇碰到她的耳垂,似是撩撥:“想要談戀愛可以,但隻能跟我談。”-梨,多汁,清甜,嚐一口,食髓知味。既許一人以偏愛,願盡餘生之慷慨。
20.2萬字8 7738 -
連載217 章

孕期小哭包,瘋批老公輕點寵
寧嫵哭著后退,旁邊的婚紗潔白如雪,卻被撕碎。“寶寶,越來越不聽話了,哥哥真的會生氣的。”江祁聿扯著領帶一步步朝她走過去,臉上的表情十分陰郁強勢。漂亮精致的女孩搖著頭想逃跑:“我們不會幸福的,你明明不愛我!”她連續做了一個月的噩夢,夢里他們都只是書中形形色色,微不足道的小角色。她只是早日的惡毒前妻,哥哥才是別人的男主,哪怕結婚了他們也不幸福。本以為自己洗心革面,退出跟女主的爭奪,選擇成全他們自己就能逃脫既定結局的命運。誰知道身為男主的哥哥一改書中給與的高冷無情的角色設定,變得令人害怕恐懼,還要強取豪奪,拿孩子控制自己。江祁聿抓到她,把女孩緊緊地抱在懷里,重新給她穿上大紅色的婚服:“哥哥都拿命愛你了,掏心掏肺了,還不夠嗎寶貝。”男人看著她隆起的肚子眼底的偏執占有欲達到頂峰。“你今天不嫁也得嫁,我親愛的江夫人。”
37.9萬字8.18 153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