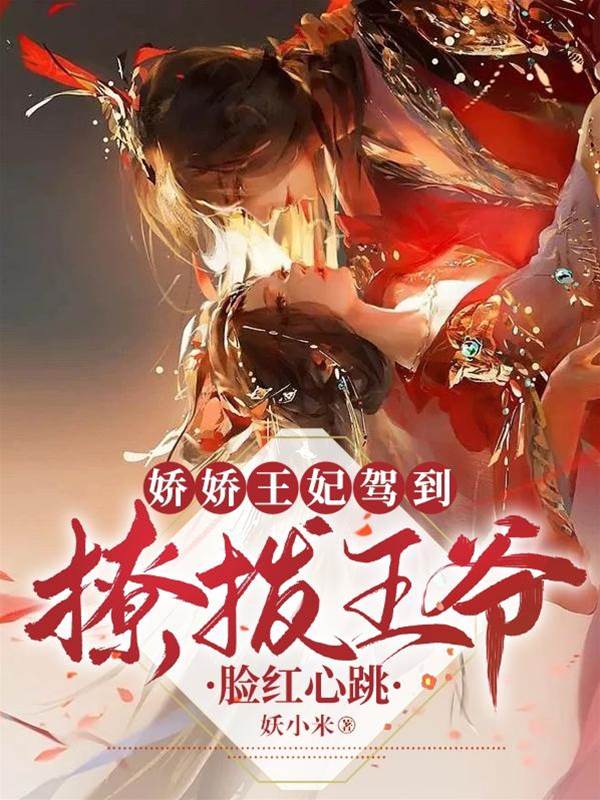《憐嬌奴,禁欲權臣夜夜寵》 第30章 穗和怎麼忍心離開他
裴景修無奈,只好退出去,靜靜守在門外。
穗和應該還活著吧,不然小叔也不會把人抱回來,還放到他床上。
裡面那麼安靜,不知道小叔是單純的守著穗和,還是在對進行什麼救治?
如果暈了,應該可以喂點水什麼的吧?
他有心想問一聲,要不要弄點蜂水來,又怕裴硯知再發火,猶豫著不敢去問。
他靠在牆上,兩條還是的,子還在止不住地發抖。
回想剛剛聽到雀兒說娘子死了的那一瞬間,他的心就像被一隻大手突然攥住,生生從腔裡撕扯出來的覺。
三年來,穗和早已為他生命的一部分,也是他的一部分。
他真的不能沒有穗和。
他捂著臉,慢慢靠牆蹲下,淚水濡溼了指。
他們的好日子才剛剛開始,穗和怎麼忍心離開他?
“起來,你這是做什麼?”閻氏隨後趕到,手將他拉起來,“娘不是和你說了,這事跟你沒關係,你這副失魂落魄的樣子,是要告訴別人你是殺人犯嗎?”
裴景修放下手,臉頹敗,再不復往日的意氣風發:“母親,你能別說了嗎,這事本來就是我的錯……”
“啪!”
閻氏抬手給了他一掌:“你的錯,你想給抵命是嗎,你想自己十幾年的辛苦付諸東流是嗎,你忘了咱孃兒仨捱過的白眼過的氣嗎,你忘了你發誓要出人頭地,把那些人統統踩在腳下嗎?”
裴景修捂著火辣辣的半邊臉,慢慢紅了眼,神從自責,慌,一點一點變得鬱,幽暗。
“母親息怒,您說的這些我都明白,但穗和應該沒有死。”他恢復了冷靜,聲音也平靜下來。
Advertisement
閻氏仍不罷休,再次強調道:“死不死都不是你的責任,是自己任妄為的結果,你若不咬死了這點,將來傳到外面,就是大麻煩。”
裴景修終於完全清醒過來,鬱的目裡又出幾分狠厲和決絕:“多謝母親提醒,兒子知道了。”
閻氏見兒子終於被自己打醒,這才鬆了口氣,著裴硯知臥房的亮語氣複雜道:“穗和是你的人,他一個做叔叔的,把侄媳婦抱回自己房裡,不覺得有失統嗎?”
裴景修臉變了變:“小叔可能也是一時急,沒顧上這些。”
閻氏說:“再急也不該這樣,不是還有阿信嗎,他為什麼非要親自抱?”
裴景修愣住,心裡不免也犯起了嘀咕。
恰好這時,阿信帶著一個大夫匆匆趕了過來。
裴景修釋然道:“阿信去請大夫了,這種事總不好讓小叔親自去。”
閻氏認為這個理由很牽強,但也沒多說什麼,母子二人跟在阿信和大夫後面進了屋。
裴硯知負手站在床前,白寢外面已經罩上了居家的玄青長衫,方才的慌張也好,憤怒也好,已盡數去,又恢復了往常那種古井無波,八風不的樣子。
因有大夫在場,他沒再讓裴景修滾出去,默默地往一旁挪了挪,給大夫讓出位子。
裴景修趁機上前,看向床上雙眼閉,死氣沉沉的穗和。
不過三日沒見,穗和整整瘦了一大圈,眼窩和兩邊臉頰都凹陷進去,眼下一片烏青,搭配白瓷般沒有的臉,要多可憐有多可憐,看得人想掉眼淚。
大夫在阿信搬來的凳子上坐下給穗和把脈,見裴景修上前,便問道:“病人是什麼原因昏厥的?”
Advertisement
裴景修面微訕,尚未開口,閻氏上來搶先道:“京中近來以細腰為,這丫頭為此節食,連著三天沒怎麼吃飯,方才不小心跌倒就昏過去了。”
“原來是的。”大夫頷首道,“如果單純是的,問題應該不大,老夫先給施針,等人醒了之後,喂些紅糖米湯給喝,過一個時辰,再進食稀粥糜,臥床靜養幾日,飲食清淡為主,慢慢就調養過來了。”
裴硯知雖然不滿閻氏的說辭,但大夫說問題不大,他總算鬆了口氣。
大夫從藥箱裡取出銀針,開始為穗和施針。
阿信出去吩咐雀兒煮米湯來。
裴景修和閻氏聽聞穗和沒什麼大礙,也都面喜。
閻氏忍不住嘟噥了一句:“我就說這丫頭賤命,沒那麼容易死。”
裴硯知聞言,剛舒展的眉頭又擰了起來。
“阿信,送大太太回西院休息。”他冷聲吩咐道。
當著外人的面,閻氏臉上有些掛不住,氣憤道:“硯知,我怎麼說也是你嫂子,長嫂如母,你對我這是什麼態度,難道在你眼裡我還沒一個小丫頭重要嗎,何況還是你侄子……”
“夠了!”
裴硯知見在大夫面前都不管不顧,忍了一晚上的怒氣再也不住:“重要的不是這個人,而是這個人不能死在我府上,倘若你們住在外面,誰死了都跟我沒關係。”
床上,穗和被銀針刺痛,悠悠醒來,聽到這句話,恍惚了一會兒,才意識到是裴硯知在說話。
穗和沒敢睜眼,心裡說不出是什麼滋味。
他說,重要的不是這個人,而是這個人不能死在他府上。
其實這樣說也沒錯,他們本來就沒什麼關係,他那樣的大人,自然犯不著為了自己這種螻蟻般的小人費神。
Advertisement
願意提點一二,是他的善舉,自己該恩戴德,不願意的話,自己也不該有什麼怨言。
正想著,耳畔傳來裴景修向裴硯知賠禮的聲音:“母親有口無心,也是事發突然慌了神,小叔多擔待。”
原來裴景修也在。
現在是什麼時辰了?
他什麼時候回來的?
是他回來給開門,才發現昏厥的嗎?
看到昏厥的時候,他心裡是什麼覺?
他會不會有一點點疚,悔恨,他還會再嗎?
穗和忍不住睜開眼,隨即震驚地發現,這本不是自己的房間,更不是的床。
床單被褥散發著淡淡的檀木香,憑著這香味,立刻判斷出是裴硯知的房間。
怎麼回事?
記得是昏倒在自己房間的,怎麼醒來卻在小叔床上?
到底發生了什麼?
穗和震驚地看向床邊站著的人,裴景修和裴硯知都在,閻氏也在。
見穗和睜開眼,裴景修很是歡喜,若非大夫正在扎針,恨不得立刻將摟懷中。
“穗……”
他張想要出的名字,卻被裴硯知一個眼風嚇了回去。
雖說大夫一般都會為病人保,但為防萬一,裴硯知不想讓大夫知道穗和的名字。
裴景修隨即也想到這點,改口道:“睡醒了,你現在覺怎麼樣?”
穗和聽到他溫的聲音,心中的委屈不控制地化作淚水流出來。
裴景修見掉淚,心疼不已,有心想為淚,又怕這樣不妥。
大夫終於施完了針,對裴硯知說道:“人沒事了,這幾日不要挪,臥床靜養,多吃流食,老夫再開一副調理腸胃的藥給服用就行了。”
Advertisement
“有勞了。”裴硯知淺淺道謝,吩咐阿信帶他出去寫藥方,付三倍的診金給他。
多出來的,自然是封口費。
大夫道謝,背起藥箱隨阿信一起告退出去。
臥房裡只剩下穗和四人。
裴景修這才上前拉住穗和的手,剛想安兩句,閻氏又搶先開口道:“穗和,你自己看看,你給大家添了多麻煩,景修平日對你那麼好,你就不能讓他省點心嗎,你覺得這事傳出去很彩嗎?”
穗和差點一口氣上不來又氣昏過去。
被裴景修鎖在房裡無人問津,怎麼到頭來又了的錯?
裴景修生怕兩人當著小叔的面絆起,打圓場道:“穗和剛醒,母親先說兩句,有話回頭再說不遲。”
說著就彎下腰去抱穗和。
“你做什麼?”裴硯知冷冷開口。
裴景修手一頓,忙道:“打擾了小叔大半夜,我把穗和抱回去,小叔也好早點歇息。”
裴硯知皺眉不悅:“你沒聽大夫說不能挪嗎?”
猜你喜歡
-
完結1252 章
壞壞王爺放肆愛
鳳傾傾重活一世,才知“深情”未婚夫渣,“熱心”手帕交毒,而對她生死不棄的,卻隻有那個她最憎恨的攝政王夫君。嚇的她趕緊抱緊攝政王的大腿:“我乖,我怕,我……求和!”男人邪魅一笑:“好,榻上合!”
144.4萬字7.2 34694 -
完結572 章
回眸醫笑:逆天毒妃惹不起
她,二十一世紀頂級醫學女特工,一朝重生,卻成了大將軍府未婚先孕的廢物大小姐。渣爹不愛?渣姐陷害?沒關係,打到你們服為止!從此廢物變天才,絕世靈藥在手,逆天靈器隨身,還有個禦萬獸的萌娃相伴,風華絕代,震懾九荒,誰敢再欺她?可偏偏有人不怕死,還敢湊上來:「拐了本王的種,你還想跑哪裡去?」納尼?感情當年睡了她的就是他?某王爺十分無恥的將人帶上塌:「好事成雙,今夜我們再生個女兒給小白作伴。」
98.1萬字8.18 45505 -
完結212 章
鐘娘娘家的日常生活
鐘萃是堂堂侯府庶女,爹不親娘不愛,但沒關系,鐘萃知道自己以后會進入宮中,并且會生下未來下一任皇帝。這些蹦跶得再歡,早晚也要匍匐在她腳下,高呼太后千歲。哪怕是對著她的牌位!這輩子,鐘萃有了讀心術,上輩子落魄沒關系,以后風光就行了,只要她能阻止那個要黑化,以全國為棋子的賭徒,在生母病逝于宮中后被無視冷漠長大的——她的崽。鐘萃都想好了,她要用愛感化他
75.3萬字8 17469 -
完結102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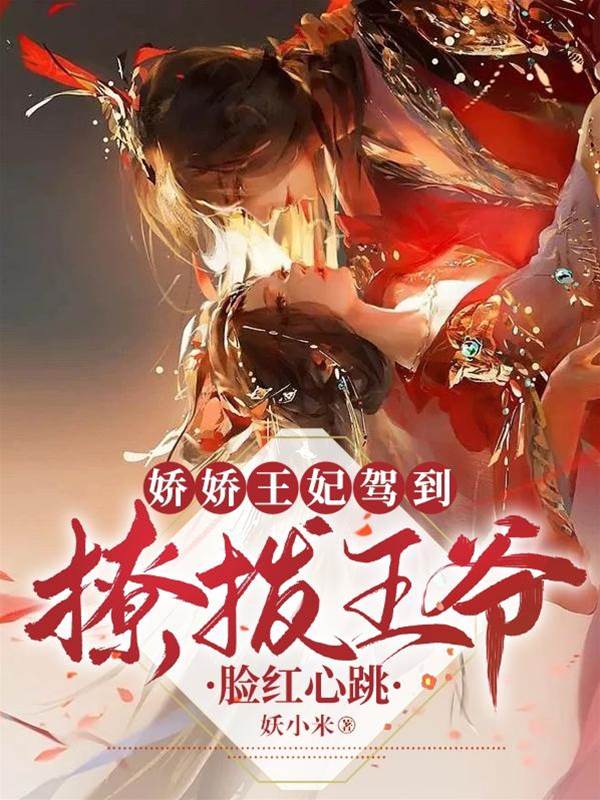
嬌嬌王妃駕到,撩撥王爺臉紅心跳
水洛藍,開局被迫嫁給廢柴王爺! 王爺生活不能自理? 不怕,洛藍為他端屎端尿。 王爺癱瘓在床? 不怕,洛藍帶著手術室穿越,可以為他醫治。 在廢柴王爺臉恢復容貌的那一刻,洛藍被他那張舉世無雙,俊朗冷俏的臉徹底吸引,從此後她開始過上了整日親親/摸摸/抱抱,沒羞沒臊的寵夫生活。 畫面一轉 男人站起來那一刻,直接將她按倒在床,唇齒相遇的瞬間,附在她耳邊輕聲細語:小丫頭,你撩撥本王半年了,該換本王寵你了。 看著他那張完美無瑕,讓她百看不厭的臉,洛藍微閉雙眼,靜等著那動人心魄時刻的到來……
183.7萬字8.18 106609 -
完結1249 章

農家小甜妻:腹黑相公寵不停
薛雙雙穿越成白溪村薜家二房的農家小姑娘,家里有老實爹,懦弱娘,小豆丁弟弟,還有一堆極品親戚。被大房搶走婚事,未婚夫上門退親?正好借此分家。買地種田蓋房子,發家致富奔小康。有人上門來提親,相公孩子熱坑頭。咦,腹黑相公的身份,好像不簡單?
232.4萬字8.18 113676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