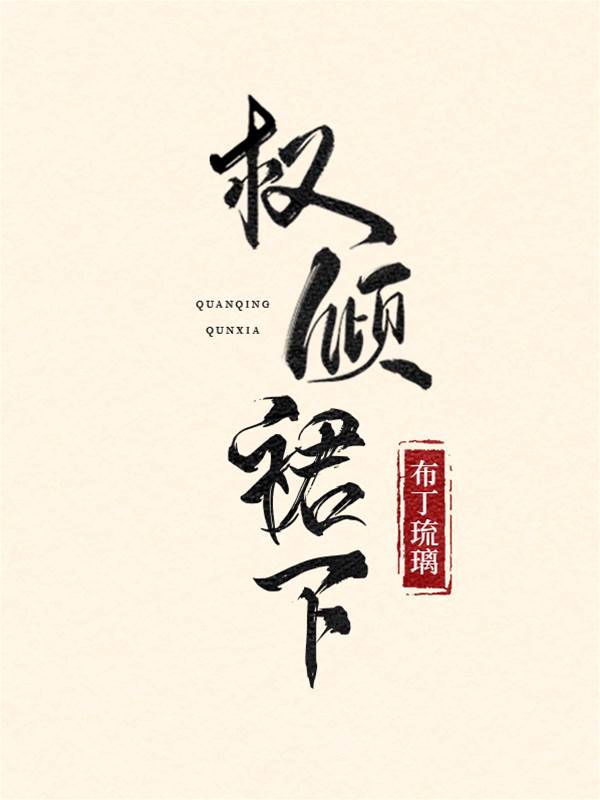《憐嬌奴,禁欲權臣夜夜寵》 第12章 求小叔憐惜
穗和到底還是沒抵抗住裴景修的循循善,為了父親,只得答應他,晚上送飯時和小叔提一提。
到了晚上,穗和存著討好的心思,把裴硯知的飯菜做得格外緻,服侍他用飯也十分殷勤。
裴硯知換了居家的玄青常服,古樸低調又深沉的,襯得他本就立的五更加深邃,搭配著手腕上的沉香珠串,越發顯得神不可捉。
好在穗和今晚做的飯菜很合他胃口,以至於他那總是沉凝的眉眼都舒展開來,消減了幾分拒人千里的冷漠。
穗和細細觀察著他的神,覺得此時是向他提出請求的好時機,便試探著說道:“小叔,我有件事想和您說。”
裴硯知放下手中的玉白湯匙,拿帕子在上了,這才掀眼皮看向:“什麼事?”
穗和張地吞了下口水,聲音綿很沒有底氣:“景修說,閣有個空缺,不是太要的職位……”
剛說到這兒,裴硯知原本舒展的眉宇又擰了起來。
穗和嚇得心尖一,餘下的話不敢再說。
“接著說。”裴硯知漠然道。
穗和遲疑了一下,著頭皮把剩下的話說完:“景修說安國公願意向陛下舉薦他,如果小叔也能捎帶著向陛下提一,會更加保險,景修這一路走來不容易,求小叔憐惜,給他一次機會。”
Advertisement
說完這話,已是愧難當,覺自己像是在行賄賄。
父親生前最不恥與這樣的人為伍,沒想到現在自己也了這樣的人。
裴硯知默然一刻,勾出一抹嘲諷:“難怪這幾日不見他人影,原來忙著跑呢!”
“跑”二字讓穗和更加愧,但還是小聲替裴景修申辯了一句:“景修說不是什麼要的職位。”
“呵!”裴硯知冷笑,“不是什麼要的職位,卻要同時用安國公和左都史的關係,他好大的排場!”
穗和無言以對,覺到他緒明顯不悅,默默垂下頭,不敢和他對視。
烏黑的髮如順的綢緞,隨著低頭的作從肩頭落前,將本來就小的小臉遮擋了大半。
裴硯知如水般冷沉的目落在頭頂,看著上面僅有的一銀釵。
釵頭垂下一粒素珍珠,孤零零地在烏髮間晃盪,如同茫茫大海上一葉孤舟,隨時會被浪頭吞沒。
他嘆口氣,到底還是緩和了聲調:“你想我幫他嗎?”
穗和已經嚇得要死,突然聽他這麼問,驚喜地抬起頭,大而澄澈的鹿兒眼帶著希冀看向他。
“景修確實很想得到這個機會。”孩子囁嚅著開口,隨即又補充道,“但如果舉薦他會對小叔有不好的影響,那就算了。”
兩人四目相對,雖然還是膽怯,卻沒有再躲閃。
Advertisement
裴硯知著,緩緩道:“後面那句也是景修說的嗎?”
“不,不是,是我說的。”穗和攥了攥手指,解釋道,“我雖然很希小叔能幫景修一把,但也不想小叔為難。”
“好,我知道了。”裴硯知倦懶地擺了擺手,“你先回去吧,此事我自有分寸。”
“多謝小叔。”穗和提了半天的心終於可以放下,恭敬地向他道謝,收拾東西離開。
裴景修就在月亮門那裡等著,見穗和回來,忙迎上去,接過手裡的食盒,迫不及待地問:“你和小叔說了沒有?”
“說了。”穗和回想方才的形,仍是心有餘悸,不想和裴景修復述細節,只輕聲道,“小叔說他知道了,讓我先回去,還說他自有分寸。”
“這麼說他是答應了?”裴景修很是歡喜,臉上綻放出舒心的笑意,在燈籠的映照下顯得格外溫潤如玉。
穗和看著他的笑臉,不知怎的,眼前竟閃過裴硯知映在燈下的冷沉眉眼。
裴景修沉浸在自己的喜悅裡,沒發現穗和的恍惚,一手拎著食盒,一手牽起穗和的手,引著慢慢往回走:“穗和,你真是我的福星,自從有了你,我沒有一不順遂的,為你贖真是我這輩子做過最正確的事。”
穗和沒說話,心裡怪怪的。
如果換作以往,這樣的春日夜晚,這樣的幽靜小道,這樣被裴景修牽著手,肯定會臉紅心跳,小鹿撞。
Advertisement
可是現在,滿心都是沒著沒落的惶恐和不安,覺自己像是水中一葉浮萍,不知下一刻會飄向何。
裴景修渾然不知,還在笑著誇:“穗和,你真是天生的旺夫命。”
旺夫命?
穗和鬼使神差地接了一句:“不知道有沒有旺妻命?”
裴景修一愣,繼而笑道:“自古妻憑夫貴,母憑子貴,你夫君我若仕途坦,不就是你的福氣嗎?”
他特地強調了“夫君”二字,以為穗和會像從前無數次那樣,聽到這兩個字就霞飛雙頰,不已。
可是並沒有,穗和只是愣愣地看著他,什麼也沒說。
妻憑夫貴,母憑子貴,這句傳了千年的老話,讓這個向來溫順乖巧的孩子平生第一次產生了一種很不舒服的覺。
但只是懵懵懂懂,自己也說不上來究竟哪裡不舒服。
“很晚了,郎君快去休息吧,有小叔和安國公助力,你一定會心想事的。”接過食盒,向廚房的方向走去。
裴景修察覺到的異樣,卻沒有去追。
穗和雖然子糯,其實骨子裡有著和父親一樣的清高孤傲,裴景修猜想,應該還是因著向小叔求的事,過不去心裡那道檻,認為自己走後門的行徑有失文人風骨。
可風骨這種東西,並非場必備,有時候,甚至不值一提。
Advertisement
宦海浮沉如同大浪淘沙,最終能在場風生水起,屹立不倒的,才是真正的贏家。
像穗和父親那樣的,再好的風骨又能如何?
但不管怎樣,穗和能打破自己心的原則向小叔開口,就說明的心還是向著他的。
的心裡,只有他。
這點他深信不疑。
所以,就算他以後娶了宋小姐,也還是會一如既往地對穗和好,絕對不會讓半點委屈。
裴景修這樣想著,轉回了自己的住。
有些事說再多也沒有用,等他進了閣,步步高昇,穗和看到果,自然就會想通這些事的。
現在,他只要做好準備,等著好事發生就行了。
可不知為何,心底約還是有些不踏實,這一次,小叔真的會幫他嗎?
猜你喜歡
-
完結441 章

將軍,夫人又要爬牆了
秦家有女,姝色無雙,嫁得定國公府的繼承人,榮寵一生繁華一生。可世人不知道,秦珂隻是表麵上看著風光,心裡苦得肝腸寸斷,甚至年輕輕就鬱鬱而終了。重活一世,秦珂還是那個秦珂,赫連欽也還是那個赫連欽,但是秦珂發誓,此生隻要她有一口氣在,就絕對不嫁赫連欽。
83.1萬字8 22482 -
完結13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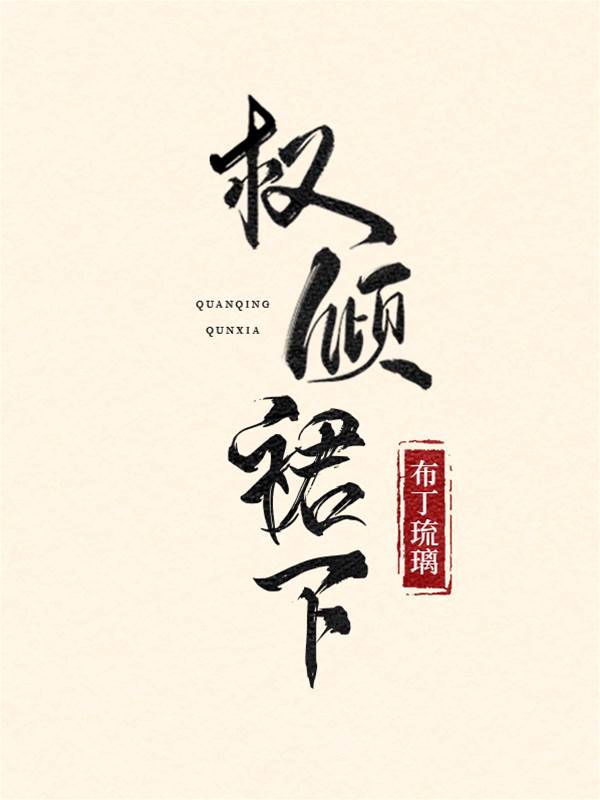
權傾裙下
太子死了,大玄朝絕了後。叛軍兵臨城下。為了穩住局勢,查清孿生兄長的死因,長風公主趙嫣不得不換上男裝,扮起了迎風咯血的東宮太子。入東宮的那夜,皇后萬般叮囑:“肅王身為本朝唯一一位異姓王,把控朝野多年、擁兵自重,其狼子野心,不可不防!”聽得趙嫣將馬甲捂了又捂,日日如履薄冰。直到某日,趙嫣遭人暗算。醒來後一片荒唐,而那位權傾天下的肅王殿下,正披髮散衣在側,俊美微挑的眼睛慵懶而又危險。完了!趙嫣腦子一片空白,轉身就跑。下一刻,衣帶被勾住。肅王嗤了聲,嗓音染上不悅:“這就跑,不好吧?”“小太子”墨髮披散,白著臉磕巴道:“我……我去閱奏摺。”“好啊。”男人不急不緩地勾著她的髮絲,低啞道,“殿下閱奏摺,臣閱殿下。” 世人皆道天生反骨、桀驁不馴的肅王殿下轉了性,不搞事不造反,卻迷上了輔佐太子。日日留宿東宮不說,還與太子同榻抵足而眠。誰料一朝事發,東宮太子竟然是女兒身,女扮男裝為禍朝綱。滿朝嘩然,眾人皆猜想肅王會抓住這個機會,推翻帝權取而代之。卻不料朝堂問審,一身玄黑大氅的肅王當著文武百官的面俯身垂首,伸臂搭住少女纖細的指尖。“別怕,朝前走。”他嗓音肅殺而又可靠,淡淡道,“人若妄議,臣便殺了那人;天若阻攔,臣便反了這天。”
52.5萬字8 22512 -
完結142 章

陛下今天也很好哄
蕭知雲上輩子入宮便是貴妃,過着千金狐裘墊腳,和田玉杯喝果汁,每天躺着被餵飯吃的舒服日子。 狗皇帝卻總覺得她藏着心事,每日不是哀怨地看着她,就是抱着她睡睡覺,純素覺。 是的,還不用侍寢的神仙日子。 蕭知雲(低頭)心想:伶舟行是不是…… 一朝重生, 爲了心心念唸的好日子,蕭知雲再次入宮,狗皇帝卻只封她做了低等的美人,還將破破爛爛的宮殿打發給她。 蕭知雲看着檐下佈滿的蛛絲,哇的一聲哭了出來。 誰知人還沒進去呢,就有宮人來恭喜婕妤娘娘,好聲好氣地請她去新殿住下。 蕭知雲(喜)拭淚:哭一下就升位份啦? 男主視角: 伶舟行自小便有心疾,他時常夢見一個人。 她好像很愛他,但伶舟行不會愛人。 他只會轉手將西域剛進貢來的狐裘送給她踩來墊腳,玉杯給她斟果汁,還會在夜裏爲她揉肩按腰。 他嗤笑夢中的自己,更可恨那入夢的妖女。 直到有一天,他在入宮的秀女中看見了那張一模一樣的臉。 伶舟行偏偏要和夢中的他作對,於是給了她最低的位分,最差的宮殿。 得知蕭知雲大哭一場,伶舟行明明該心情大好,等來的卻是自己心疾突犯,他怔怔地捂住了胸口。 小劇場: 蕭知雲想,這一世伶舟行爲何會對自己如此不好,難道是入宮的時機不對? 宮裏的嬤嬤都說,男人總是都愛那檔子事的。 雖然她沒幹過,但好像很有道理,於是某天蕭知雲還是大膽地身着清涼,耳根緋紅地在被褥裏等他。 伶舟行(掀開被子)(疑惑):你不冷嗎? 蕭知雲:……去死。 伶舟行不知道蕭知雲哪來的嬌貴性子,魚肉不挑刺不吃,肉片切厚了不吃,醬味重了會嘔,葡萄更是不可能自己動手剝的。 剝了荔枝挑了核遞到蕭知雲嘴邊,他神情古怪地問道:是誰把你養的這麼嬌氣? 蕭知雲眨眨眼(張嘴吃):……
22.6萬字8 2295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