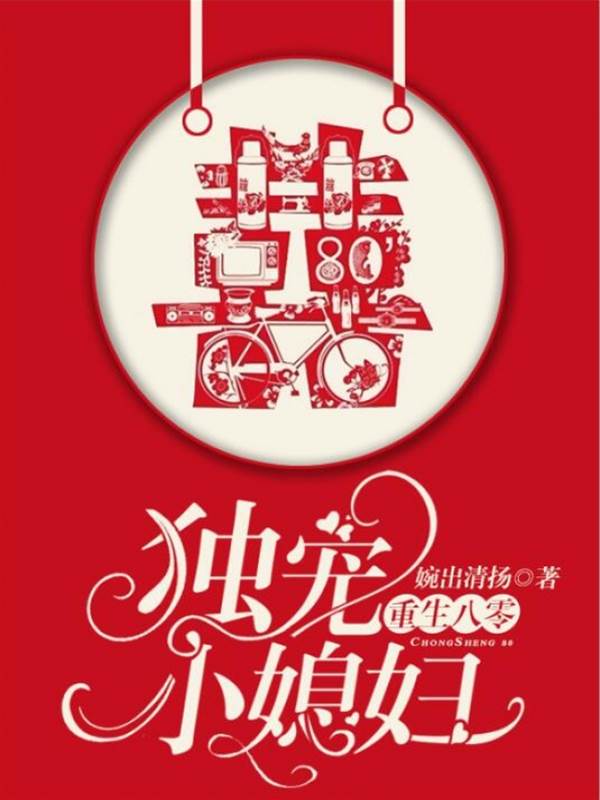《上嫁》 第368章 婚禮【二】
廂房的屏風外,擺了喜袍、冠、繡鞋和珠釵,紅紅火火的十八件‘過門禮’,了‘百年好合’的喜字。
程禧在梳妝鏡前,安安靜靜描眉,盤發。
“午宴在飯堂,是迎客宴,晚宴是正式婚禮。李家的賓客多,不得不分檔次。”大保姆介紹。
價貴的,在老宅,親自觀禮;價不夠貴的,在酒樓,錄影觀禮。
貴賓和普賓不同場。
沈、方、孟、錢四大家族的世,中午宅,其餘貴賓下午宅。
“方家的斌哥兒是伴郎。”大保姆笑,“你哥哥和老夫人商量了,瀚哥兒是伴娘!”
難怪,伴娘服大大,原來是沈承瀚的尺碼。
窗戶有雨聲。
庭院站了一個人。
棉喜褂,龍喜袍,腰間是金赤綢帶,拿了一副孔雀的新娘團扇。
風華毓秀,明豔灼灼。
在周家,周京臣試穿過喜服。
沒這麼隆重。
今天,英氣水的短髮,繫了新郎花,他白皙,眉目幽邃,無須上妝,自有一清貴的味道。
“京哥兒,瞧你媳婦兒!”大保姆攙著程禧出來。
男人側。
程禧很濃妝,周夫人不喜妖,管嚴格,偶爾比賽化妝,他十次有九次不在現場。
看過照片。
紅,蠻腰,霓彩舞。
小小年紀,亦是風萬千。
勾得男人心猿意馬。
霧濛濛下,周京臣面孔是溼潤的,彷彿一汪春,雙手作揖,“夫人。”
程禧回禮,“先生。”
“還老師呢!”他訓斥,“不好好讀歷史,古代新婚夫婦稱呼什麼?”
大保姆教,“京哥兒稱呼夫人,您稱呼夫君呀。”
程禧皮疙瘩,“我不喊。”
“不喊?”周京臣扭頭。
“你去哪——”
Advertisement
“誰喊我,我娶誰,直接房。”他搖扇子,朝傭人的廂房招呼,“未嫁的小保姆,老保姆的兒,有一個算一個——”
溜下臺階,肩之際,飛快喊,“夫君。”
男人一拽,“沒聽清。”
程禧蹦了一尺高,咬他耳朵,大吼。
周京臣險些聾了,腦仁震得嗡嗡響。
“嗎?”仰頭。
“小胖子。”
“小白臉。”
他握住手,塞了團扇。
程禧的冠十分奢華,所以不戴紅蓋頭了,大大方方炫耀,拜堂時,喜扇掩面。
“哥哥。”遮了一下面龐,眼睛水氾濫。
“嗯。”周京臣波瀾不驚。
“你沒回答,不?”
“湊合。”
不計較,“你俊。”
男人嚨溢位一聲笑,指二樓,“烤鴨。”
程禧一懵。
驀地,周京臣挨近,隔著薄薄的團扇,抵著。
睜大眼。
“極。”他笑意一瀉而下。
中堂。
老夫人在主座,周淮康夫婦在高堂。
一群喜婆圍繞在四周。
“京哥兒像畫中人似的。”保姆們調侃,“油頭面,招人。”
“阿姨,誇我,不誇,挑撥離間是吧?”周京臣佯裝氣憤,牽著程禧,“禧祖宗才是畫里人,我是金屋藏畫的狂徒。”
鬨堂大笑。
周夫人恨鐵不鋼,“以為他結了婚,更穩重了,沒想到越來越沒正形!”
停在中央,跪下。
喜婆捧了一碗餃子,程禧剛要吃,周京臣奪了勺子,啃了一口,吐了,“沒。”
“胡鬧!”老夫人啐罵。
周夫人踢他,“什麼沒?是生的!”
“已經生了禮禮。”他振振有詞,“多餘吃餃子。”
周京臣曉得,周家盼孫,李家盼兒孫興旺。
Advertisement
可他不盼。
禮禮出生,禧兒疼得要死要活,廢了半條命,他記得推出產房憔悴虛弱的模樣,不願疼第二次了。
大年初二,沈承瀚打電話拜年,提了這茬:權貴,豪門,哪家不是二胎三胎?沈、方兩家老太爺膝下各有四房子,搶著生孫輩,按‘人頭’分割家產。李氏家族家大業大,孫輩一代不爭氣,只剩周京臣延續香火了,生公子繼承份,生小姐上億的陪嫁,不缺錢,不缺名,就缺骨。
周京臣固執,“不生。”
“萬一禮禮出意外——”沈承瀚話糙理不糙,“多一個孩子,李家多一個保障。”
“禧兒沒了,生一窩孩子,沒意義。”周京臣仍舊固執,“我要禧兒。”
沈承瀚愣了。
高幹子弟叛逆,但大事上,是服從家族的。至沈家這邊的圈子,凡是高嫁,即使男人不催,人主生。
錢家的公子在酒桌上講:老婆可以另娶,男人有資本,年年做新郎,孩子才是脈傳承。
唯獨周京臣,妻大於子,妻大於孝義。
沈承瀚不由佩服他了。
周夫人比沈太太、方太太霸道專橫,周京臣這一年如何熬的,熬出名分,熬出婚禮,熬垮了華家,綠了葉家,又扛住了祝卿安...圈裡的子弟,沒有這份謀略和勇氣。
“新人敬茶——”喜婆捧了茶,給程禧,舉過頭頂,先敬了姑婆,再敬周淮康夫婦。
“父親,母親。”程禧磕頭。
周夫人心安理得喝茶,周淮康匆匆彎腰,扶,“禧兒,起來!地上涼。”
老夫人歡喜,訓誡周京臣,“你承諾我了,在李氏族譜記載禧兒是原配,不許離。”
周京臣莊重,“是。”
“你接管了李氏,納嫡系,禮禮是嫡重孫了。從今開始,老宅的二百多口子人,禧兒當家。”
Advertisement
程禧一怔,“我數學不及格...不擅長算賬...”
老夫人笑著問,“擅長什麼?”
又一怔。
糟了。
什麼都不擅長。
“擅長管理丈夫。”周京臣解圍,“禧兒脾氣大,吃醋,我怕了,李氏集團董事長沒有桃緋聞,口碑清白,是禧兒的功勞了。”
全場一陣笑。
程禧躲在團扇後,“你又欺負我。”
“這是欺負?”他瞥了一眼,“幫你打名聲呢,方圓百里說起小周太——”
周京臣賣關子。
好奇,“說我什麼?”
“大潑婦...周董事長懼。”
程禧氣得扇子一一顛的。
敬完茶,在庭院迎客。
孟家、錢家夫婦是初次見面,二位太太和善,各自帶了公子。孟家的公子是法,話不多,喚了二哥,二嫂,在角落喝茶;錢家公子是‘包租公’,名下幾十套門店收租,頗為好,老宅漂亮的小傭人,在廊簷下打罵俏。
沈家是最後場的。
程禧在中堂陪太太們閒聊,周京臣了沈承瀚出門。
“禧兒孃家的賓客只有舅舅一家,太寒酸了。我繼任了本地商會的會長,人人議論禧兒高攀了李家,這場婚禮,我打算讓禧兒出風頭,堵一堵外人的。”
沈承瀚領悟了,“我坐孃家桌,扮小叔叔?”
“李家親戚認識你,坐孃家桌也是婆家人。”周京臣一本正經分析。
“你什麼意思啊...”沈承瀚預不妙。
“扮個大姨,行嗎。”
扮個姨,便罷了,大姨...沈家小公子芳齡二十八,花樣年華...和‘大姨’實在不沾邊。
“你怎麼不扮!”沈承瀚瞪眼珠子。
“我扮了,新郎呢?”
“我當新郎,演什麼角不是演啊?新郎喝酒胃口遭罪,作為兄弟,我替你罪。”
Advertisement
周京臣目惻惻。
沈承瀚委屈,“我沒結婚呢!我扮大姨,傳遍了子弟圈,哪個姑娘嫁我啊。”
“換個角。”周京臣思索,“小姨,三姑,四嬸...”
“我扮小姨吧。”沈承瀚認命了。
和周京臣多年的發小,沒撈到好,吃盡了苦頭。
......
沈承瀚穿了大保姆的中式唐裝,戴了假髮,返回中堂。
正是熱鬧,他用鴛鴦喜帕擋了下,沒完全暴真容,鬼祟的姿勢顯得矜持。
有長輩發現他了,他不敢對視,小碎步迴避。
“二嫂的親戚?”錢家公子抓住。
沈承瀚尖著嗓子,“孃家小姨。”擔憂太假,又補充,“和新娘母親是雙胞胎姐妹。”
錢家公子上下打量他,再打量程禧,“二嫂是基因突變了,不像孃家人,幸好不像。”
沈承瀚往裡面走。
“喲!”周夫人撞上他,嚇一激靈,“這個大壯丫頭是孟家的兒?”
孟太太恰巧聽見,不高興了,“我哪生得出這樣的兒。”
“韻寧。”沈承瀚麻開口。
周夫人蹙眉。
“親家母。”他笑瞇瞇,拉周夫人的手,“多關照了。”
“你是?”
他演戲漸佳境,“禧兒的親小姨。”
周夫人覺得廓悉,仔細端詳他,“禧兒的小姨真啊...”
款唐裝小,在沈承瀚上是五分了,了一截小,茸茸的。
“是承瀚吧?”周夫人掀開喜帕,狠狠扔他臉上,“混賬小子!我手,直呼我大名,佔我便宜!”
錢太太和方太太拍手笑,“瀚哥兒從小一肚子壞水,現在更壞了,戲弄你周伯母了?”
沈承瀚踩著高跟鞋,四逃竄。
......
老宅外,整條街巷掛了囍燈籠。
一輛黑悍馬泊在巷子口。
車窗降了一半,葉柏南夾著煙,遙李家大門。
不知待了多久,了多久。
一名廚師走出西門,直奔這輛車,“李慕藍遞了訊息,宅的安保森嚴,沒機會接近程小姐。”
葉柏南猛吸一大口。
菸灰燙了手。
摁滅。
“通知周京臣,我參加婚禮。”
保鏢猶豫,“葉家沒請柬...”
“你去通知,他一定同意。”葉柏南靠著椅背,闔目養神。
保鏢邁進大門,和管家涉了一番。如果是別人,管家不搭理,偏偏是葉柏南,在業界是有威,有排面的,不好怠慢。
周夫人和周京臣在東南窗下,準備拜堂禮,管家引著保鏢走過去。
保鏢恭恭敬敬,“葉總與周公子、程小姐有,二位婚禮忘了葉總,葉總卻沒忘了禮數。”
弦外之音,是李家不懂禮數。
輕視了葉家。
周夫人面難堪,“他砸場子嗎?”
“婚禮誠邀了各界名流權貴,葉總天大的膽子也不會在李家的地盤砸場子。”保鏢不卑不,“若是李宅沒位置,酒樓添一個位置,葉總不挑剔。”
周京臣一張臉深沉,駭。
半晌,“請葉總宅,五號桌貴賓席。”
除了四大家族在主桌,五號桌是最面,最風的客席。
“京臣!”周夫人不樂意,“他來者不善。”
頭號的危險人,在眼皮底下,掌控他一舉一,反而安全;拒之門外,急了他,倒是惹麻煩。
猜你喜歡
-
完結853 章

他是人間妄想
人間妖精女主VS溫潤腹黑男主 三年後,她重新回到晉城,已經有了顯赫的家世,如膠似漆的愛人和一對可愛的雙胞胎。端著紅酒遊走在宴會裡,她笑靨如花,一轉身,卻被他按在無人的柱子後。他是夜空裡的昏星,是她曾經可望不可即的妄想,現在在她耳邊狠聲說:“你終於回來了!” 她嘴唇被咬破個口子,滿眼是不服輸的桀驁:“尉先生,要我提醒你嗎?我們早就離婚了。”
148.9萬字8 178764 -
完結455 章

成了前任舅舅的掌心寵
“你是我陸齊的女人,我看誰敢娶你!”交往多年的男友,娶了她的妹妹,還想讓她當小三!為了擺脫他,顏西安用五十萬,在網上租了個男人來結婚。卻沒想到,不小心認錯了人,她竟然和陸齊的小舅舅領了 證。他是國內票房口碑雙收的大導演,謝氏財團的唯一繼承人,也是那個惹她生氣後,會在她面前跪搓衣板的男人!有人勸他:“別傻了,她愛的是你的錢!” 謝導:“那為什麼她不愛別人的錢,就愛我謝靖南的錢? 還不是因為喜歡我!”
39.9萬字8 23726 -
完結40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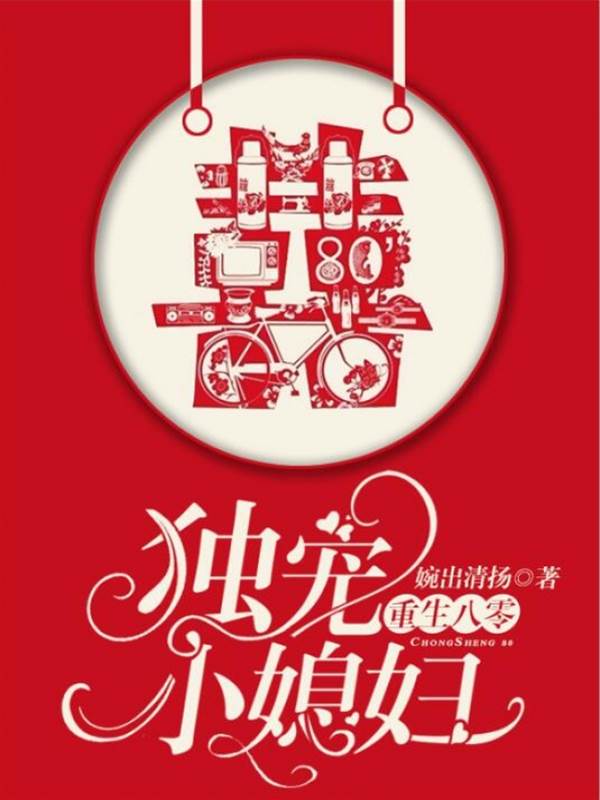
重生八零:獨寵小媳婦
九十年代的霍小文被家里重男輕女的思想逼上絕路, 一睜眼來到了八十年代。 賣給瘸子做童養媳?!丟到南山墳圈子?! 臥槽,霍小文生氣笑了, 這特麼都是什麼鬼! 極品爸爸帶著死老太太上門搗亂? 哈哈,來吧來吧,女子報仇,十年不晚吶,就等著你們上門呢!!!
72萬字8 960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