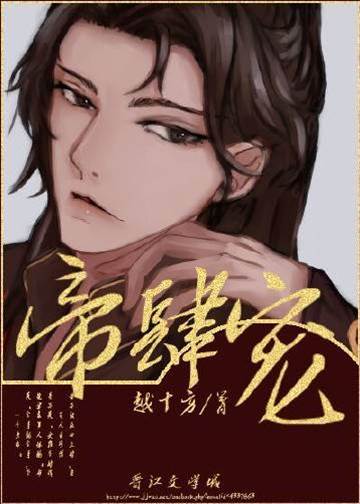《病嬌瘋寵,暴君掐著她的腰叫乖乖》 第115章
V這種事,大家不可能不知道,包括寧昀,但是他既然沒有阻止,說明八是真的打算要給威遠侯府和晉王聯姻。
這件事,寧寒嶼也想的明白。
他若是要破壞晉王府和威遠侯府的聯姻,就必須從別的地方想辦法。
看見底下跪著的黑人,他使了個眼,把人招上前來,對他耳語了幾句,那人便離開了。
此時已經夜,遲挽月待在寧懷昭的營帳裏,正在給他換藥。
寧懷昭赤著上,坐在床上,遲挽月手中拿著一卷白布正在纏繞在傷口。
因為傷在後背肩胛骨,有些不方便,遲挽月的行有些笨拙,纏到後背的時候,不得不傾窩在寧懷昭懷裏,半抱著他。
兩個人不得不親接,尤其是遲挽月的小臉無意中蹭到他前的皮時,整張臉都紅了,作也變得有些慌張無措。
寧懷昭垂眸,看著的模樣,角不由得勾了起來,眼尾纏繞著縷溫與風流。
“阿寶。”
他刻意低頭湊近遲挽月,聲音低沉,帶了幾分若有若無的蠱。
那聲音曲曲折折的鑽進遲挽月的耳朵裏,惹得覺得從耳朵到後背都是麻的,手一抖,手中的白布就掉在了他後。
Advertisement
遲挽月慌張起,看都不敢看寧懷昭,眼睫,像是振翅膀的蝴蝶。
隻是,寧懷昭不讓如願,手攬住了的腰。
隨著他的力道,遲挽月本就站不穩,直接倒在了寧懷昭的懷裏,小臉著他的皮,燙的忍不住了一下,手不由自主的握拳。
“阿昭,你……你先放開我。”
“不放。”
寧懷昭的聲音很輕,帶了幾分氣音,從遲挽月的耳邊掠過,帶來一陣陣的栗。
“阿寶的上怎麽這麽香?”
寧懷昭眼中盛滿了笑意,瞧見這樣的遲挽月,便越發起了逗弄的心思。
遲挽月果然被撥的說不出話,隻察覺到寧懷昭的落在的耳邊,一一吻過的耳緣、耳垂、耳後。
遲挽月覺得自己的上像是被熱氣熏過似的,燙的難,聲音的,帶了幾分無意識的和嗚咽:“阿昭。”
寧懷昭的眼睛一寸寸的變紅,本來隻是想要逗逗懷裏的人,沒想到他的火也全部燒了起來。
寧懷昭攬著遲挽月的腰,手臂用力,把的子朝著自己懷裏。
遲挽月仰著小臉,笨拙的回應著。
Advertisement
兩個人之間的曖昧氣息一點點升高,仿佛連帶著房間裏的溫度都跟著燃燒了起來。
外麵有宮端著水盆進來,看見這一幕,嚇得倒一口涼氣,連忙轉過去。
“王爺恕罪,小郡主恕罪。”
遲挽月猛然反應過來,推了推寧懷昭,想從他懷裏離開。
這作扯到了寧懷昭後背的傷口,疼的他皺了一下眉頭,卻的抱著遲挽月沒有鬆手,轉頭看了一眼那個站在門口背對著自己的宮,語氣裏帶了幾分不悅:“出去,沒本王的吩咐不準進來!”
“是。”
宮連忙走了出去。
營帳裏頓時隻剩下寧懷昭和遲挽月兩個人,空氣頓時又變得有些尷尬起來。
遲挽月抬眼去看寧懷昭,眼裏帶著幾分怯,咬了咬角問道:“你不怕宮出去胡說啊?”
寧懷昭的眼睛仍然是紅的,像是紅寶石一樣,縷縷亮的紅在它眼中纏繞運行。
“胡說?阿寶倒是說說能胡說什麽?”
遲挽月一噎,那倒也是。
他們兩個人是實實在在的有,從一開始就沒有避諱過,像這種親的舉雖然在外人眼裏看來傷風敗俗,不知廉恥,遲挽月卻覺得是喜的一種表達。
Advertisement
看的表,寧懷昭眼裏泛濫出一片片笑意,睫翻飛,垂著眼去親遲挽月的。
遲挽月的不行,忍不住後退了一步:“我先給你包紮好。”
站起,拿起來他後的白布,認真的給寧懷昭包紮好了以後,才把衫披在他上。
看忙完,寧懷昭手拉住的手腕,把人拉進了自己懷裏。
昏黃燈影下,兩個人的影,疊著打在營帳中,看起來甜恩。
“阿昭,你說皇上這次會不會給我們賜婚啊?”
看著麵前乖的小姑娘,寧懷昭的心裏便覺得了一片,泛濫氤氳出無盡意。
“應當快了。”
聞言,遲挽月的眼裏也落層層疊疊的笑意:“希如此,不然的話,我還要提心吊膽。”
寧懷昭不由得輕笑:“提心吊膽的應還是本王才對。”
就在今天,寧寒嶼還朝著寧昀想要下遲挽月,他知道,像寧寒嶼這樣抱著目的的人不在數。
遲挽月靠在寧懷昭前,也想起來了今天寧寒嶼的那一幕。
“阿昭,我覺得那個寧寒嶼一定是存心搞破壞,真是太討厭了。”
寧懷昭想了想,忽然瞇了瞇眼睛。
Advertisement
“阿寶,你說今日的刺殺與他有沒有關係?”
遲挽月從他懷裏抬頭,對上寧懷昭的眼睛:“阿昭的意思是?”
“知道皇上臨時加了比賽的定然是參與遊獵的人,今日寧寒嶼突然提出賜婚已經在意料之外,他又不知死活的來挑釁。”
真的隻是為了來惡心惡心他嗎?
遲挽月坐直了子,表也變得嚴肅起來。
“我今日還同我爹說,那些黑人似乎並不想要我的命,所以留,不然的話,你恐怕還沒去,我的命就沒了。”
“那如果真是寧寒嶼的話,他是想做什麽?”
寧懷昭若有所思,眼睛裏逐漸落狠戾,帶著層疊寒霜。
“有可能是想用你來挾持威遠侯府或者是本王,也有可能……”
他頓了頓,低頭看向遲挽月,說出了另外一種可能。
遲挽月眨了眨眼睛,追問了一句:“有可能什麽?”
寧懷昭看了一眼,手拂過的眉眼,聲音語氣裏帶著抑的怒氣和擔憂。
“他明知皇上不會將你賜給他,卻還是提出了賜婚,阿寶,你覺得另外一個可能是什麽?”
猜你喜歡
-
連載3575 章

錦鯉棄婦:隨身空間養萌娃
一覺醒來,安玖月穿成了帶著兩個拖油瓶的山野棄婦,頭上摔出個血窟窿。米袋裡只剩一把米;每天靠挖野菜裹腹;孩子餓得皮包骨頭;這還不算,竟還有極品惡婦騙她賣兒子,不賣就要上手搶!安玖月深吸一口氣,伸出魔爪,暴揍一頓丟出門,再來砍刀侍候!沒米沒菜也不怕,咱有空間在手,糧食還不只需勾勾手?且看她一手空間學識無限,一手醫毒功夫不減,掙錢養娃兩不誤!至於那個某某前夫……某王爺邪痞一笑:愛妃且息怒,咱可不是前夫,是『錢』夫。
322.4萬字8.08 312731 -
完結8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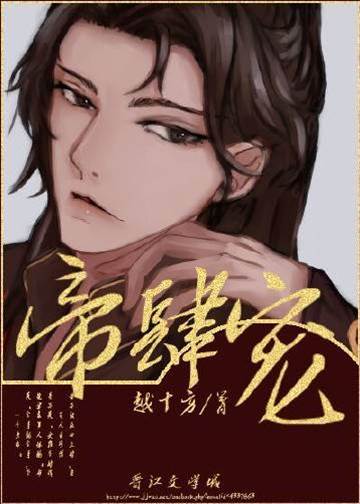
帝肆寵(臣妻)
從軍六年渺無音訊的夫君霍岐突然回來了,還從無名小卒一躍成為戰功赫赫的開國將軍。姜肆以為自己終于苦盡甘來,帶著孩子隨他入京。到了京城才知道,將軍府上已有一位將軍夫人。將軍夫人溫良淑婉,戰場上救了霍岐一命,還是當今尚書府的千金,與現在的霍岐正當…
28.8萬字8 26490 -
完結451 章

歡恬喜嫁
前麵七世,徐玉見都走了同一條路。這一次,她想試試另一條路。活了七世,成了七次親,卻從來沒洞過房的徐玉見又重生了!後來,她怎麼都沒想明白,難道她這八世為人,就是為了遇到這麼一個二痞子?這是一個嫁不到對的人,一言不合就重生的故事。
81.3萬字8 15677 -
完結532 章
醫庶無雙
原主唐夢是相爺府中最不受待見的庶女,即便是嫁了個王爺也難逃守活寡的生活,這一輩子唐夢註定是個被隨意捨棄的棋子,哪有人會在意她的生死冷暖。 可這幅身體里忽然注入了一個新的靈魂……一切怎麼大變樣了?相爺求女? 王爺追妻?就連陰狠的大娘都......乖乖跪了?這事兒有貓膩!
103.5萬字8 19364 -
完結206 章

賠罪
施綿九歲那年,小疊池來了個桀驁不馴的少年,第一次碰面就把她的救命藥打翻了。 爲了賠罪,少年成了施綿的跟班,做牛做馬。 一賠六年,兩人成了親。 施綿在小疊池養病到十六歲,時值宮中皇子選妃,被接回了家。 中秋宮宴,施綿跟在最後面,低着頭努力做個最不起眼的姑娘,可偏偏有人朝她撞了過來,扯掉了她腰間的白玉銀環禁步。 祖母面色大變,推着她跪下賠禮。 施綿踉蹌了一下,被人扶住,頭頂有人道:“你這小姑娘,怎麼弱不禁風的?” 施綿愕然,這聲音,怎麼這樣像那個與她拜堂第二日就不見蹤影的夫婿?
33.9萬字8.18 4105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