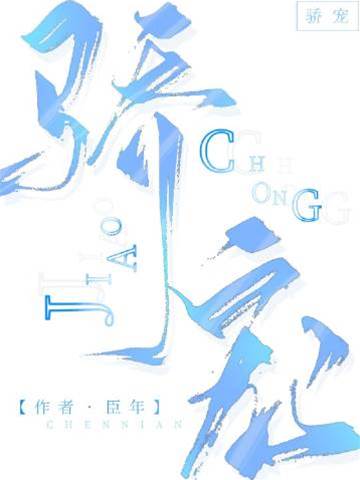《聲色犬馬》 第27章 別喊疼
他把比作狗,並不稀奇。
早就知道,是聶知熠的一條狗。
他很霸權的,隻許讓他的狗為他一個人服務。
疼的冒汗,指尖都麻了。
“別喊疼。”他不耐煩地皺眉頭:“為了別人弄的傷痕累累,我這裏不認。”
把嗓子眼裏的又咽回去了。
他折騰夠了才鬆開手,點燃了一支雪茄,卻不吸,夾在指尖,任憑那煙霧繚繞盤旋在的頭頂。
被嗆的咳,一咳口就痛。
“聶先生。”好容易憋住:“今天的事,想必羅家人已經去聶家興師問罪了,老爺子他們很生氣吧?”
說到這裏,聶知熠挑了挑眉。
這倒是真的,他父親聶廣生最討厭這種事,聶振的花邊新聞搞得人盡皆知,他一打開手機就是兩公婆在醫院互毆的小視頻,聶家有頭有臉,搞出這種事實在是有辱門風,老爺子被氣的吃了兩次降藥。
Advertisement
晚上羅家人帶著羅瑞欣來聶家,羅院長的父親和老爺子有深,還曾經救過老爺子一命,羅家人不搬出那陳芝麻爛穀子的事說事,再說這事本來就是聶振的錯,聶老爺子都用了家法,給了聶振實實在在的一龍頭拐杖,讓他跟羅瑞欣道歉。
這事看上去這麽了了,但聶家人在羅家人的麵前從此就氣短了。
羅家人走後,聶廣生讓兒子去書房跪著,什麽時候老爺子氣消了,什麽時候起來。
聶家倒也不是家教那麽森嚴,老爺子氣在聶振在外麵吃卻這麽不小心,竟然被羅家人抓住了把柄,大罵他蠢,大罵他攻心。
“聶先生。”翟雙白見他角略勾,知道都猜對了。
他低眸:“你想說,你這麽做是為了新水城的項目?”
Advertisement
“不然呢,聶先生,郭總的長約不值得我做這麽大的犧牲吧。”
他把手指間快要燃盡的煙頭彈進對麵洗手間的水池裏,手拽了拽領帶,仰頭靠在椅背上。
他沒再說話了,就這麽一不地保持這個姿勢很久很久。
“聶先生。”翟雙白小心翼翼地喚了他一聲,他也沒有任何靜,甚至還發出了低低的均勻的呼吸聲。
用手肘撐起看了看,聶知熠好像睡著了。
他們一起連過了兩夜,聶知熠好像都在失眠。
他對自己果然了解,困的時候自然會睡著。
惡魔睡著的時候,還是惡魔,他的呼吸聲都像是魔咒,纏繞著翟雙白,聽得心煩氣躁。
不過,半個小時後聶知熠就醒了。
他是瞬間醒來的,醒了之後就若無其事地整理領帶。
Advertisement
他自己打不好領帶,翟雙白隻能忍著疼長胳膊幫他打。
他的目始終在審視,鋒利的手刀一般的目在臉上千刀萬剮。
打完了剛準備回手,他握住了的手腕。
“翟雙白,我不要求你忠心耿耿,但你記住了,收人錢財替人消災,下次再搞這種為別人拚命的事,我會一一拆掉你的骨頭。”
他猛地鬆開,跌落床上,整個膛都痛的要裂開了。
猜你喜歡
-
完結96 章
再見及再愛
家道中落,林晞卻仍能幸運嫁入豪門。婚宴之上,昔日戀人顏司明成了她的“舅舅”。新婚之夜,新婚丈夫卻和別的女人在交頸纏綿。身份殊異,她想要離他越遠,他們卻糾纏得越來越近。“你愛他?”他笑,笑容冷厲,突然出手剝開她的浴巾,在她耳朵邊一字一句地說,“林晞,從來沒有人敢這樣欺辱我,你是第一個!”
17.2萬字8.18 20793 -
完結1965 章

盛寵名門佳妻
旁人大婚是進婚房,她和墨靖堯穿著婚服進的是棺材。空間太小,貼的太近,從此墨少習慣了懷裡多隻小寵物。寵物寵物,不寵那就是暴殄天物。於是,墨少決心把這個真理髮揮到極致。她上房,他幫她揭瓦。她說爹不疼媽不愛,他大手一揮,那就換個新爹媽。她說哥哥姐姐欺負她,他直接踩在腳下,我老婆是你們祖宗。小祖宗天天往外跑,墨少滿身飄酸:“我家小妻子膚白貌美,給我盯緊了。”眾吃瓜跟班:“少爺,你眼瞎嗎……”
284.1萬字8 29639 -
完結43 章

我的愛生生不息
雲知新想這輩子就算沒有白耀楠的愛,有一個酷似他的孩子也好。也不枉自己愛了他二十年。來
4.3萬字8 13074 -
完結493 章

甜心玩火:誤惹霸情闊少爺
訂婚宴當天,她竟然被綁架了! 一場綁架,本以為能解除以商業共贏為前提的無愛聯姻,她卻不知自己惹了更大號人物。 他…… 那個綁架她的大BOSS,為什麼看起來那麼眼熟,不會是那晚不小心放縱的對象吧? 完了完了,真是他! 男人逼近,令她無所遁逃,“強上我,這筆賬你要怎麼算?”
90.4萬字8 37776 -
完結77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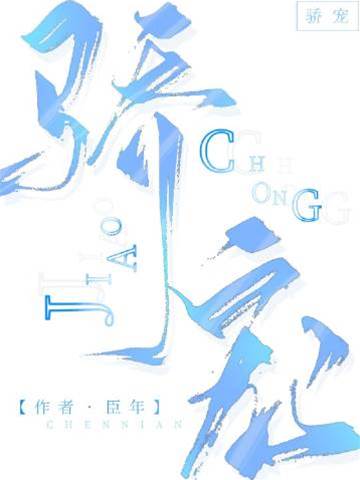
驕寵
作為國家博物館特聘書畫修復師,顧星檀在一次美術展中意外露臉而走紅網絡,她一襲紅裙入鏡,容顏明艷昳麗,慵懶回眸時,神仙美貌顛倒眾生。后來,有媒體采訪到這位神顏女神:擇偶標準是什麼?顧星檀回答:我喜歡桀驁不馴又野又冷小狼狗,最好有紋身,超酷。網…
31.3萬字8 4218 -
完結503 章

沈總別虐了,夫人和新歡約會上熱搜了
結婚三週年紀念日那天,沈澤撂下狠話。 “像你這樣惡毒的女人,根本不配成爲沈太太。” 轉頭就去照顧懷孕的白月光。 三年也沒能暖熱他的心,葉莯心灰意冷,扔下一紙離婚協議,瀟灑離開。 沈澤看着自己的前妻一條又一條的上熱搜,終於忍不住找到她。 將她抵在牆邊,低聲詢問,“當初救我的人是你?” 葉莯嫌棄地推開男人,“沈總讓讓,你擋着我約會了。”
36.8萬字8 3364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