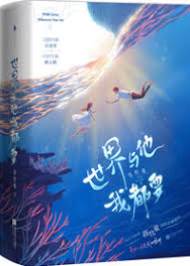《崇樓如故》 第37章 等著機會要他的命
連夜,秦修遠趕往江北,翌日,沈崇樓整理好秦家商鋪火災的證據,來到雲錦坊。
下人好茶好點心招待沈崇樓,正襟危坐在上方的沈崇樓並沒有,他沒見到秦修遠,隻見到了秦修遠的書許致遠。
“他人呢?”沈崇樓問。
書搖頭:“不知道。”
“不知道?秦修遠最信任的就是你,況且,你的名字都是秦修遠取的,你跟我說不知道他去哪了?”
沈崇樓話畢,扯角,冷笑了一下,顯然不信。
不過,這是秦修遠的書,不和他說實話也能理解,繼續追問沒意思。
沈崇樓的手指敲了敲桌麵上的檔案袋,接著朝書投去淩厲的眸:“如故跪著求他,他定然是答應了如故不再提親,可我聽父親那邊的人說,秦修遠非但沒有撤回那樣的換條件,還造謠生事說我和如故有了關係。”
“若不想我將事弄大,等秦修遠回來,你們應當好生勸勸他,別披著羊皮卻幹著惡狼才會做的事。”沈崇樓嗤聲說道,他向來不屑如此下三濫的手段。
書一直沒有吭聲,當沈崇樓近,男人那雙劍眉冷冽地向攏著,書的心開始忐忑起來。
“和我裝啞?”沈崇樓的手用力地拍在書肩膀上,“沒關係,如故小時候也喜歡和我裝啞,但你知道我如何對的嗎?”
書搖搖頭,沈崇樓笑了笑,道:“我買盡喜歡的東西,悄悄塞在的書袋子裏,每次都會驚喜地笑出聲來。”
“可那是我對最疼的人采用的方法,而你……算什麽?你裝傻裝啞,好生讓人惱火!”沈崇樓反問,下一刻,就將書一手摁在了柱子上。
Advertisement
“沈三,這裏是雲錦坊,不是江北由著你為所為。”書雖然心裏生出一怕意,但鼓足了勇氣,警告對方。
沈崇樓鋒眉一挑,一副恍然大悟的模樣,哦了一聲,道:“所以在你們看來南京是秦家的,以至於敢我小妹的主意?”
書閉眼,輕聲道:“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麽,沈三……”
“秦修遠果然會挑忠心的人,你這人就算送到監獄嚴刑拷打,估計也吐不出半個字。”
聽不出沈崇樓究竟是誇他,還是損他,不過,當沈崇樓話畢,書就覺腰間有東西抵著,若是沒有猜錯,是沈崇樓腰間的槍。
時間如指間沙,大廳越來越靜謐,反倒讓人陷恐慌的境地。
沈崇樓並沒有掏槍,他隻是在書的耳邊留下一句冰冷的話:“我隻希你將話一字不地帶給秦修遠,若想要如故,除非從我上踏過去,不然,拿命來換。”
書依舊沉默,可眼底深的驚慌,還是出賣了他。
沈崇樓重重地鬆開書,朝瀚哲示意離開,書見他轉,立刻上前拿起桌上的檔案袋拆開,見東西是真的,立刻就要撕毀。
“你想撕就撕,不用猶豫,我那裏還有許多份,你手上的那份不過是我讓人連夜抄出來的副本。”
沈崇樓的聲音傳來,帶著幾分嘲弄,書聞聲朝前麵去,沈崇樓反頭對他搖著頭,角勾起,是嘲諷的弧度。
……
江北,大帥府,上頭坐著的兩人,邊都擺放著拐杖。
不同地是拐杖的質地,以及上頭刻的名字,左邊那拐杖刻著沈昭年,右邊的則是秦修遠。
Advertisement
此時,沈昭年一臉不悅,黑沉著問秦修遠:“你突然跑到江北來,什麽意思?”
“沈大帥,我想,有些賬,我們是時候好好算一算了。”秦修遠說著,之前溫潤如玉的臉,掛上了冷漠的表。
沈昭年一頭霧水,若秦修遠是和他談南北商業上的分歧,絕對不會是這樣的姿態,可他不曾和秦修遠有別的衝突。
既然要算賬,算什麽賬?
“江北可不比南京,你闖進我的地方,本就死路一條,還要和我算賬,難不是糊塗賬?”沈昭年話裏有話,拐著彎說秦修遠腦子有問題。
秦修遠笑而不語,卻在沈昭年站起來的那一刻,反手將沈昭年在了椅子上。
兩個人的腳都不方便,沈昭年雖是征戰沙場多年的人,沒料到秦修遠的手勁這麽大。
“嗯……你說的沒錯,確實是糊塗賬。”秦修遠雙眼一片猩紅,怒聲怒地瞪著沈昭年,“你可知曉,我母親是誰?”
沈昭年雖然年事已高,終究底子在,最後還是推開了秦修遠。
高的怒聲在辦公室裏響起:“你母親是誰,我怎麽知道,何況和我有什麽幹係,我看你活膩了才會沒事找事!”
隨著話音一落,沈昭年到上方的槍就抵在了秦修遠的腦門上。
隻要秦修遠再多刺激沈昭年一下,槍子兒就不認人了。
“十五年前你去過一次南京的秦淮樓,亥時三刻,你對一個靈韻的子做了什麽?”秦修遠近乎咬牙切齒地問沈昭年。
翻天倒海的回憶朝沈昭年湧來,那晚發生的事,是他人生抹不去的汙點。
Advertisement
秦修遠眉眼中有輕嘲的神態,問:“記不起來?需不需要我提醒你?”
沈昭年沉默,他都記得,而且,永遠也不可能忘卻。
對著秦修遠的槍,從沈昭年的掌心鬆落,掉在地上。
“……是你母親?”沈昭年用著抖的嗓音問著秦修遠。
秦修遠並沒有回答,而是一掌掐在了沈昭年的頸脖上,沈昭年明明能做出最快的反應抵擋秦修遠襲來的手,可沈昭年眼皮都未眨一下。
“不然,我為何要與你算賬?”憤恨的語氣,甚至恨不得沈昭年立即去死的眼神,都來自秦修遠。
“是我對不起,那晚,是生了誤會,我以為是秦淮樓陪酒的風塵子,誰知道是……”沈昭年說到這裏,再也沒有說下去的機會。
秦修遠聽到‘風塵子’四個字,已經怒不可支,五指收攏,就要斷送沈昭年的命。
沈昭年艱難地呼吸著,他的手緩緩抬起,卻不是為了將秦修遠的手弄開,而是有話對秦修遠說。
秦修遠下意識地鬆了鬆五指,依舊未將手撤離,隻聽沈昭年道:“吸了大煙,腦子很不清醒,自己跑到我房間,我才誤會是……”
“我是喜歡麗的子,可我也不會奪別人的妻。”說到這裏,沈昭年沒有再說下去。
該解釋的,他都解釋了,沒有解釋的,是因為當年做過的錯事的的確確也存在過。
秦修遠的臉上,終於有了一容。
有一點,沈昭年確實沒騙他,他的母親大煙。
他還記得,母親喜歡躺在床上吸大煙,那時,他年歲尚小,隻知道每次去母親房間總是煙霧繚繞,並不知曉那是不能,而了便會上癮的害人東西。
Advertisement
即便母親喜好大煙,可也知道大煙不好,也好麵子,很想擺這樣的生活,卻像是著了魔似的離不開那鬼東西。
當然那是他長大後看到母親留下的信,才明白母親當初吸大煙的心。
事總有敗的一天,被父親發現後,父親決意將母親趕出秦家,並且對外聲稱他娘親病故。
他還記得,母親走的時候,不曾留過他和安容,卻死都要帶走燒片的煙槍。
秦修遠一直以為母親不在意他和小妹,可有一天,母親跑回來,對他和小妹說:“你願跟著你爹還是願意跟著娘離開南京,若跟著我,我帶你們去大上海,我會想辦法養你們。”
他很猶豫,還未來得及給母親答案,可他也從未想過,那將是母親見他的最後一麵。
後來,母親被來南京逍遙的沈昭年糟蹋了,就在秦淮樓。
除夕的頭一晚,父親得到了小道消息,秦淮樓一個靈韻的子不了別人的辱沒,上吊自殺了。
而靈韻,就是母親趕出秦家之後,換的小名。
父親幾乎一夜白了頭,秦修遠至今想,若母親不大煙,父親還是很母親的。
除夕夜父親才抱著他在懷中,含淚道:“修遠啊,以後你就你大娘為母親,你的母親這次真死了。”
自此,秦修遠就希自己快些長大,如此一來,他就有能力調查究竟是哪個王八羔子了他母親。
然而,沈昭年的保工作做得如此,秦修遠想,若不是他找到當年送茶水的小二,一輩子不可能知道那人是誰。
“沈昭年,你知不知道,我無時無刻不等著這樣的機會親手要了你的命。”秦修遠吐出冰冷的一句話。
沈昭年的眼神黯然,他隻是輕聲回應了一句:“外頭都是我的人,隻要我喊一聲,他們都會進來,你覺得你能要了我的命?”
秦修遠吃力地彎了彎腰,將地上的槍撿起,對準了沈昭年,冷言道:“那就試試,是他們進來的快,還是槍快。”
“要什麽,你說吧。”忽地,沈昭年如此說,且臉上帶著淡薄的笑。
秦修遠雙眉微攏,沈昭年這個時候竟然還笑得出來,隻聽沈昭年道:“你若真想要我命,早就手了,不會和我談這麽久,我想,比起直接要我命,你更想看著我痛苦。”
“我有一種預,你想從我這裏得到某樣東西,不過也有可能我的預錯了,畢竟沒有東西能夠讓我生出痛。”沈昭年大風大浪見多了,依舊冷靜地分析道。
沈昭年破了秦修遠的心思,秦修遠冷笑著,將槍扔得遠遠的:“我以為打仗的人,都是蠢腦袋。”
他徹底放開沈昭年,坐回了原位:“我要的不是東西,是人,你的義沈如故。”
猜你喜歡
-
完結199 章

惹不起的趙律師
遭遇家暴,我從手術室裡出來,拿到了他給的名片。 從此,我聽到最多的話就是: “記住,你是有律師的人。”
51.2萬字8 27141 -
完結548 章

沈先生大腿我抱定了
在小說的莽荒時代,她,喬家的大小姐,重生了。 上一世掩蓋鋒芒,不求進取,只想戀愛腦的她死於非命,未婚夫和她的好閨蜜攪合在了一起,遠在國外的爸媽給自己填了個弟弟她都一點兒不知情。 一場車禍,她,帶著腹中不知父親的孩子一同喪命,一切就像命中註定...... 對此,重生後的喬寶兒表示,這一世,她誰也不會相信! 左手一個銀鐲綠毛龜坐擁空間,右手......沈先生的大腿湊過來,喬寶兒傲氣叉腰,她就是不想抱,怎麼破? ......
99.3萬字8 28234 -
完結340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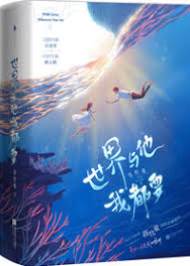
這世界與他,我都要
溫牧寒是葉颯小舅舅的朋友,讓她喊自己叔叔時,她死活不張嘴。 偶爾高興才軟軟地喊一聲哥哥。 聽到這個稱呼,溫牧寒眉梢輕挑透着一絲似笑非笑:“你是不是想幫你舅舅佔我便宜啊?” 葉颯繃着一張小臉就是不說話。 直到許多年後,她單手托腮坐在男人旁邊,眼神直勾勾地望着他說:“其實,是我想佔你便宜。” ——只叫哥哥,是因爲她對他見色起意了。 聚會裏面有人好奇溫牧寒和葉颯的關係,他坐在吧檯邊上,手指間轉着盛着酒的玻璃杯,透着一股兒冷淡慵懶 的勁兒:“能有什麼關係,她啊,小孩一個。” 誰知過了會兒外面泳池傳來落水聲。 溫牧寒跳進去撈人的時候,本來佯裝抽筋的小姑娘一下子攀住他。 小姑娘身體緊貼着他的胸膛,等兩人從水裏出來的時候,葉颯貼着他耳邊,輕輕吹氣:“哥哥,我還是小孩嗎?” 溫牧寒:“……” _ 許久之後,溫牧寒萬年不更新的朋友圈,突然放出一張打着點滴的照片。 溫牧寒:你們嫂子親自給我打的針。 衆人:?? 於是一向穩重的老男人親自在評論裏@葉颯,表示:介紹一下,這就是我媳婦。 這是一個一時拒絕一時爽,最後追妻火葬場的故事,連秀恩愛的方式都如此硬核的男人
52.7萬字8.18 7881 -
完結566 章

滿級熱戀:傅少嗜妻如命
【甜虐 偏執霸寵 追妻火葬場】“傅延聿,現在隻能救一個,你選誰?”懸崖之上,她和季晚晚被綁匪掛在崖邊。而她丈夫傅延聿,華城最尊貴的男人沒有絲毫猶豫:“放了晚晚。”聞姝笑了,她一顆棋子,如何能抵過他的白月光。笑著笑著,她決然躍入冰冷的大海……後來,沒人敢在傅延聿麵前再提“亡妻”……某日,傅延聿不顧場合將一女子堵在角落,如困獸般壓抑的看她:“阿姝,你回來了。”女人冷笑著推開:“傅少,你妻子早死了。”傅延聿隻是紅了眼,死死的拽住她……
98.2萬字8.18 4396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