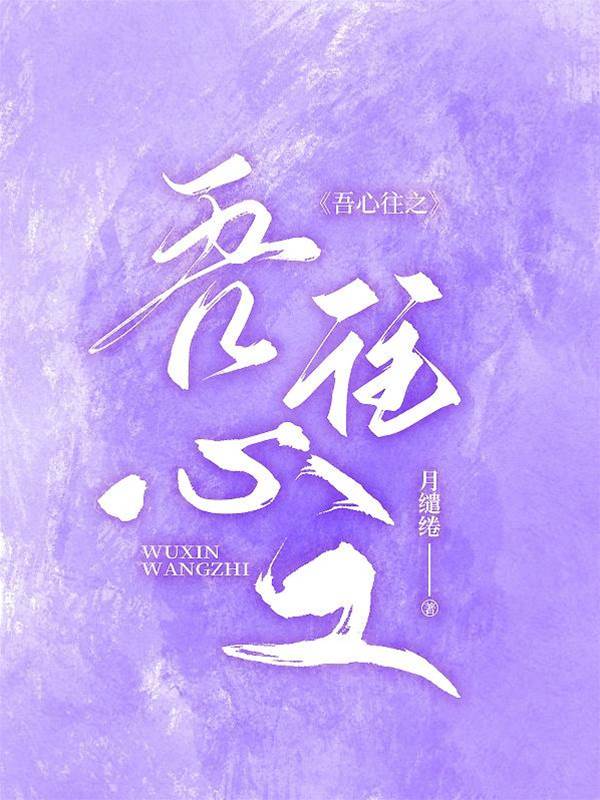《破繭》 第三十八章 高考日 我犯賤。
夏鳶蝶呼吸—室。
開機畫已經結束,手機屏幕上跳出幾十個紅的未接來電——全部來自於遊烈一個人。最後一通電話,在五分鐘前。
夏鳶蝶攥得指尖生白,深吸口氣,快速點進了聊天記錄裡。
那是一張背景昏暗的照片,夏鳶蝶一眼就能看穿,是在丁懷晴他們常去的那個廢棄活室。照片中央放著張椅子,穿新德校服的孩被綁在上面。
而丁嘉致就在孩上,半遮了孩的臉。
和夏鳶蝶那隻—模—樣的書包,躺在昏暗的椅子旁。
“———!"
只第—眼,夏鳶蝶就猜到了丁嘉致的意圖。也只這一眼,孩面上刷地褪盡。
夏鳶蝶想都沒想,著指尖點下游烈的手機號碼撥了回去。
在心裡默唸過一萬遍的“不要去”,最後一希卻碎在了話筒傳出的電子語音裡——
“對不起,您撥打的電話暫時無人接聽,請稍後.…..…”"
“對不起,您撥打的電話.…..…"
“對不起......."
第三次掛斷,夏鳶蝶生攥住了手指,阻止自己按下第四次。
眼角通紅,這是第一次被什麼事什麼人氣得渾戰慄發冷,而比起憤怒,更大的恐懼像是將城摧的雲,向心頭蔓延籠罩。
“哎呀,不接電話嗎?”男生笑了下,“新德中學離著遊烈的考點,怎麼也有二十幾分鐘的路程吧?你猜,遊烈去沒———”
“啪!“
—記耳很狠扇在了男生臉上,將他扇得偏過頭去。
男生臉上的表從震驚到不可置信再到沉,他剛轉要發狠,就忽覺手腕一,跟著便被前生扭著胳膊將手腕直接背擰在他後——
Advertisement
夏鳶蝶擡腳,朝對方膝蓋彎狠狠—踢。
阿——!”
男生慘著跪地。
夏鳶蝶鬆了手,僵著影,本能地往樓梯方向走了幾步。
“這位同學?”考場門,監考老師探出來,有些疑地看了眼後方向,“出什麼事了嗎?”
"..…沒事。”
夏鳶蝶聽見自己的聲音像是從另一個人的裡傳出來的。冰冷又僵。
“那你趕場吧,”老師看了眼腕錶,“英語考試有聽力的,開考前十五分鐘就止場了。”
興許是孩臉實在煞白,老師看著不放心地補了句:“你哪裡不舒服嗎?“
“老師,我可以打個電話嗎?“
老師猶豫了下:“行吧,你抓啊。最多一分鐘。”
夏鳶蝶用冰涼也發僵的手拿起手機,給趙叔叔撥了電話過去。
對面接得很快:“小蝶??你沒事嗎?那遊烈怎麼打電話給我說你出事了!我正在開車往新德那邊趕呢,你——”
“遊烈應該...過去了。”
老師站在門口,愣了下,擡頭。
那個全考場最淡定也最平靜的孩,就在這句話出口時,忽然眼淚就決堤一樣地淌了下來。
“對不起、對不起——“
孩蹲下去,將發冷的蜷,呼吸聲慄難已:“對不起叔叔我不能去.……..求你幫幫他.....對不起...…"”
站在教室外的老師繃住了肩背,出張的神。
手機對面的聲音聽不到,而手機這邊只有孩碎著聲的道歉。老師都準備聯繫突發狀況的負責老師了,卻聽見考前三十分鐘預備鈴打量——
蹲在地上的孩放下手機,掐斷了通話。
Advertisement
將它放進包裡,起,近乎暴地抹掉眼淚,然後孩紅著眼圈,拿起明文件袋,朝教室走去。
除了淚痕半乾的臉,沁紅的眼瞼,孩慢慢變得面無表。
最後—步到教室門前,哭啞的聲音將文件袋遞向老師:“請您,檢查。”
老師有些回不過神,匆忙檢查了遍:“真沒事嗎同學?“
孩搖頭,接過,轉走向自己的考桌。
像臺冷冰冰的機。
新德中學今天空一片。
雖然沒有被設爲考點,但高一高二學生仍舊放了假,學校裡爲還要回來收拾東西的高三生們開著校門,校園裡都空空的,不見人影。
除了育館後。
廢棄的活室,半扇鐵門斜倒在裡面的臺階下,另外半扇也被支離地歪在牆邊,搖搖墜。
而活室更是狼藉—片。
照片裡綁著孩的椅子倒在一旁,一條已經斷下來了,而照片裡那個配合地將全都藏在影裡的生,也早在踢斷了門衝進來的遊烈將站在幾個男生中央的丁嘉致踹倒在地時,尖著跑了出去。
這場架的最初,沒有這樣慘烈——
遊烈踢斷門門進來時額角青筋暴起,從面孔到脖頸都將冷白漲得通紅,猙獰模樣將幾個男生嚇得不輕。
直到那惡狠狠的—腳將丁嘉致直接踹倒在地,他們才反應過來將兩人隔開。
而在生尖聲離開後,遊烈在原地僵站了幾秒,似乎是要轉走的。
沒人打算攔。
他那個樣子太駭人,而且丁嘉致的目的已經達到——最後一場英語考試,遊烈怎麼也不可能趕得及了。
然而就在那一刻,被踹得險些背過氣去的丁嘉致從地上佝僂著爬起來,他捂著小腹,嘶聲笑了。
Advertisement
“等著吧遊烈。總有—天,老子讓那張照片真。”
"—”
走到臺階下的影驟然僵停。
後來...—發不可收拾。
男生們最初還是想幫丁嘉致的,也確實手了,直到他們發現遊烈彷彿徹底瘋了——他似乎不管不顧就真要在這裡打死丁嘉致。
幾個男生嚇得收了手,想給兩人拉開。
結果尖銳的警鈴聲就從遠的校園大道傳進來,男生們再顧不得,全都慌了神嚇得躥出活室去。
遊烈被兩個警察從丁嘉致的脖子上扣住手腕,摁在地上時,他左眼已經被額角淌下的鮮染得一片通紅,看不清視野。
比他更慘烈的丁嘉致長過氣,嘶聲笑著翻過,一邊笑一邊劇烈地咳嗽,他指著一片的活室外。
丁嘉致咧,含著滿的,痛快地笑起來:
“沒來——沒來哈哈!我讓人去告訴了,可夏鳶蝶沒來啊遊烈!本不在意你死活!——你是死是活,還沒—場考試重要呢哈哈哈咳咳...…"
笑到一半的聲音被撕心裂肺的咳嗽蓋過去。
“別!”
按著遊烈的兩個警察狠聲,吃力地住這個白襯衫都被染得紅的年,其中一個從後腰出冰冷的手銬。
“咔噠。”
手銬銬上。
遊烈跌闔下了染的長睫。
被警察從那個仄的房間裡往外帶,到臺階下,後猶傳回來丁嘉致嘶啞的聲音。“遊烈,我是輸給你了,可你也沒贏。”
他咳嗽著,嘶聲作笑,“那種人,就算你把心掏給,也本不會在意!“
“讓他閉!”跟隊的老警察皺著眉,“看看重不重,死不了就一起帶走!““是,隊長。”
Advertisement
老警察皺眉,看了眼被從面前帶過去的年。猩紅的將男生的左眼眼瞼染得駭人,失或者暴力讓他面出蒼白的冷。他闔著眼,額角,鼻樑,顴骨,凌冽張揚的五間全是污痕和,像是本該清貴卻頹敗在污泥裡的金。
人被塞進警車,老警察坐在他─側。
門合上,警笛尖銳地嘶鳴。
老警察皺著眉:“你就是遊烈?怎麼回事,門衛說是你讓他報的警?不是說有個孩被——被綁
架了嗎,人呢,人現在在哪兒?“
車裡久久死寂。
半晌,垂著頭的男生後仰,靠在警車後排的皮座裡。
從他額頭淌下,沒漆黑的髮際。
他像笑了。
或者只是薄冷而嘲弄地扯了下脣角。
“沒人,”遊烈聲音沙啞,“我兩的仇,跟其他人沒關係。”
夏鳶蝶從未想過,人生裡的第一次提前卷,會是在高考的英語考場。
和整場考試一樣,像個冷冰冰的、只備理思考能力的機人,確認過名字和考號,確認過答題卡填塗,然後拿起文件夾,起,到前排將考卷遞給老師,點頭,最後轉出了教室。
文件夾被塞進書包裡,用力過度,尖角在手指上劃了條口子。
鮮紅的—下子涌出來。
孩慢慢攥手指。
下—秒,拎起書包朝樓梯口跑去。
那也是夏鳶蝶人生裡最荒唐也瘋狂的一場,在那無比謹慎、每一步都走得小心翼翼的人生路上,這是第一次發了瘋似的,不管不顧地往前跑。
跑到呼吸裡全是腥氣,跑到衝出陌生的校門,跑到在一張張陌生而驚訝的面孔裡橫衝直撞。
“同學——哎!”
拎著話筒的不知道什麼人攔在面前,夏鳶蝶躲不及,兩人撞在一起,踉蹌地摔在地上。火辣辣的片刻就被麻木蓋了過去。
夏鳶蝶起,沒有看地上的人和做一團的人羣半眼,終於衝到了街邊,攔下第一輛出租車。
—路風景模糊得像在一個夢裡。
夏鳶蝶已經不記得,自己是怎樣回到別墅區,怎樣看見一臉愁容的趙阿姨驚慌地跑過來,在耳邊急切地擔心地敘說著什麼。
說了夏鳶蝶也聽不清。
那—理智用盡後,腦海裡此刻只有一個人的名字。“遊烈呢。”
孩從來溫吞的聲音像是困在沙漠幾日沒有進水的狀態:“阿姨,遊烈回來了嗎?“
“他人沒什麼大事….啊阿..濡生去警察局了....."
趙阿姨斷續的話音在耳旁迴盪。
到此刻,夏鳶蝶終於聽見了心跳的聲音。闔了闔眼。
“好。”
再不出一多餘的說話的力氣,用搖頭拒絕了趙阿姨的一切好意,夏鳶蝶慢慢朝樓梯走去。
後面一切仍是模糊的。
只記著自己在牀邊茫然地坐了很久,然後看見鏡子裡狼狽的,鬼一樣的自己。
於是慢慢撐著起,將校服去,換上—條長,遮住了膝蓋上糊糊的傷。然後下樓去。
wWW•t t k a n•C〇
就坐在客廳的沙發上,像只被拆了弦兒的木偶,捧著趙阿姨擔心地放在茶幾上的水杯,抿了幾口,就嗆了幾口。
這─等就等到天黑。
到某—刻,別墅玄關的門忽然打開——
沙發上的孩僵了下。
水杯險些手,—沒地,僵坐在最外面的離門口最近的沙發上,朝玄關扭頭。
遊烈回來了。
白襯衫黑長被浸,深淺不一,額上的傷做了清洗和理,卻更顯得那張臉冷白蒼寂。他低闔著眼,—傷地邁出了玄關。
沒換的黑皮鞋踩過地毯,遊烈進來,沒出—聲音。
夏鳶蝶不記得自己從什麼時候開始屏息,只是一語不發地著他,看他走近,覺得他應該會當不存在,應該會就那樣走過去。
但遊烈停下了。
沾著的外套被他隨手丟棄,男生冷戾地垂低了眼尾,漆眸像是沒有緒地掃過沙發上僵坐的。
倒是乾乾淨淨,還換了長。
除了頭髮紮了長馬尾,眼鏡沒戴,子漂亮,好像和第一次見到的孩沒有任何區別。
[就算你把心掏給,也本不會在意。]
遊烈垂眸,輕嗤了聲。
他慢慢蹲下。
“夏鳶蝶,”遊烈聲音啞得厲害,冰冷又沉戾,他卻笑著,也不在意脣角的傷泛青滲,“你就不能裝一下,關心我麼。”
孩脣瓣輕了下。
“遊烈,”夏鳶蝶輕聲,跌下眼瞼,“你先上樓休息吧,我們明天再說,好不好。”
“...行。”
遊烈啞聲笑了,他撐著膝,影僵了下才慢慢起。黑漆漆的墨染進他眸裡。
男生轉,冷峻漠然地走出去兩步,然後長停下。
像是一再抑不住的緒猙獰過他眼尾,撕開了那張冷冽寂然的外皮,他轉,到沙發前,拎起孩的胳膊,然後俯——
在趙阿姨的驚呼聲裡,遊烈將沙發上的扛在了肩上。他轉朝樓梯走去。
天暈地旋,都衝進腦袋裡了,夏鳶蝶眼前黑了下,失重讓差點暈過去。但到最後,自己都沒喊—聲。
樓梯臺階離好遠,地面越來越高,想著摔下去可能要住加護病房。
—樓轉平臺,平臺轉二樓。
二樓又往上。
夏鳶蝶心了下,聲音仍是安靜的:“遊烈。”
遊烈像沒有聽到,繼續上樓。
“你忘了,”夏鳶蝶合上了眼,“你說過的,外人,不能上三樓。”
“是。”
遊烈自嘲地嗤了聲笑,冰冷沁骨——
“我犯賤。”
猜你喜歡
-
完結12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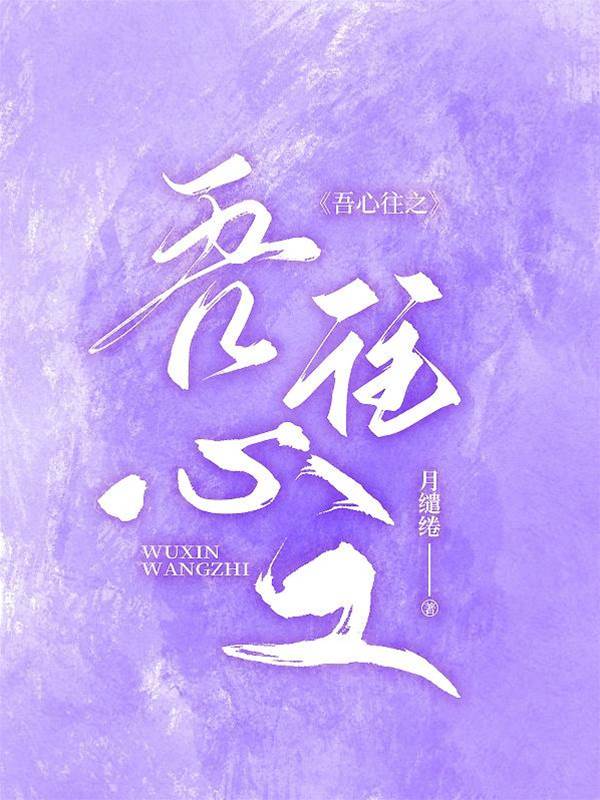
吾心往之
【久別重逢,破鏡重圓,嘴硬心軟,有甜有虐he 】【獨立敏感的高冷美人??死心塌地口是心非的男人】【廣告公司創意總監??京圈權貴、商界霸總】——————阮想再次見到周景維的時候,那一天剛好是燕城的初雪。她抱著朋友的孩子與他在電梯間不期而遇。周景維見她懷裏的混血女孩兒和旁邊的外國男人,一言不發。走出電梯關閉的那一刻,她聽見他對旁邊的人說,眼不見為淨。——————春節,倫敦。阮想抱著兒子阮叢安看中華姓氏展。兒子指著她身後懸掛的字問:媽媽,那是什麼字?阮想沉默後回答:周,周而複始的周。
22.3萬字8 33508 -
完結141 章

錯嫁瘋批老公後,我直接帶球死遁
夏鳶穿進一本瘋批文,成爲了下場悽慘的惡毒女配,只有抱緊瘋批男主的大腿才能苟活。 系統:“攻略瘋批男主,你就能回家!”夏鳶笑容乖巧:“我會讓瘋批男主成爲世界上最幸福的人!”瘋批男主手焊金絲籠。 夏鳶:“金閃閃的好漂亮,你昨天給我買的小鈴鐺可以掛上去嗎?”她鑽進去一秒入睡,愛得不行。 瘋批男主默默拆掉金絲籠,佔有慾十足抱着她哄睡。瘋批男主送給她安裝了追蹤器的手錶。 夏鳶:“你怎麼知道我缺手錶?”她二十四小時戴在手上,瘋批男主偷偷扔掉了手錶,罵它不要碧蓮。 當夏鳶拿下瘋批男主後,系統發出尖銳的爆鳴聲:“宿主,你攻略錯人了!”夏鳶摸了摸鼓起的孕肚:要不……帶球死遁?
26萬字8.18 4076 -
完結166 章

肆無忌憚
當紅小花虞酒出道后順風順水,嬌艷張揚。 新電影宣傳,她上了一檔節目。 當主持人詢問成名曲時,虞酒第一次公開承認:“寫給初戀的。” 全網驚爆,開始追蹤。 初戀是誰成了娛樂圈里的謎。 . A大最年輕的物理教授蘇頌舉辦了一場公開課,官方全程直播,教室內座無虛席。 下課后人流過多,有同學不小心撞到身旁女孩,口罩假發掉了一地。 虞酒精致的臉出現在鏡頭中。 全網觀眾:?? 你一個女明星去聽物理教授的公開課? 熱議許久,當事人終于發了微博。 【虞酒:我愛學習,學習愛我。】 言辭認真,網友們姑且信了。 沒多久,A大論壇熱帖:【你們知道蘇教授是虞酒那個傳說中的初戀嗎?】 主樓附有一張熱吻舊圖。 當年將蘇頌按倒在課桌上的虞酒,還穿著高中校服。
23.8萬字8.18 4566 -
連載41 章

斷絕關系後,五個姐姐後悔了
對於唐果兒,林子海可以忍。 但是對於林晨,林子海完全忍不了。 “林晨,你少在這裡逼逼賴賴!” “你偷了就是偷了!” “別扯開話題!” 林子海沒好氣道。 林晨無語的搖了搖頭,然後道: “哎,不是,林子海!” “你怎麼就那麼喜歡玩這種低端的把戲?” 從林子海先前說的話,林晨已經肯定自己書桌裡的東西,到底是怎麼回事了。 想不明白,林子海成年後一個陰險奸詐,做事滴水不漏的人,怎麼高中時期這麼蠢? 這種誣陷的事情,做過一次了,居然還來第二次。 又不是所有人,都像林家人那樣寵著他,那樣無條件的相信他。 “誣陷這種小孩子的把戲,你都失敗過一次了,現在還來第二次。” “你是不是覺得,你沒進去,心裡很是不甘心啊?” 林晨說完,抱著胳膊,盯著林子海。 周圍看戲的同學們聞言,又將目光看向了林子海。 一群吃瓜的同學,直接小聲的議論了起來。 …… “聽林晨的意思,這裡面還有別的隱情?” “就算林晨不說,我都已經想到是怎麼一個事兒了?” “哥!哥!哥!你快說說!” “叫爸爸!” ...
7.1萬字8.18 1254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