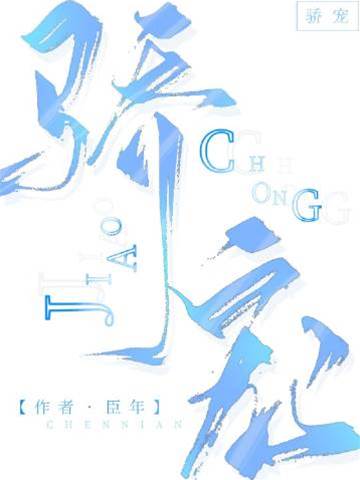《太陽落日前》 1、01
《太落日前》
文/時祈
新春,首都機場。
下午五點五十分,陳燃站在隊伍的后方等待安檢。遮擋的嚴實,黑的短款羽絨服,黑長,黑馬丁靴,黑的墨鏡,黑的口罩,渾上下生人勿近的氣息,一言不發,垂眸,盯著手機的屏幕。
陳燃在看和林至白的聊天記錄。
林至白是陳燃的初,兩人在大四相識。那時每個人都忙,陳燃也是,忙著找一份合適的工作,像只沒了頭的蒼蠅,在春招的會場跑來又跑去,投出簡歷比小山都高。
陳燃還差最后兩份簡歷投完,一邊埋頭回復朋友的消息,一邊趕到下一個人流堆,消息還沒發出去,陳燃就撞上了林至白,那是一很淡的沉香味。
陳燃抬起頭,愣了下。
對方和在場的人都不同,他不慌也不忙,沒有校園里的魯莽,也沒有社會上的疲憊。
他自在又從容,外邊是件淺棕的風,里邊是合的白襯,鼻梁很,架了一副金邊的眼鏡,很輕地沖笑了笑,那雙眼睛會微微向下彎,無意間了幾分深。
他把扶正,說了一句小心點兒。
春招現場的人多,陳燃連句謝的話都沒來得及說,兩個人就被人流沖散。
當然,陳燃沒想過兩個人會再見,直到三天后,接到了林氏的面試邀請,面試正是林至白。
從陌生人到上下級,從上下級到悉的朋友,從悉的朋友到。陳燃聽過不小說里的節,無一例外,俗氣非常,英俊又多金的男主角在人群里和主角相遇,他們一見鐘,他們非彼此不可,從來不相信,但是遇到林至白,陳燃忽然就信了,世界上大概真的有這樣的人,他們深又專一,溫又。
Advertisement
陳燃的生理期不規律,又貪涼,每次都疼一團,林至白總是耐心,他會哈著氣,會把手熱,一點兒一點兒慢慢給暖了小肚子。
陳燃挑食,羊不吃,胡蘿卜不吃,苦瓜不吃,芹菜不吃,茄子不吃,一種菜炸著不吃但炒著可能會吃,林至白每次都能記得一清二楚,在點菜的時
候規避掉全部討厭的可能。
陳燃不記得路,林至白每次都標記好方向,幫找到,送到達,什麼事都能想到。
陳燃每次聊起什麼,林至白似乎也總是能接上的話,他的未來和計劃里似乎總是有,會計劃他們如何去見對方的父母,會計劃他們的婚禮是什麼樣,會計劃有幾個孩子,會計劃房子如何裝修。
兩年,這兩年里,他們是朋友圈里公認的模范,林至白家世優越,林氏未來的接班人,有教養,有禮貌,他沒有任何缺點,找不出一點兒問題,每個人都和說林至白,他們會結婚,會生子,會有一個好的未來。
可誰能想到陳燃有一天會被小三。
這樣的一個人,以至于陳燃從沒想過會是一個調劑品。
林至白像是用全部的力來,他把所有的時間都留給,怎麼可能是一個調劑品?
陳燃想不明白,也想不通。
可這就是事實。
這麼多年,陳燃從來沒有翻過林至白的手機,知道林至白的手機里全是重要的信息,也相信林至白對的。
直到昨天,林至白去外地出差,陳燃無意間瞥到了他聊天的對話框。他收回的速度太快,但人的第六總是神奇,在林至白洗澡的時候,陳燃翻了他的手機。
這也是陳燃第一次知道林至白有個未婚妻。
Advertisement
林至白給的備注簡單又親昵,只是疊字,冉冉。
林至白的聊天背景是他們在一起拍攝的訂婚照,照片里,明冉明眸皓齒,朱紅的,萬般風流轉眉眼。林至白的手是那樣的好看,總是著陳燃的臉,如今卻輕輕攬在另一個人的腰側。他垂眸,眼底不變,仍是深,不止是看才會有的深。
瀏覽了兩個人的聊天記錄,大概清楚明冉和他兩個人是青梅竹馬,兩小無猜,他們家世相當,興趣相當,要不是的份,陳燃不得把全部甜又可的詞都放到兩個人上。
陳燃記得林至白喜歡芭蕾,對此完全不通,一日又一日的研究,惡補了多知識,從來沒想過還有一個人,明冉,在國外的芭蕾舞團出演,是個出的芭蕾舞者。
還有那麼一次,睡夢
里林至白難得對了一次燃燃,一直以為是在喊的名字,想到在睡夢中林至白也在掛記自己而,等林至白睡醒的時候,就這麼抱著枕頭笑呀笑,還跟他打趣,說有些笨蛋連睡覺都忘不掉。當時林至白有沒有回答?好像是沒有的。他只是有一瞬間的失神,然后下床給倒了杯水,兩個人的話題也就此打住。
愚蠢。
真是愚蠢到了極致。
總以為林至白,可太高估林至白的,或許林至白從來都沒有過。
到底是還在過節,機場的人并不算多,尤其還往外邊兒飛,排隊的人就那麼幾個,氣溫不高,陳然掉的羽絨服,把東西放至進了小框,安檢,尋找登機口。
手機在震,陳燃退出了和林至白的聊天界面,轉而是高中時期的好友,胡涂。
胡涂不喜歡打文字,發來的全部都是語音,一串又接了一串。
Advertisement
【難得胡涂:「語音1」】
【難得胡涂:「語音2」】
【難得胡涂:「語音3」】
陳燃點開語音,先前跟胡涂說了要去杉磯,要親眼看到林至白和明冉,不信林至白真的會這樣對,死不了這份心。
胡涂是個湖南的湘妹子,一口塑料普通話,即使在外多年也毫無改變:“早就說林至白不是什麼好人,現實里哪兒有那麼注重細節的男人?我都跟你說過,這種男人,不是gay,就是渣男。”
“他們有錢人是不是都這樣?真服了,他未婚妻也不管管?還是各玩各的。那麼多好男人呢,誰還真上趕子要他,他是比別人多哪?強哪?”
“就我們學校的譚驍比他強一萬萬萬萬倍,我說的是萬萬萬萬倍。”胡涂所在是所世界頂級的院校,學費高昂,培養了數不盡的商業名流,能上得起學,非富即貴,不知道是什麼原因,胡涂沒繼續說完,“就是可惜.......”
陳燃一邊聽胡涂的語音,一邊走到到貴賓廳等候值機,當然知道,這世界上的好男人不止林至白一個人,可畢竟兩年的,眼淚還是沒忍住,滾了下來。
林至白和來過這里。
那會兒是他們一周年的紀念日,林至白問要什麼獎勵,陳燃說想跟林至白一起去一
次旅行,哪兒都無所謂。林至白訂好了一切,陳燃什麼也沒想,什麼也沒問,就這麼提了個行李箱,傻乎乎地跟上了林至白,毫不怕林至白把弄丟又或者拐賣。
林至白還會抬手,無奈地沖笑:“傻瓜,你就不問問我去哪兒?也不怕我做點兒壞事?”
還會說:“那我也心甘愿呀。”
心甘愿?陳燃現在只覺得可笑,真是為沖昏了頭腦。
Advertisement
陳燃低手,了下羽絨服的口袋,空空如也。
上有帶紙巾的習慣,一般都是綠茶味的心相印。先前看聊天記錄的時候,口袋里的紙巾就無意識地用掉了一包,這會兒確實沒有多余的,還沒起,一包新的紙巾就出現在了眼前。
是最常用的牌子。
綠茶味的,心相印。
陳然順著紙巾包裝,看了過去。
室的線暗淡,偏偏在抬起頭的這一刻,烏云撥散,橙黃的過玻璃打了過來,視線也在瞬間鮮亮。
對方是個年輕的男人,年齡大約與相同。線落在他的黑的夾克暈出溫熱的波。他上裹得嚴實,頭發凌,別有一種不羈的。他的眸子很深,眼尾上挑,廓鋒利,單耳戴了一顆極品的藍寶石所制的耳釘,明亮而閃爍。
他又把紙巾往前遞了遞,挑眉,似乎不理解:“不要嗎?”
陳燃抿著,看著他。他沒有彎腰,姿勢隨意,看起來只是隨口來講一句話,并不是真的有什麼預謀。
現在確實需要一包紙巾,陳燃沒理由拒絕,只是還沒等接過,紙巾就被扔到了懷里。
紙巾沒拆封,嶄新的,陳燃愣了下,抓住包裝的外沿,大約是被男人放置在手心里,還有些許溫熱,與機場的溫度不同,形冷暖的差異。
他的作太突然,陳燃還沒反應過來,一句謝謝都沒說出口,對方已經坐在了對面的沙發扶手上,而后一歪,滾落地靠在了椅背,完全不在意到底會做出什麼樣的反應,他的眼睛也隨之閉住。
他更不會等講話,人就先一步開了口。
他說:“不客氣。”
猜你喜歡
-
完結96 章
再見及再愛
家道中落,林晞卻仍能幸運嫁入豪門。婚宴之上,昔日戀人顏司明成了她的“舅舅”。新婚之夜,新婚丈夫卻和別的女人在交頸纏綿。身份殊異,她想要離他越遠,他們卻糾纏得越來越近。“你愛他?”他笑,笑容冷厲,突然出手剝開她的浴巾,在她耳朵邊一字一句地說,“林晞,從來沒有人敢這樣欺辱我,你是第一個!”
17.2萬字8.18 20793 -
完結1965 章

盛寵名門佳妻
旁人大婚是進婚房,她和墨靖堯穿著婚服進的是棺材。空間太小,貼的太近,從此墨少習慣了懷裡多隻小寵物。寵物寵物,不寵那就是暴殄天物。於是,墨少決心把這個真理髮揮到極致。她上房,他幫她揭瓦。她說爹不疼媽不愛,他大手一揮,那就換個新爹媽。她說哥哥姐姐欺負她,他直接踩在腳下,我老婆是你們祖宗。小祖宗天天往外跑,墨少滿身飄酸:“我家小妻子膚白貌美,給我盯緊了。”眾吃瓜跟班:“少爺,你眼瞎嗎……”
284.1萬字8 29639 -
完結43 章

我的愛生生不息
雲知新想這輩子就算沒有白耀楠的愛,有一個酷似他的孩子也好。也不枉自己愛了他二十年。來
4.3萬字8 13074 -
完結493 章

甜心玩火:誤惹霸情闊少爺
訂婚宴當天,她竟然被綁架了! 一場綁架,本以為能解除以商業共贏為前提的無愛聯姻,她卻不知自己惹了更大號人物。 他…… 那個綁架她的大BOSS,為什麼看起來那麼眼熟,不會是那晚不小心放縱的對象吧? 完了完了,真是他! 男人逼近,令她無所遁逃,“強上我,這筆賬你要怎麼算?”
90.4萬字8 37776 -
完結77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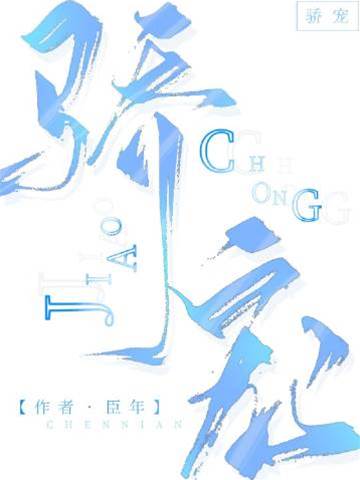
驕寵
作為國家博物館特聘書畫修復師,顧星檀在一次美術展中意外露臉而走紅網絡,她一襲紅裙入鏡,容顏明艷昳麗,慵懶回眸時,神仙美貌顛倒眾生。后來,有媒體采訪到這位神顏女神:擇偶標準是什麼?顧星檀回答:我喜歡桀驁不馴又野又冷小狼狗,最好有紋身,超酷。網…
31.3萬字8 4218 -
完結503 章

沈總別虐了,夫人和新歡約會上熱搜了
結婚三週年紀念日那天,沈澤撂下狠話。 “像你這樣惡毒的女人,根本不配成爲沈太太。” 轉頭就去照顧懷孕的白月光。 三年也沒能暖熱他的心,葉莯心灰意冷,扔下一紙離婚協議,瀟灑離開。 沈澤看着自己的前妻一條又一條的上熱搜,終於忍不住找到她。 將她抵在牆邊,低聲詢問,“當初救我的人是你?” 葉莯嫌棄地推開男人,“沈總讓讓,你擋着我約會了。”
36.8萬字8 3364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