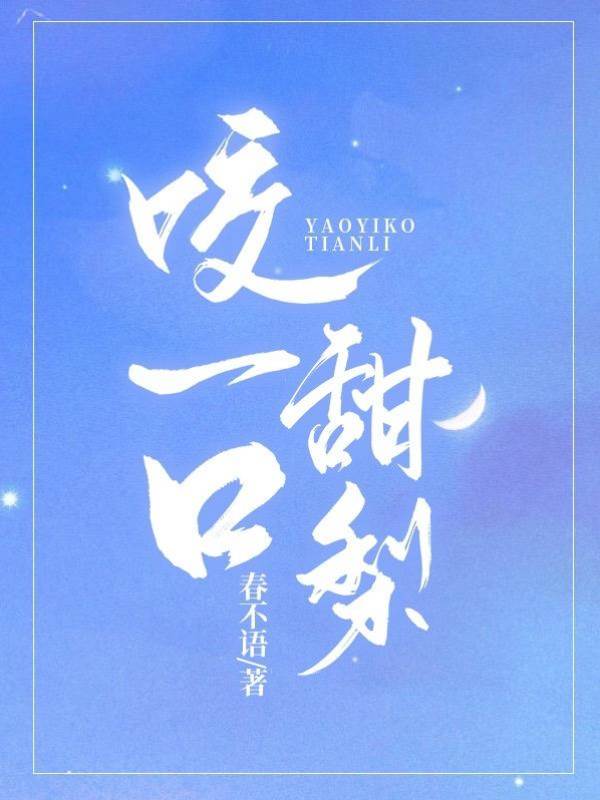《大院嬌妻純又欲,高冷硬漢破戒了》 第17章 我要親你了啊
“我再問你最后一遍,到底幫不幫我開介紹信!”
“不幫。”
周時凜的態度也很堅決。
他比溫淺大五歲,有責任為的安全負責。
“你需要錢我給你,單獨出門不行。”
兩人僵持不下。
溫淺盯著面前的男人,眼神里的熱度看得周時凜全都發起了熱,他有些尷尬地往旁邊挪了挪,凸起的結不自覺。
“吃飯吧。”
“不吃。”
溫淺忽然傾湊近,狡黠地勾了勾,嗓音甜膩“你不同意我就要親你了,親到你同意為止。”
人設已經不重要了。
反正在周時凜眼里,就是個一直饞他子的。
這話一出口,一向泰山崩于面前而不改的周隊長嗖得一下彈跳起來,英俊的面孔染上一紅暈,幸好黑,看不太出來。
那也夠尷尬的。
“孩子要自重!”
“我知道啊,可你是我男人啊,我親自己男人怎麼就不自重了,還是,你想讓我去親別的男人?”
周時凜“……”
他就知道,自己從來不是的對手。
最后,在溫淺的磨泡下,周時凜終于松了口,去指導員那里開了介紹信,下午就帶著溫淺去縣城火車站買火車票。
火車站人擁。
周時凜材高大,一路上虛攬著溫淺將護在懷里,兩人得很近,可誰都沒有說話,一種尷尬中帶著一別樣的甜在空氣中蔓延。
Advertisement
想到來時周時凜塞給自己的三百塊錢,溫淺心里一暖。
他說去一趟羊城不容易。
手里有錢心里就不慌,還說讓多進些貨,可也有自己的原則,那三百塊錢最后還是悄悄留在了家里。
火車開。
溫淺從窗口探出頭,朝著周時凜揮了揮手。
“等我回來。”
這一刻,穿越人。
周時凜的眼里只有溫淺那張笑靨如花的俏臉。
他角帶笑“注意安全,早點回來。”
夜幕降臨。
> 周時凜是在睡覺的時候才發現在枕頭底下的三百塊錢,看著那厚厚一沓大團結,一時間心有些復雜,這次,溫淺是真的從骨子里開始改變了。
真的變了。
而他似乎也變了,開始忍不住擔心,擔心獨自一人出遠門,有沒有害怕,有沒有吃飯……
同一時間。
溫淺正在吃飯。
吃的是周時凜下午在國營飯店專門買的豬大蔥餡包子,白白胖胖的大包子涼了也好吃,饞得隔壁小孩眼著,口水流了一地。
“媽,我要吃包子。”
中年人用袖子胡給兒子了口水,討好地看著溫淺笑“大妹子,你看你大侄子饞啥樣了,要不你給孩子嘗一口?”
溫淺“?”
啥玩意?天上掉下個大侄子?
往對面的母子倆上瞅一眼,面無表的拒絕“沒了,想吃包子去餐廳買,那里邊的包子還不要糧票。”
Advertisement
中年人笑得不自然。
“孩子吃不了多。”
還想再說幾句,溫淺已經閉上了眼睛,雙手環在前,周散發著生人勿進的氣息,人只能訕訕地閉了,順便往哭鬧不止的孩子屁上拍了一掌。
“什麼人啊,一點都不知道尊老。”
一晚上相安無事的過去。
第二天。
溫淺拿著巾去洗漱,一走,中年人左右看了看,見對面的戴眼鏡男人還在睡覺,猶豫了一秒,輕手輕腳拉開了溫淺放在座位下的手提包。
洗漱回來的溫淺沒發現異樣。
車廂里已經熱鬧起來,有說話的,有活的,也有吃早飯的,閉的空間里混合了無數種氣味,熏得人腦仁嗡嗡響。
溫淺也不嫌難聞。
從手提包里照例拿出包子,還有周時凜特意給買的鹵牛,然后
就發現了不對勁的地方,包里的東西好像被翻過。
吃的在。
服也在。
錢隨攜帶著裝兜兜里了,只有一樣東西不見了——介紹信!
介紹信丟了就得流落街頭。
可誰會介紹信呢,這玩意既不當吃也不當喝,了也沒什麼用,重新將角角落落找了一遍,溫淺確定介紹信真的不見了。
介紹信沒長。
除非是有人故意為之。
溫淺思索了幾秒,意味深長的目落在了對面的中年人上。
Advertisement
人本就心虛,被這種犀利的目盯著就更虛了,厲荏嚷嚷道“你自己丟了東西可別想賴別人!”
“你怎麼就知道我丟東西了?”
一句話,溫淺就可以確定介紹信就是中年人走的,原因無他,因為自己沒有給兒子吃包子。
索也不著急了。
好整以暇地往后靠了靠,角噙著一抹了然的笑。
中年人有點慌。
剛才拿了介紹信還沒來得及銷毀,現在介紹信就在上,若是對方強勢搜的,那不就餡了?
想了想,立即站起來就走。
“別擋著我去廁所。”
溫淺直起腰,出一條攔在人腳下,臉上的笑容早已消失殆盡,也懶得兜圈子,直接開門見山道“我的介紹信是你的吧?還回來,不然你就拉在兜子里吧。”
這話說得中年人臉大變。
強撐著沒有怯,撒潑似的放聲喊冤“我聽不懂你在說啥,別以為你是城里人就可以欺負俺們農村人,俺要上廁所!”
人聲音尖銳。
簡單一句話就挑起了周圍乘客對溫淺的不滿。
“農村人咋啦,憑啥看不起農村人!”
“往上數三代,哪個不是農村人!”
“年紀輕輕欺負人,不是個好東西!”
一時間,群激。
中年人得
意洋洋,一個小丫頭,秧瓜子似的,也敢跟自己斗,利用群眾輿論噴死。
Advertisement
“讓開!”
“不讓!”
溫淺針鋒相對,一把揪住中年人的袖,扯著不讓離開,另一邊還不忘向周圍的人大聲解釋。
“我也是農村人,可我不干狗給農村人丟臉的事。”
“你因為一個包子懷恨在心了我的介紹信和一百塊錢!”
一百塊錢啊!
這話一出,人群嘩然。
“是不是弄錯了?”
“咋可能,若是沒有嫌疑,人家咋會揪著不放!”
“真給咱農村人丟臉!”
轉眼之間。
輿論一邊倒。
中年人慌了神,抖著嗓子大喊“我沒拿,不是我!”
話音剛落,車廂另一頭,戴眼鏡的男人領著乘警來了。
乘警一來。
人群瞬間安靜。
中年人更是看見救星一般,委屈地抹著淚。
“同志,我沒拿的介紹信和錢。”
“我一個農村人,孤一人帶著孩子去邊疆探親,一路上倒了好幾趟車,還要走幾十里山路,腳都磨破了,再苦再累俺都沒抱怨一個字,咋能干狗的下三濫事。”
這一番話說真意切。
不周圍的人唏噓不已,連乘警都容了。
“原來你是軍嫂啊。”
說罷,他轉頭看向溫淺。
“這位同志,你是不是搞錯了,軍嫂同志怎麼會做這種抹黑軍人家屬形象的事,要不你再好好找找?”
溫淺抿不語。
都想給中年人鼓掌了,奧斯卡欠一個小金人啊。
還軍嫂呢,真給軍嫂丟臉!
眼看著形勢對自己不利,溫淺眼睛一轉,學著人哭了起來,抹了把眼角并不存在的眼淚,慘兮兮道“我四找了都沒有,肯定是拿的,要是不把我的介紹信和一百塊錢還回來我就跳火車!”
猜你喜歡
-
連載223 章

總裁追婚記:嬌妻哪裏逃
三年前,初入職場的實習生徐揚青帶著全世界的光芒跌跌撞撞的闖進傅司白的世界。 “別動!再動把你從這兒扔下去!”從此威脅恐嚇是家常便飯。 消失三年,當徐揚青再次出現時,傅司白不顧一切的將她禁錮在身邊,再也不能失去她。 “敢碰我我傅司白的女人還想活著走出這道門?”從此眼裏隻有她一人。 “我沒關係啊,再說不是還有你在嘛~” “真乖,不愧是我的女人!”
29.6萬字8 5229 -
完結1939 章

替嫁后我被大佬纏上了
所有人都說,戰家大少爺是個死過三個老婆、還慘遭毀容的無能變態……喬希希看了一眼身旁長相極其俊美、馬甲一大籮筐的腹黑男人,“戰梟寒,你到底還有多少事瞞著我?”某男聞言,撲通一聲就跪在了搓衣板上,小聲嚶嚶,“老婆,跪到晚上可不可以進房?”
290萬字8.18 188912 -
完結105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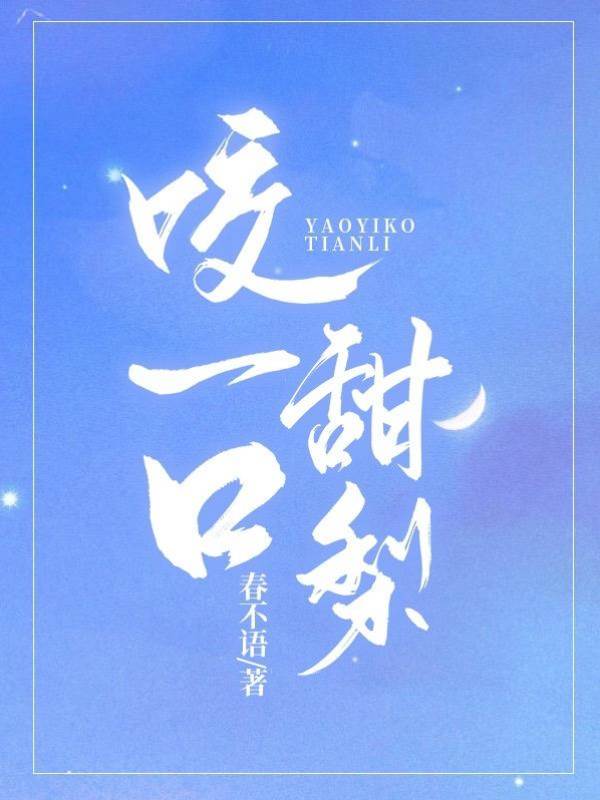
咬一口甜梨
白切黑清冷醫生vs小心機甜妹,很甜無虐。楚淵第一次見寄養在他家的阮梨是在醫院,弱柳扶風的病美人,豔若桃李,驚為天人。她眸裏水光盈盈,蔥蔥玉指拽著他的衣服,“楚醫生,我怕痛,你輕點。”第二次是在楚家桃園裏,桃花樹下,他被一隻貓抓傷了脖子。阮梨一身旗袍,黛眉朱唇,身段玲瓏,她手輕碰他的脖子,“哥哥,你疼不疼?”楚淵眉目深深沉,不見情緒,對她的接近毫無反應,近乎冷漠。-人人皆知,楚淵這位醫學界天才素有天仙之稱,他溫潤如玉,君子如蘭,多少女人愛慕,卻從不敢靠近,在他眼裏亦隻有病人,沒有女人。阮梨煞費苦心抱上大佬大腿,成為他的寶貝‘妹妹’。不料,男人溫潤如玉的皮囊下是一頭腹黑狡猾的狼。楚淵抱住她,薄唇碰到她的耳垂,似是撩撥:“想要談戀愛可以,但隻能跟我談。”-梨,多汁,清甜,嚐一口,食髓知味。既許一人以偏愛,願盡餘生之慷慨。
20.2萬字8 7736 -
連載256 章

全球通緝令,抓捕孕期逃跑小夫人
曾經顏琪以爲自己的幸福是從小一起長大的青梅竹馬。 後來才知道所有承諾都虛無縹緲。 放棄青梅竹馬,準備帶着孩子相依爲命的顏鹿被孩子親生父親找上門。 本想帶球逃跑,誰知飛機不能坐,高鐵站不能進? 本以爲的協議結婚,竟成了嬌寵一生。
45.2萬字8 4572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