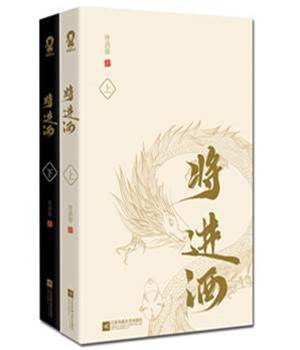《懸日》 第76章 N.蕉鹿之夢
蘇洄的皮散發著青草與朗姆酒的香氣,霧一樣籠罩寧一宵的。
他分開的兩挨著沙發邊緣,腳趾抵在長絨地毯上,著,栗得如同一枝雨后的冰島雪糕,擁抱的缺失令人不安,卻又帶來一種全新的驗。
如窗外的汐,涌起又落下。蘇洄吻他的樣子,令寧一宵想到多年前的那枚櫻桃梗,他曾經想象過那打結的全過程,如今一一復現在自己上。
“蘇洄,你是水做的嗎?”
寧一宵沒他,手放在一邊,看上去好像置事外。
蘇洄喜歡用問題回答問題,“弄臟你了?”
“到都是。”原本懶散靠在沙發上的寧一宵忽然靠過來,給了他一個有些暴的吻,幾乎像進他嚨深那樣肆無忌憚。
蘇洄跳躍的時不時割裂,這一刻忽然聯想到寧一宵開會時一本正經的模樣:戴著眼鏡,神冷漠認真,一張一合,全英文的討論,嚴謹專注,邏輯清晰,言語間穿著晦的數學公式與神經網絡模型。
和現在判若兩人。
除了自己,沒人見過這顆聰明的頭腦被念所擺布的樣子。
沒辦法,寧一宵便比往常時候更眷親吻,給蘇洄極大的滿足。
他們像是麥芽糖制的兩個人偶,接吻時會融化,千萬縷地相互粘連,越吻越黏,無論如何也分不開,注定要化作同一灘糖水。
接吻會模糊人的理智,喚醒潛意識。寧一宵幾乎是習慣地抬起手,在蘇洄往后躲時,想控住他的后腦。
“不可以犯規……”
蘇洄笑了出來,眼神卻有些失神,口齒也不太清晰,“干脆綁起來好了……”
可下一秒局勢便翻轉,他被進沙發里。
Advertisement
“寧一宵,你犯規了——”
“那又怎麼樣?你可以喊停。”寧一宵的手過蘇洄的臉,不輕不重地握住他的咽,“如果你想的話。”
蘇洄毫無反抗的力氣,雙目失神,恍惚間他想到自己被困在神病院的日子。
那時候能接到的書寥寥無幾,可他又亟需書籍,找得到的也大多與基督教有關,其中有一本是一位基督教徒的自傳,寫著圣徒與天使的夢中奇遇:
[……他的金箭一次次地刺我的心臟。當他拔.出金箭時,我的五臟六腑也跟著被拽住,徒留一個被上帝之點燃的我。疼痛如此強烈,讓我止不住.,但這痛楚又如此幸福,我企盼它可以永恒持續……]①
而那湊巧是蘇洄非常癡迷的雕塑《圣特雷莎的狂喜》的靈來源。
他從未踏足于羅馬圣瑪利亞教堂,未曾親眼見過那座雕塑群,但收藏了許多攝影作品,藏在臥室的屜里,雕塑里的每個微小的細節都記憶深刻,無論是微張的雙,還是蜷的腳趾。
此時此刻的他,靈魂離,仿佛為第三視角欣賞雕塑的觀客,視野里的自己,正如那位虔誠的修,癱迷離,被幻覺里紗幔一般的金芒所籠罩。
語言系統也徹底崩壞,含混的舌頭重復著寧一宵的名字和很多個“no”,但于事無補。
凌晨兩點,被抱到浴室的蘇洄在溫熱的水里逐漸恢復,如同一株水生植,一點點重新煥發生機。
他背靠在寧一宵懷中,酒完全醒了,只覺得渾酸乏,但又力旺盛。
“困嗎?”寧一宵低下頭,用他高的鼻梁有一搭沒一搭地蹭著蘇洄的肩窩,時不時很輕地吻兩下,弄得蘇洄很。
Advertisement
蘇洄邊躲邊搖頭,鼻腔中發出表示否定的單音節,笑著把泡沫弄到寧一宵臉上,“你想睡覺了嗎?”
寧一宵也搖頭,銜住他的耳垂,很快又松開。
蘇洄渾沒力氣,又怕,被他折騰得難,于是自己跑到浴缸另一頭靠著,腳踩在寧一宵口。
寧一宵便順勢低頭,吻了吻他沾著泡沫的足背。
“蘇洄。”
“嗯?”他懶懶回應。
“你很漂亮。”
蘇洄的反應略帶,仰起臉看天花板。明明經常被這樣夸贊,可聽到寧一宵說,還是止不住雀躍。
“我說真的。”
“……謝謝。”
寧一宵也笑了,力道不輕不重地著他的小。
本來一直仰著頭,蘇洄下忽地一沉,看向寧一宵,“可以去看海嗎?”
寧一宵抬了抬眉,“現在?”蘇洄點點頭,“我想去,你要不要和我一起?”
“過來親我一下。”
蘇洄立刻湊過去,在寧一宵上親了一口,出期待的表。
寧一宵信守承諾,起,嘩啦啦帶出許多水,像在浴缸上方下了場雨。
“躺著,我給你拿服。”
五分鐘后,寧一宵牽著蘇洄的手,直接沿著臺側面的白樓梯走到海灘邊。這里靜得只有海的聲音,深藍的夜空,黑的大海,被月照得雪白的沙灘,印在沙石上的一對影子。
“寧一宵。”
“嗯?”
“你還會討厭海嗎?像以前一樣。”
寧一宵靜了幾秒,“好像沒那麼討厭了。之前想到大海,全是不好的記憶,后來再想到海,已經不是那些會讓我做噩夢的回憶了。”
蘇洄的頭發被海風揚起,他挽到耳后,倒退著走路,對寧一宵笑,“會想到我嗎?”
Advertisement
寧一宵點頭,“嗯。有時候我坐在辦公室或者這棟房子里,也會看海,看著看著就會想起你,想象如果你在,應該會很喜歡這樣的風景。不過有時候,我也會想起我媽媽,偶爾甚至會看到走在沙灘上,穿了一白的子,很好看。”
蘇洄握住了他的手,只是溫地。
“會很憾吧。”
“嗯。”寧一宵覺自己的生命完全是憾組的,“其實我很怕想起,因為知道不會再出現了,我無論多努力,都不可能讓看到,讓也擁有。很長一段時間我都很排斥聽到別人提起我的父母,因為我比誰都希在這里。”
寧一宵說著,有些苦地笑了,“連你都沒有見到。”
蘇洄眼眶酸,“是啊,好可惜。”
“到最后,什麼都不剩,只留下一個箱,到現在我都沒有打開看過,是看到樣子差不多的箱子,就會很焦慮。”
這是寧一宵第一次坦誠地向蘇洄剖白,哪怕六年過去,他依舊沒辦法坦然接母親的死亡。
“但現在自由了。”蘇洄說,“就像告訴你的,只要撒進海里,就會無不在。看到海,就像是看到。”
寧一宵點頭。
他們坐在沙灘邊,著汐反復襲來,卷走沙礫與貝殼。
“我有時候也覺得很憾。”蘇洄握著一把沙子,聲音很輕,“明明我才26歲,可是卻好像活了好久好久,什麼都失去了,最開始是我的爸爸,我的健康,再后來就越來越多,像泥石流一樣,全部卷走了。”
蘇洄笑著看向寧一宵,“我還沒有跟你說過,就在我和你分手的幾天前,我叔叔因為神分裂自.殺了,去靈堂之前,我媽帶著我去了他家,想上我嬸嬸,我自己上了樓,結果發現也走了,只留了幾行字,說要去陪他。”
Advertisement
到現在為止,蘇洄也沒能忘記那時候的沖擊力。
“如果叔叔不是神病人,這一切都不會發生。”
兩人的沉默很短,寧一宵忽然開口,“你把我們代其中了。”
這是他所不知道的,也難以想象的。
蘇洄沒有否認,“很難不這樣做吧,我的病自殺率更高,何況那個時候,我確實也快撐不住了,躁狂都救不了我。我想盡了所有辦法,都不能扭轉他們的思想,無論如何也要讓我和你分開。”
“其實我最后悔的不是分手本,是我說分手的時候太含糊其辭了。”
蘇洄低下頭,困在神病院的小房間里,這最痛苦的一幕無數次在腦海重演,“我怕我說得太清楚,告訴你我那段時間經歷的一切,你會選擇堅決不分開,我知道你肯定會這樣,所以只能說,沒什麼理由。”
寧一宵的手上蘇洄的后背。
“我知道你討厭沒有理由的離開,我也知道,你可能真的會放棄一切帶我走,但是我很害怕這樣。”蘇洄聲音逐漸低下去,“對不起,都是因為我,我們之間錯過了六年。”
寧一宵抱住他,“我都明白,就算你什麼都不說,我也知道。”
蘇洄笑了,撥開頭發給他看自己脖子上已經愈合變淺的傷口,“你看,我去我外公的病房,搶了床頭柜上的水果刀抵在這里,結果劃破了也不知道,他們覺得我瘋了,都很怕我,但又本不打算聽我的話。”
寧一宵早就注意到那個細長的痕跡,只是他從來不提,很怕是蘇洄的傷心事,提起讓他介意或自卑。
聽到蘇洄自己說了,寧一宵也松了口氣,但更無法想象當時蘇洄有多痛。
“都過去了。”寧一宵攬過他的肩,吻了吻他的發頂。
“但那些日子都回不來了。”蘇洄說。
“回不來的才是人生。”
聽到這句話,蘇洄莫名很認同,點了點頭。
“我有一段時間特別恨他們,尤其是我外公,所有人,我以為他們都不要我了。”
蘇洄靠著對寧一宵的眷存活下來,也逐漸喪失了對家人的期盼。
“出來之后,我花了很長時間攢錢,因為記憶力衰退,他們的聯系方式我都忘得差不多了,只能找所有能求助的機構求助,他們說會幫我查,但最后告訴我,我的外公死了,我媽媽也去世了,外婆在外養老,但不知道位置。”
“而且我回不去。”蘇洄苦笑,“哪怕我白天給游客畫畫,晚上去餐廳打工,辛苦攢夠了機票,也回不去,因為我是神病人,需要有監護人的簽字才可以。”
多諷刺啊。
蘇洄笑著說,“我只能滯留在那里,也很想找你。”
其實蘇洄做出過很多努力,他曾經上網搜索到了寧一宵的論文,在最后一頁的作者信息里,看到了他的郵箱,可發出去的郵件似乎變了垃圾郵件,寧一宵本沒有看到。
“那你是怎麼找到外婆的?”寧一宵輕聲問。
“是懷特教授幫我找到的。”蘇洄垂著眼,睫輕微地,“他在加拿大參加學會議,我那時候會把自己做的一些東西拿去賣,其實一整天下來也沒幾個人會買,但他看到了,說要帶我去紐約學藝,我以為他是騙子。”
蘇洄笑了出來,“但是他給我看了他的作品,還帶著我去了那個學會議,讓我坐在后面聽,就像是一個從天而降的貴人,把我拉了出來。”
“我托他幫忙找外婆,其實真的很難,簡直就像大海撈針,但很巧,他有一個學生,已經畢業了,接了一個療養院的重建設計工作,所以那個人每天都會去療養院,還會和里面的老人聊天,記錄他們的需求。”
說到這里,他眼睛都亮了,“那天他來學校,巧我也在,他覺得我很眼,一開始我沒在意,他也走了,結果沒多久他竟然折返回來,告訴我,他沒看錯,我是他前不久見過的一位老人的孫子,他看過畫像。”
“我當時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就像做夢一樣。懷特教授立刻帶我去了那家療養院,在智利的一個小鎮,聽說整個鎮子都沒有多人,如果不是因為那個設計師,我可能一輩子也找不到外婆了。”
蘇洄想到和外婆見面的畫面,難以抑制地落了淚。
“那個時候就坐在療養院的長椅上,拿著一張掌大的畫像,盯著不。”
寧一宵替他抹了眼淚,“怎麼會有畫像?”
猜你喜歡
-
完結285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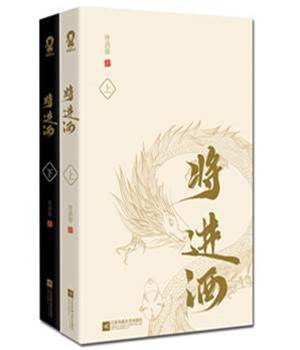
將進酒
浪蕩敗類紈绔攻vs睚眥必報美人受。惡狗對瘋犬。中博六州被拱手讓于外敵,沈澤川受押入京,淪為人人痛打的落水狗。蕭馳野聞著味來,不叫別人動手,自己將沈澤川一腳踹成了病秧子,誰知這病秧子回頭一口,咬得他鮮血淋漓。兩個人從此結下了大梁子,見面必撕咬。 “命運要我一生都守在這里,可這并非是我抉擇的那一條路。黃沙淹沒了我的手足,我不想再臣服于虛無的命。圣旨救不了我的兵,朝廷喂不飽我的馬,我不愿再為此赴命。我要翻過那座山,我要為自己一戰。” 1v1,HE,HE,HE。 【預警】 1、主cp蕭馳野x沈澤川,蕭攻沈受。 2、有條百合線,還是重要角色。 3、攻比之前幾本的哥哥們更加混賬。 4、作者是個沒文筆的大魔王,練節奏。 5、我給磕頭了各位大爺,看文案,看文案,【看清文案】。
89.8萬字8 7384 -
完結191 章

魔尊他念念不忘
1.池牧遙穿書後曾被迫和大反派奚淮一起關“小黑屋”,奚淮被鎖鏈禁錮著,靈力被封印。 他的處境極為尷尬,需要他修煉到築基期打開洞穴的禁制,二人方可獲救。 可……他是合歡宗男修啊啊啊啊啊啊!難不成拿大反派來修煉嗎? 看過這本書的讀者都知道,拿奚淮修煉的那個炮灰死得格外淒慘。 跑!破開禁制後他立即跑得無影無踪! 奚淮得救後突然著了魔,發了瘋的在三界尋找一個人。 不知道名字,不知道相貌,只知道那人是合歡宗的男弟子。 想來,找到那個拿他修煉了整整三年的小子,必定會殺之為快。 2.池牧遙入了修真界最沒有前途的御寵派,還是三系雜靈根。 眾人都說,他空有美貌,卻沒有實力,不配被稱之為三界第一美人。 3.仙界大會上,魔修們不請自來。 那個一身魔焰的青年立於人前,傳聞中他暴戾恣睢,跌宕不羈,現如今已經成了名門正派的噩夢。 此行,必有陰謀。 眾人防備之時,卻見奚淮突然靠近池牧遙,微瞇著雙眸看著他:“你的修為並沒有什麼精進,可是沒有我協助的緣故?” 池牧遙裝傻:“道友何出此言?” 4.修真界的瘋子奚淮突然安靜了,熱衷於在洞府裡“折磨”池牧遙。 夜裡池牧遙只能苦苦哀求:“不能再修煉了,我的修為快超過宗主了……” 5.本以為在被追殺,沒成想竟成了魔尊的白月光? 獨占欲極強偏執魔尊攻×前合歡宗唯一男弟子美人受 『“老婆老婆你在哪裡呀”』×『“跑呀跑呀我跑呀”』 又名《小魔尊找媳婦》《沒錯,我就是那個和反派關過小黑屋的砲灰》《本該是炮灰卻意外成為了魔尊的白月光》 【不正經仙俠】【年下】
43.1萬字8 15372 -
完結187 章

江湖遍地是奇葩
二十二歲,沈千淩拿到了人生第一個影帝! 然後就在他拿著獎杯熱淚盈眶之時,一塊天花闆轟然掉落,準確無誤砸中他的頭! 然後他就……穿越了! 秦少宇含笑:若是小淩願意,我追影宮隨時都能辦喜事! 沈千淩淚奔:老子特別不願意! 歡脫掉節操,這個一個沒有下限,奇葩遍地的江湖! HE,1V1,爆笑,神經病,_(:з」∠)_。 主角:沈千淩,秦少宇 編輯評價: 日月山莊的小少爺沈千淩從樹上摔下來,失憶了!不僅如此,清醒後簡直換了個人似的。事實上,如今的他是在拿到人生中第一個影帝時被砸中腦袋後,穿越而來。沈千淩很悲催的變成了個弱柳扶風的萬人迷小少爺,更悲催的發現這個世界好奇葩,爹爹娘親乃至哥哥們都贊同自己嫁給一個男人!更更悲催的是,那個男人竟厚著臉皮騙沈千淩說:你懷了我的孩子…… 作者以一貫歡脫的風格,爲我們講述了一個滿世界都是影帝的故事!已是影帝沈千淩扮穿越而來扮無辜,厚臉皮的未婚夫秦少宇裝深情,愛兒心切的娘親說風便是雨……情節有趣,惹人爆笑不已。本文沒有傳統江湖文的血雨腥風,但作者仍有心的
59.1萬字8.18 12597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