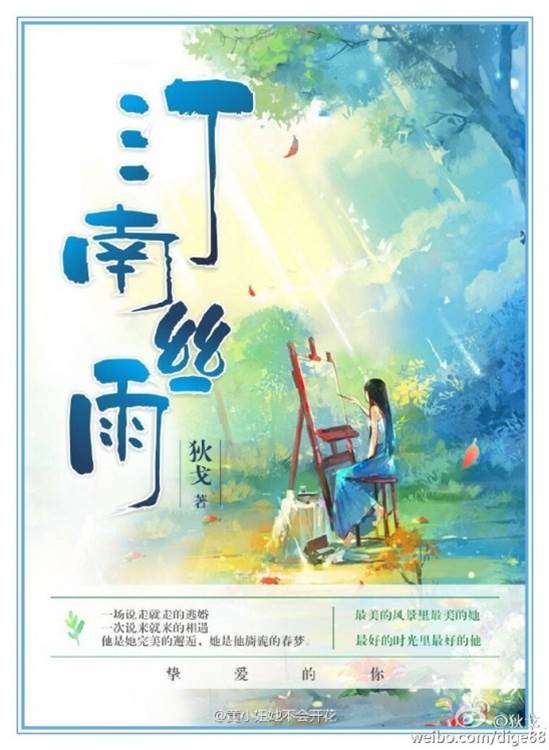《小嬌寵花招多,高冷大佬直呼抵不住》 第39章 這怕不是得寵上天吧
4Th“?”
邵崇年並不知道宗玉笙在說誰。
他今天一天都在開會,如果不是宗玉笙發燒,他或許這會兒還在公司加班,他是真的不知道黎曼琳以他的名義都做了些什麽,甚至晚上派車去接這件事,都是助理安排的。
宗玉笙見邵崇年皺眉一頭霧水的樣子,隻覺得沒意思,他可以直接要求不要在他麵前提起黎曼琳,也沒必要在麵前裝傻。
“算了,我還是繼續睡。”宗玉笙翻了個,背朝著邵崇年的方向。
是不好,這話問得本就越界了,他避而不答也好,省得難堪了。
邵崇年沒再說什麽,隻是坐回椅子上,繼續理公務。
房間很靜,靜得能清楚聽到他敲擊鍵盤的聲音。
一時有些睡不著,又不敢說話,怕打擾他。
後半夜,也許是退燒藥的藥效過了,宗玉笙的高燒又反複,迷迷糊糊間覺得自己好像被死亡的手扼住了,整個人都在發沉。
想要尖求救,但是,卻什麽聲音都發不出來。
忽然,有一隻涼涼的手覆到額上,那人大概是發現了高燒又反複,輕輕推搡想把起來去醫院,但宗玉笙卻意識迷離,咕噥著撒:“我不要去醫院,我不要打針……”
這是小時候逃避去醫院最常用撒的模式,父母什麽都慣著,唯獨在這件事上絕對不會慣著。
所以,每次高燒不退,最後都會被拉去醫院挨屁針,對那針頭已經產生了深刻的影。
猜床邊的那個人最後也會把架到醫院去。
可邵崇年沒有,一直都躺在綿綿的床裏,沒有換位置。
又過了一會兒,耳邊多了幾道人聲,聽著男男都有。
然後……然後……宗玉笙好像又挨了屁針!
Advertisement
什麽?
是做夢還是真實發生的?
“爸……媽……”終於發出了聲音,但呼喚的人卻永遠都不可能再回應。
宗玉笙眼角有淚滾下來。
“邵先生,哭了。”
護士驚慌,這是從業十年,第一次給年人打針把人打哭的,更何況,這人還不是一般人,是個冒發個燒都驚的邵崇年大半夜大張旗鼓調集醫護過來打退燒針的人。
不會把打壞了吧。
打壞的話,眼前這個男人會一層皮吧。
邵崇年走到床邊,聽到宗玉笙裏咕噥著喊爸媽,他沉了口氣,輕輕幫抹掉了眼角的淚。
這人平時張牙舞爪的,好像沒什麽怕忌,一到生病,又變回了實實在在的小生模樣,可也正是偶爾流出的這一麵,讓他覺得真實。
生病難的時候,誰不會想父母呢。
他也會。
“邵先生,我下手很輕的,也不知道怎麽……”
“沒關係,矯。”
護士:“……”
這是能聽的?
護士尷尬地笑了一下,心想,矯還不是您老慣出來的,發燒的人迷糊囈語說不想去醫院,您就真的把醫院搬到了家裏,這怕不是得寵上天吧。
**
打完針之後,宗玉笙的高燒才算慢慢退下去。
後半夜,徹底睡舒坦了。
這一覺醒來,劫度完了,天也亮了。
宗玉笙睜開眼睛,看到邵崇年趴在床邊睡著了,他還穿著昨天的西裝,看樣子是守了一夜。
他的手,甚至連睡著了都還抓著的手沒放。
宗玉笙扭頭,看著他睡著的側,心裏得泛起一池春水,但同時,又有點害怕,怕這樣溫脈脈的瞬間多了,會沉淪。
他們可以是最純粹的關係,但不能有。
當然,這對邵崇年來說,或許並不算,但是,怕自己會心。
Advertisement
宗玉笙回了手。
邵崇年睡得淺,覺到的手,他睜開了眼睛坐正,來不及舒展一下僵的四肢,就著急用手背去的額頭。
“燒退了?”
“退了。”宗玉笙說。
邵崇年這才了個懶腰。
“邵先生,你怎麽趴在這裏睡啊?不難麽?”宗玉笙淺淺表達關心。
“你說呢?”
“我昨晚發燒,我什麽都不知道。”
“是啊,你是什麽都不知道。”邵崇年著發脹的太,想起昨晚還是有點後怕。
他還是第一次見年人發燒發得這麽高的,到最後,他都覺得如果再不急送醫,可能會筋。
可偏這人發著燒還一子的倔強,死活不肯去醫院。
他沒辦法,才把若康的一支醫療隊連夜調到海居來。
“抱歉,嚇著你了吧,我從小就這樣,幾乎每次發燒都得打屁針或者掛水才能退下來。”
“那你不早說?”早點告訴他,他至不會慌到失態。
“昨天吃了藥退下來了,我以為這次會例外不用打針呢。”頓了頓,“等等,說起打針,我是不是挨針了?”
邵崇年不語。
說起打針,他更頭疼。
昨晚急打完退燒針,他原以為隻要燒退了就好了,可誰知哭哭啼啼半夜,他怎麽哄都哄不好。
“打了。”
宗玉笙趕手去按自己酸脹的左,“誰給我打的針,你嗎?”
“我可沒這個本事。”邵崇年說。
“那是誰?”
“護士。”
“護士?哪裏來的護士?”
邵崇年還沒回答,就見眨著眼又問了一句:“這個護士信得過嗎?”
“什麽意思?”
“我的意思是,你這樣把護士招到海居裏來,不會讓別人知道你在海居金屋藏嗎?”
畢竟,現在和之前可不一樣了,現在黎曼琳已經回國了,而且,可領教過了,這個人絕對不是善茬。
Advertisement
如果讓黎曼琳知道邵崇年還在海居藏了個小人,估計得捅破了天。
“這不是你需要擔心的事。”邵崇年語氣倏然變冷。
昨天從若康調來的人,都是明月灣的簽約醫生,他每年支付高昂的簽約費用,他們還不至於多多舌去傳雇主的八卦。
倒是,看來是腦子沒燒糊塗倒是燒明了,一睜眼就懂自保了。
**
宗玉笙去洗了個頭洗了個澡,洗去了昨晚的兩汗,覺像是重生了。
而重生後的第一覺就是,了。
宗玉笙下樓,看到邵崇年站在客廳的吧臺上泡咖啡。
他已經洗漱好換過服了,行走的西裝架子今天難得沒有穿西裝,而是穿上了淺的薄和長,渾散發著高山孤雪的清孑。
宗玉笙走到他邊,從後抱住了他。
能覺到,自剛才問了護士是否信得過後,邵崇年的氣就變了。不知他在介懷什麽,總之,昨晚的脈脈溫,一下子就散了。
“邵先生,你昨晚照顧了我一夜,我該怎麽報答你呢?”問著,手像小魚一樣遊進他的擺,在他上胡遊走。
邵崇年一把抓住的手:“你想幹什麽?”
“我想報答邵先生啊。”宗玉笙繞到邵崇年麵前,湊進他的懷裏,昂頭去吻他的。
邵崇年別開頭,躲開了的吻。
“你確定這是報答不是報複?”他問。
“嗯?”宗玉笙不解。
邵崇年推開了:“我看你是想把冒傳染給我。”
宗玉笙:“……”
天地良心,可真的沒有。
“既然你把我想得那麽壞,那就別怪我真使壞了。”宗玉笙話落,直接踮起腳,用手箍住了邵崇年的後腦勺,強吻住他的。
平時都是被侵占掠奪的那一個,今天忽然發起攻擊,完全沒有章法可言。
Advertisement
一,撬一撬,咬一咬……
可十八般武藝都用絕了,邵崇年還是薄閉,毫沒有要失守的樣子。
果然,隻要他不想,就沒辦法勾到他。
宗玉笙氣餒,正要放棄鬆開他,邵崇年忽然反客為主,摟住的腰,啟勾住了的舌尖。不過他吻得很輕,這個吻沒有一點點,好像純屬是為了配合的玩鬧。
一吻結束,兩人輕微地息著。
“邵先生不怕被我傳染嗎?”宗玉笙得了便宜還賣乖。
“我要是怕被你傳染,昨天晚上就不會回來。”更不會守整整一夜。
宗玉笙覺氣氛變好了一點,笑嘻嘻地複又抱住他,趁熱打鐵:“邵先生,想不想要?”
邵崇年蹙眉:“你不要命了?”
才剛退燒就敢問他這樣的虎狼問題。
“可是,你的給我傳遞信號,好像說你要誒。”宗玉笙指了指邵崇年的。
某位弟弟已經起立敬禮。
“邵先生如果想要,我當然舍命奉陪啊。”宗玉笙蹭著他,“所以,要嗎?”
邵崇年手把推開了。
自從開葷後,他的好像越過了他的大腦,直接控於。
不靠過來,就什麽事都沒有,可一旦靠過來,他立刻就像是被施了是魔法一樣,變得不像之前的那個他。
“不解決不難嗎?”宗玉笙問。
“我有的是辦法解決。”邵崇年說。
宗玉笙心湖裏落下一塊大石,水花四濺。
是啊,他又不止一個人,著什麽急?
**
這次冒,可以用“病來如山倒”形容。
宗玉笙已經很久沒有得過這樣嚴重的冒了,每天戴著口罩帽子遮得嚴嚴實實去上課,課程一結束就回海居睡覺。
蕭一筱調侃是不是打著冒的名義去整容了,鬼鬼祟祟不見人。
苗苗幫腔:“就笙笙那臉蛋,還需要整容?”
蕭一筱:“也是,整容就等於毀容。”
這一周,邵崇年每天下班都會回海居,宗玉笙真搞不懂他,不和做,卻每天回來,也不知道是幾個意思,害為了見他,每天還得洗頭。
一周後,宗玉笙的冒終於痊愈。
馮老師見狀態恢複,開始要求每天去練舞房訓練,為校慶演出做準備。
就這樣,剛好就又忙了起來。
對此,邵崇年頗有微詞:“你們老師是不是應該再讓你多休息幾天?”
宗玉笙以為他是不滿學校的訓練榨了原本屬於他的時間,於是乎,直接服一,過去摟他:“邵先生,現在做嗎?”
邵崇年瞪一眼:“你腦子裏就沒點別的事?還是覺得我腦子裏就沒點別的事?”
宗玉笙:“……”
好吧,這男人真難琢磨。
那之後好幾天,邵崇年都沒有回海居,宗玉笙也樂得清淨,雖然每次在他麵前表現出如狼似虎的樣子,但其實每天訓練完回家累得骨頭都要散架了,隻是不想讓他覺得掃興而已。
又過了一周,校慶要表演的曲目宗玉笙終於完全吃,覺得自己可以稍微放鬆一下,準備和室友們約個夜宵,結果從舞蹈房裏一走出來,就看到了林西沉靠在車邊等。
“笙笙!”林西沉見出來,朝招手。
宗玉笙簡直服了這個男人,繼上次論壇的事鬧得沸沸揚揚之後,林西沉竟然還有臉來學校。
他真是主打一個隻要他不覺得尷尬,尷尬的就是別人。
“笙笙!”林西沉見宗玉笙不理,趕追上來,“我有點事找你,我們聊一聊吧。”
“我和你沒什麽好聊的,之前禾酒店的監控視頻我還保存著,你要再出現在我麵前,小心我去告你擾!”
“你別這樣,我是真的有事想要告訴你。”
宗玉笙並不問什麽事,直接說:“我不想聽。”
“是你小叔的消息,你也不想聽?”林西沉直接放大招。
果然,宗玉笙聽到“小叔”兩個字,腳步瞬間就頓住了。
“我小叔?你知道他在哪裏?”
宗氏破產之後,宗玉笙的小叔宗盛珒也出了事,他在和投資人談判的路上出了車禍,當時宗盛珒乘坐的轎車為了躲避一輛大貨車,不慎衝出盤山公路,墜海中。
車子墜海後,當地的警察立刻開展搜救,但是海中隻找到了當時開車司機的,小叔宗盛珒不見了,搜救隊在附近海域尋找了很多天,都沒有找到他。
最後,專家下判斷,說很可能順著海水的流向被衝到其他海域中去了,很難再找回。
宗盛珒就這樣既不見人也不見的失蹤了。
猜你喜歡
-
完結638 章
買一送一:首席萌寶俏媽咪
盛安然被同父異母的姐姐陷害,和陌生男人過夜,還懷了孕! 她去醫院,卻告知有人下命,不準她流掉。 十月懷胎,盛安然生孩子九死一生,最後卻眼睜睜看著孩子被抱走。 數年後她回國,手裡牽著漂亮的小男孩,冇想到卻遇到了正版。 男人拽著她的手臂,怒道:“你竟然敢偷走我的孩子?” 小男孩一把將男人推開,冷冷道:“不準你碰我媽咪,她是我的!”
116.1萬字8.18 310839 -
完結75 章

一見到你呀
1. 向歌當年追周行衍時,曾絞盡腦汁。 快追到手的時候,她拍屁股走人了。 時隔多年,兩個人久別重逢。 蒼天饒過誰,周行衍把她忘了。 2. 向歌愛吃垃圾食品,周行衍作為一個養生派自然向來是不讓她吃的。 終于某天晚上,兩人因為炸雞外賣發生了一次爭吵。 周行衍長睫斂著,語氣微沉:“你要是想氣死我,你就點。” 向歌聞言面上一喜,毫不猶豫直接就掏出手機來,打開APP迅速下單。 “叮鈴”一聲輕脆聲響回蕩在客廳里,支付完畢。 周行衍:“……” * 囂張骨妖艷賤貨x假正經高嶺之花 本文tag—— #十八線小模特逆襲之路##醫生大大你如此欺騙我感情為哪般##不是不報時候未到##那些年你造過的孽將來都是要還的##我就承認了我爭寵爭不過炸雞好吧# “一見到你呀。” ——我就想托馬斯全旋側身旋轉三周半接720度轉體后空翻劈著叉跟你接個吻。
21萬字8 9512 -
完結43 章

我的愛生生不息
雲知新想這輩子就算沒有白耀楠的愛,有一個酷似他的孩子也好。也不枉自己愛了他二十年。來
4.3萬字8 13074 -
完結60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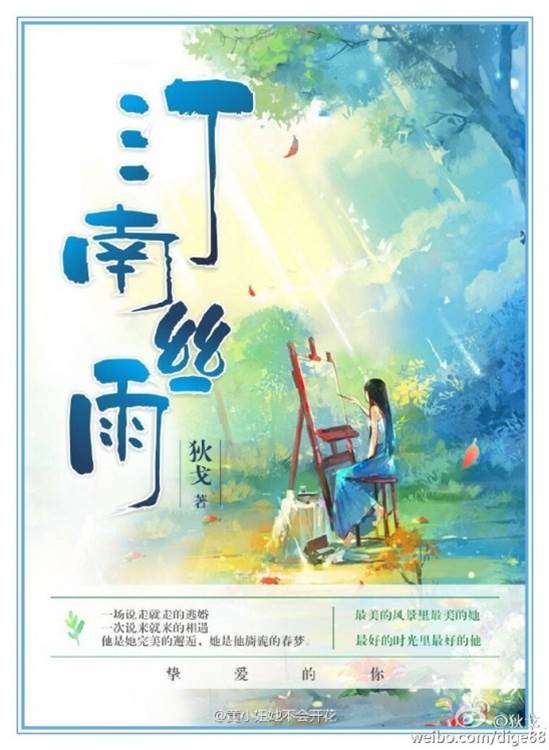
汀南絲雨
通俗文案: 故事從印象派油畫大師安潯偶遇醫學系高才生沈司羽開始。 他們互相成就了彼此的一夜成名。 初識,安潯說,可否請你當我的模特?不過我有個特殊要求…… 婚後,沈醫生拿了套護士服回家,他說,我也有個特殊要求…… 文藝文案: 最美的風景裡最美的她; 最好的時光裡最好的他。 摯愛的你。 閱讀指南: 1.無虐。 2.SC。
16.9萬字8 9132 -
完結222 章

退婚后被殘疾大佬嬌養了
真千金回來之後,楚知意這位假千金就像是蚊子血,處處招人煩。 爲了自己打算,楚知意盯上了某位暴戾大佬。 “請和我結婚。” 楚知意捧上自己所有積蓄到宴驚庭面前,“就算只結婚一年也行。” 原本做好了被拒絕的準備,哪知,宴驚庭竟然同意了。 結婚一年,各取所需。 一個假千金竟然嫁給了宴驚庭! 所有人都等着看楚知意被拋棄的好戲。 哪知…… 三個月過去了,網曝宴驚庭將卡給楚知意,她一天花了幾千萬! 六個月過去了,有人看到楚知意生氣指責宴驚庭。 宴驚庭非但沒有生氣,反而在楚知意麪前伏低做小! 一年過去了,宴驚庭摸着楚知意的肚子,問道,“還離婚嗎?” 楚知意咬緊牙,“離!” 宴驚庭淡笑,“想得美。” *她是我觸不可及高掛的明月。 可我偏要將月亮摘下來。 哪怕不擇手段。 —宴驚庭
60.5萬字8 3342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