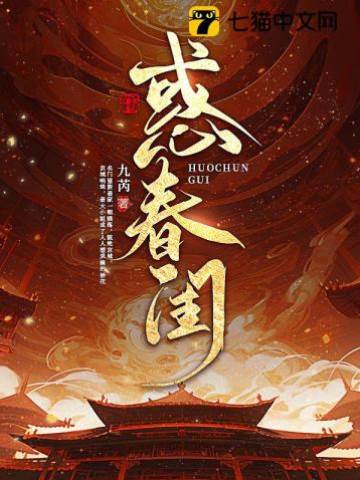《你都要請旨嫁人了,孤還克制什麼》 第61章 我想要出宮
陳洮能為謝臨珩的心腹,辦事能力自是不必多說。
聽到“避子湯”這三個字,他當即拿出帔帛,對虞聽晚說:
“普通的避子湯雖能避孕,但有一定的傷效果,公主您先出手腕,微臣為您把把脈,結合您的質調和一下藥方,盡量做到不傷。”
虞聽晚出手。
陳洮將帔帛放在腕上。
輕垂著頭,仔細把脈。
不多時,他收了帔帛,說:
“微臣這就去改良藥方,請殿下稍微一等。”
虞聽晚收回手,“有勞陳太醫。”
陳洮躬:“不敢,這是微臣分之事。”
陳洮離開后,按照虞聽晚的口味準備的膳食隨之呈了上來。
歲歡和若錦在左右侍奉虞聽晚用膳。
“公主,這都快午時了,您早膳還沒用,先用早膳吧。”
若錦也說:“稍后還要喝藥,總不能空腹的。”
虞聽晚拿起筷子,在滿桌的飯菜上掃過。
腹中雖空的,但過了的那勁兒,這會兒倒是又不了。
在若錦和歲歡番夾菜下,虞聽晚吃了五分飽放下了筷子。
又過了半個時辰,熬好的避子湯被端了上來。
那藥碗一靠近,那種苦到的味道就在殿蔓延開。
虞聽晚皺了皺眉。
端著這碗‘避子湯’,頭一次有些猶豫。
Advertisement
用勺子攪了攪,隨后遞到邊嘗了一小口。
那黑乎乎的藥剛一口,就立刻從旁邊拿了顆餞含進里。
苦到極致的味道,從舌尖迅速炸開,哪怕含了餞,仿佛都化不去那苦味。
見擰著眉,若錦輕聲開口:
“公主?”
虞聽晚將藥放在桌上,仇大苦深地盯著它,“今天這避子湯,怎麼這麼苦?”
若錦同樣看向那碗黑漆漆的藥,“陳太醫說,這是修改后的藥方,有效又不傷,只一個缺點,就是很苦。”
虞聽晚咽下口中那顆餞,重新端起藥碗,沒再用小勺,直接端著碗,屏著呼吸,一口氣迅速喝了下去。
就在喝完最后一口的同一時刻,若錦立刻遞過去兩顆餞。
“公主,快去去苦味。”
虞聽晚將餞咬在里,看著面前的藥碗,當即抬手。
“快端下去。”
一碗湯藥下去,虞聽晚覺得剛才吃的飯都白吃了,胃里翻江倒海,近乎痙攣。
歲歡立刻讓人收了下去。
并快步走到窗前,開窗通風,散去殿的苦藥味。
—
晚上。
戌時一到,謝臨珩就來了淮殿。
他掃過空的殿宇,問:“公主呢?”
歲歡低著頭,聲音很低:“……公主在偏殿。”
Advertisement
謝臨珩轉,往偏殿走去。
后面的歲歡正想跟上,卻聽到他說:
“不必跟著。”
虞聽晚喜歡各種花卉,小時候,建帝給弄了很多珍奇的花花草草,供賞玩。
后來年齡再大一些,金尊玉貴、千百寵的小公主對親手種養花草起了興趣。
一有時間,就拿著各種花種,學著花匠的樣子,自己培育花苗。
曾經的寧舒公主,是整個皇宮的掌上明珠,建帝和司沅將唯一的寶貝兒寵得跟眼珠子似的,喜歡什麼,他們就無底線的給什麼。
種花這種小小的好,自然是全力支持。
‘支持’的結果便是,沒過多久,昔年帝后的宮殿中,就出現了很多小公主擺弄的各種奇怪花草。
甚至就連建帝的書房,都被擺上了各種小花卉。
每逢覲見的大臣瞧見那些‘開的隨心所、無所約束又極為漂亮’的鮮花并問及花的來歷時,建帝每每都會寵溺又自豪地說:
——“這是公主親手種的花,是不是比花房培育的好看多了?”
宮變之后,國破家亡,是人非。
虞聽晚再也沒有種植過任何一株花草。
夜一點點降臨,虞聽晚坐在窗前,借著殿外宮盞的暈,出神地看著淮殿庭院中那棵開到荼靡的楸樹花。
Advertisement
宮變之前,先前的宮殿中,也有這麼一棵高大的楸樹。
但宮變那日,那棵楸樹被北境那群敵寇毀壞了。
現在淮殿中的這棵楸樹,是當初住進來半個月之后移栽過來的。
那個時候剛經歷宮變,夜夜夢魘,日日緒萎靡不振,甚至一度病倒臥床不起。
直到昏昏沉沉間,庭院中被人移栽了這棵和宮變時死去的那棵非常相似的楸樹,
過往的一幕幕,仿佛都通過這棵楸樹重現在眼前。
后來借著這棵楸樹,虞聽晚強行讓自己振作起來,每日看著它繁茂的枝葉一點點下那些傷痛,一步步從那些淋淋的過往中走出來。
謝臨珩過來時,看到的,就是這麼一幕。
男人腳步微不可查地頓了下。
視線掠過窗外的楸樹花,定格在形單薄的子上。
他眸漆邃,眸底神明明滅滅,讓人看不分明。
須臾,謝臨珩走過去。
從后擁住。
將微微僵的子納進懷里。
輕聲問:“寧舒,還想要什麼?”
虞聽晚眼底掀起一點點零星的芒。
明知是不可能,方才思緒的影響,仍舊是下意識問了句:
“不管我想要什麼,太子殿下都能應允我嗎?”
謝臨珩黑眸微斂,沒應聲。
Advertisement
虞聽晚轉過,看向他。
語氣認真:“我想要出宮。”
謝臨珩眼底劃過一抹轉瞬即逝的痛。
他指腹過眉眼,聲線依舊。
“除了這個,我都能答應你。”
“寧舒,除了出宮,你還想要什麼?”
虞聽晚眼皮垂下,輕呵,“可我只想出宮。”
謝臨珩掌著后腦勺,讓抬頭看他,漆黑濃稠的眸,凝著的。
薄微,字句清晰。
“寧舒,我說過,只要你答應做我的太子妃,何時出宮,全憑你心意。”
虞聽晚的聲音冷涼如水,直直對上他視線:“謝臨珩,你的太子妃能是任何人,但絕不可能是我。”
本不相信,在擔了太子妃的名義和份后,以他的子,還會放出宮。
現在沒有這層份,都被困在這個深宮中死死不了,又何況是為東宮儲君的妃嬪。
那時,有著這層此生都難以擺的份的束縛,這一輩子,怕是都別想再離開這囚籠半步。
再者,厭惡現在的皇宮是一方面,不想和謝家的任何人牽上半分關系是另一方面。
所以謝臨珩口中那種——婚后允自由出宮的承諾,本不信,也不敢信,更不愿信。
猜你喜歡
-
完結521 章

一品女仵作
女法醫池時一朝穿越,成了仵作世家的九娘子。池時很滿意,管你哪一世,姑娘我隻想搞事業。 小王爺周羨我財貌雙全,你怎地不看我? 女仵作池時我隻聽亡者之苦,還冤者清白。想要眼神,公子何不先死上一死?
96.1萬字8.18 24943 -
完結132 章

國子監小食堂
孟桑胎穿,隨爹娘隱居在山林間,生活恣意快活。一朝來到長安尋找外祖父,奈何人沒找到,得先解決生計問題。陰差陽錯去到國子監,成了一位“平平無奇”小廚娘。國子監,可謂是天下學子向往的最高學府,什麼都好,就是膳食太難吃。菜淡、肉老、飯硬、湯苦,直吃…
66.7萬字8 17393 -
完結312 章

和離后,戰神王爺每天想破戒
穿越後,鳳卿九成了齊王府棄妃,原主上吊而死,渣男竟然要娶側妃,鳳卿九大鬧婚宴,踩着渣男賤女的臉提出和離。 渣男:想和離?誰會要你一個和離過的女子! 顧暮舟:九兒,別怕,本王這輩子認定你了! 鳳卿九:可我嫁過人! 顧暮舟:本王不在乎!這一生,本王只要你一個! 攜手顧暮舟,鳳卿九翻雲覆雨,憑藉自己高超的醫術,在京都名氣響亮,豔壓衆人。 渣男後悔,向她求愛。 渣男:以前都是我不對,過去的就讓他過去吧!我們重新開始好不好? 鳳卿九:不好意思,你長得太醜,我看不上! 渣男:我到底哪裏比不上他? 她冷冷地甩出一句話:家裏沒有鏡子,你總有尿吧!
55萬字8.18 124421 -
完結17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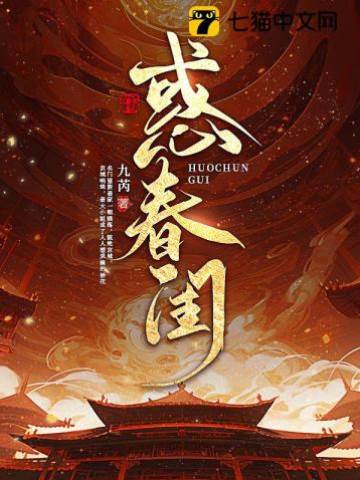
惑春閨
名門望族薑家一朝隕落,貌絕京城,京城明珠,薑大小姐成了人人想采摘的嬌花。麵對四麵楚歌,豺狼虎豹,薑梨滿果斷爬上了昔日未婚夫的馬車。退親的時候沒有想過,他會成為主宰的上位者,她卻淪為了掌中雀。以為他冷心無情是天生,直到看到他可以無條件對別人溫柔寵溺,薑梨滿才明白,他有溫情,隻是不再給她。既然再回去,那何必強求?薑梨滿心灰意冷打算離開,樓棄卻慌了……
31.5萬字8.18 8576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