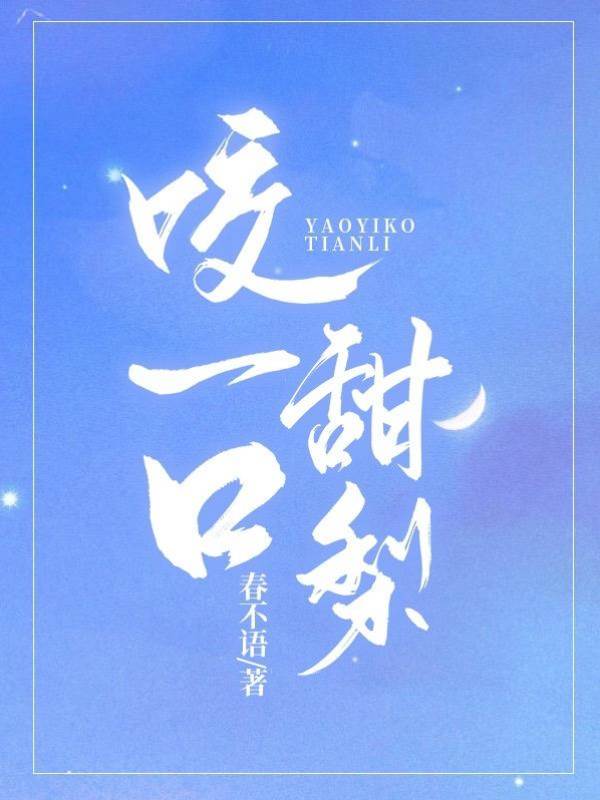《偏寵掌心嬌,少帥輕點撩》 第453章 拜年
從大帥和大帥夫人的院子出來,項沖帶著樓歆又去江四爺和姰暖那兒拜年。
姰暖雖然出了月子,但還沒在屋外走。
不過一大早就梳了頭發,換了新裳,就是防著有客人來做的準備。
項沖單獨去書房見江四爺,柏溪就領了樓歆上樓來。
兩人進屋時,姰暖正在屋里陪闊闊玩兒。
小家伙都不記得多久沒見過母親,這會兒黏乎得不得了,一直在姰暖懷里要抱著,也不鬧著下去玩兒。
他如今胖墩墩,姰暖可抱不他了,就摟著他坐在榻上,看兒子拿小餅干喂貓。
見樓歆進來,含笑招呼人坐。
“來了,過來說話。”
樓歆笑了笑,搬了個繡凳坐在邊,看了看闊闊和榻上那只胖的圓滾滾的白貓,主開口說。
“我來給您拜年,先前母親剛過世,我上掛白,沒好來看夫人。”
姰暖月眸淺彎,“我知道,這些日你一個人,也辛苦。”
樓歆淺笑搖頭,“世人都要經歷這一遭,都過去了。”
岔開話題,從袖兜里掏出幾個小紅包,手遞給闊闊:
“大爺,我給你備好了歲錢,要健健康康長大啊。”
闊闊抬起頭,黑溜溜的眼看了看樓歆,又看姰暖。
姰暖笑,“怎麼還給這麼多?”
樓歆,“不多,還有四爺和五小姐的,他們還小,我就不過去看了,等能抱出來了,再抱一抱。”
姰暖角彎了彎,就對著闊闊點頭示意。33qxs.m
闊闊立馬一把抱住幾個小紅包,樂滋滋的笑,出兩排潔白小米牙。
Advertisement
“謝謝紅包,嬸嬸新年好。”
樓歆一愣,驚訝于這孩子真甜。
姰暖和柏溪也齊齊笑起來。
姰暖了把兒子的發頂,告訴樓歆:
“盈盈剛教的,現在正這個年紀,教什麼學什麼,現學現賣。你們來前,還拽著跟他父親喊新年好,一定要紅包。”
江四爺哪給人準備過紅包?自己的孩子也一樣。
最后被小家伙掛在兒上,不給就哭給鬧的,只能把自己手上常年戴的金曜石戒指薅下來給了他。
姰暖先前剛從闊闊手里給把指戒哄回來。
樓歆聽罷也笑的掩了掩,又夸道。
“大爺聰慧。”
兩人聊了一會兒,紅樓就上來稟話,說項沖準備走了。
樓歆也同姰暖告別,下樓跟著項沖一起離開。
一走,姰暖便同柏溪說:
“看起來氣不錯,應該從母親病逝的悲痛里緩過來了。”
柏溪點點頭,“項總軍回來了,當然也有人安,會好起來的。”
姰暖笑了笑,“但愿大家的日子,都過得越來越好。”
“會的。”柏溪也笑。
兩人說著話,門外傳來沉穩腳步聲,江四爺上來了。
闊闊見著他,手里餅干一扔,著小紅包從姰暖懷里呲溜下去,邁著小短兒撲到他上,抱住軍靴。
“父七,紅包沒給闊!”
姰暖‘撲哧’笑出來,連忙掩住。
江四爺垂眼看著掛在上的小球,無語失笑,屈指彈他腦瓜崩兒。
“還沒忘這茬?戒指都給你了!金曜石的,不比大洋值錢。”
Advertisement
闊闊擰著小眉頭,理直氣壯嚷嚷:
“母七稀飯,闊送給母七,沒有紅包啦!父七給紅包!”
江四爺頭疼擰眉,又氣又好笑地斥他:
“...你先把話給老子說清楚了,什麼父七母七,你還是爹吧!”
闊闊不依,拽著他使勁兒晃:
“給!爹給!爺爺給,祖姆姆給,母七給,就爹不給!爹給闊!”
意思是,誰都給,憑什麼就爹不給?
姰暖聽了笑不可遏,差點笑疼了肚子。
江四爺也笑起來,一手薅了兒子領,將小家伙提溜起來抱在懷里,無奈妥協。
“給,給你,爹給你包個頂大的!”
又跟姰暖說,“這麼財迷,像了誰?”
姰暖笑了一會兒,連忙扭頭朝宋姑姑睇眼。
宋姑姑笑盈盈又去翻了個紅包出來,姰暖往里頭塞了滿滿的大洋,讓江四爺給闊闊。
小家伙抱著幾個小紅包,笑得心滿意足,一雙黑溜溜大眼睛瞇一條兒。
到正午開飯,因為大帥和大帥夫人在宅子這邊過年,江家人都到宅子這邊聚了個齊全,人人都給闊闊塞大紅包。
沉甸甸的滿懷大洋,闊闊抱不住,轉頭全放在大帥夫人懷里。
大帥夫人驚訝,“祖母給你收著?”
闊闊趴在上,點了點頭一臉嚴肅:
“幫闊收,拿很多,給姆姆買大房子,很多很多房間,很多很多床。”
眾人聽著言稚語有趣,雖然不明所以,但還是紛紛被逗笑。
三姨太抱著孫子,笑呵呵逗闊闊:
Advertisement
“大爺還用買大房子?你父親的宅子都夠大了,難不還不夠住?”
大帥夫人摟著闊闊,也笑著替孫子解釋:
“前一陣兒搬過來,鬧著要跟他母親住去,暖暖那邊坐月子,又多兩個小的,哪兒顧得上他?我就哄他說那邊沒屋子給他住,他去了要睡地板!”
寶貝的了闊闊嘟嘟的小臉兒,逗他道:
“我們闊闊出息了,知道自己攢錢買大房子,這就不用睡地板了,是不是?”
眾人聽罷,這才明白過來怎麼回事,頓時更笑得厲害。
姰暖笑了會兒,再看闊闊,卻有點心酸了。
扭頭跟江四爺耳語,“太小了,我們都多久沒好好陪他?我如今也出了月子,接過來住吧。”
不能讓孩子心里不平衡,以為父親母親只親弟弟妹妹,卻不管他。
這麼一想,姰暖心里就揪得慌。
江四爺握住手,包在掌心了。
“...習慣就好,大了反倒不能慣他這病,往后難不不分開?”
姰暖無語,“這麼冷,是不是親生的?兒子以后要怪你!”
江四爺輕笑,歪頭同耳語:
“,讓他們都怪爺,鐵定不是母親不親。”
姰暖月眸輕瞪,“他們?”
江四爺,“等那兩個再大點兒鬧騰起來,也給他們攆出去,一視同仁,沒什麼親不親的。”
姰暖驚得頭發都要豎起來,直勾勾盯著他,滿眼控訴。
“......哪有你這樣的?”
江四爺笑得波瀾不驚。
*
飯后,又有人陸續來給大帥拜年,男人便起去了書房坐。
Advertisement
人跟孩子都在二樓中廳。
家里難得這麼熱鬧,姰暖還挨個兒抱了抱程兒和錦兒。
“哎呀好重,剛兩個月呀,你照顧的真好。”
李栩月聽言笑了笑,“能吃能睡的,很省心,我聽媽媽說,省心的孩子都養。”
薛紫凝輕輕刮了下錦兒嘟嘟的小臉兒,也嘆道:
“真是幾天一個樣子,瞧瞧現在,比程兒的臉都圓了。”
又說起自己養的程兒,“我瞧著比闊闊,比錦兒,都要費心些,要麼只他最瘦,如今還長了脾氣,不就急的要哭,我真是頭疼死。”
雖然在抱怨,但臉上還是笑盈盈的,可見心里很疼養子。
李栩月抿笑了下,沒說什麼。
姰暖也只撿好聽的講,打趣道:
“有脾氣還不好?江家的孩子哪個沒脾氣?闊闊如今都要橫小霸王,程兒要沒脾氣,可得被他大哥欺負,到時候大嫂又該心疼了。”
薛紫凝笑,“都是自家孩子,欺負就欺負了,出去不被旁人欺負便。”
正說笑著,柏溪就上來了。
到姰暖耳邊低聲稟話:
“外頭來人,找五爺,那個歌姬,說來給大帥和夫人拜年,書房那邊在談事,還沒往里稟,您看...”
......
猜你喜歡
-
完結223 章

總裁追婚記:嬌妻哪裏逃
三年前,初入職場的實習生徐揚青帶著全世界的光芒跌跌撞撞的闖進傅司白的世界。 “別動!再動把你從這兒扔下去!”從此威脅恐嚇是家常便飯。 消失三年,當徐揚青再次出現時,傅司白不顧一切的將她禁錮在身邊,再也不能失去她。 “敢碰我我傅司白的女人還想活著走出這道門?”從此眼裏隻有她一人。 “我沒關係啊,再說不是還有你在嘛~” “真乖,不愧是我的女人!”
29.6萬字8 5232 -
完結1939 章

替嫁后我被大佬纏上了
所有人都說,戰家大少爺是個死過三個老婆、還慘遭毀容的無能變態……喬希希看了一眼身旁長相極其俊美、馬甲一大籮筐的腹黑男人,“戰梟寒,你到底還有多少事瞞著我?”某男聞言,撲通一聲就跪在了搓衣板上,小聲嚶嚶,“老婆,跪到晚上可不可以進房?”
290萬字8.18 189382 -
完結105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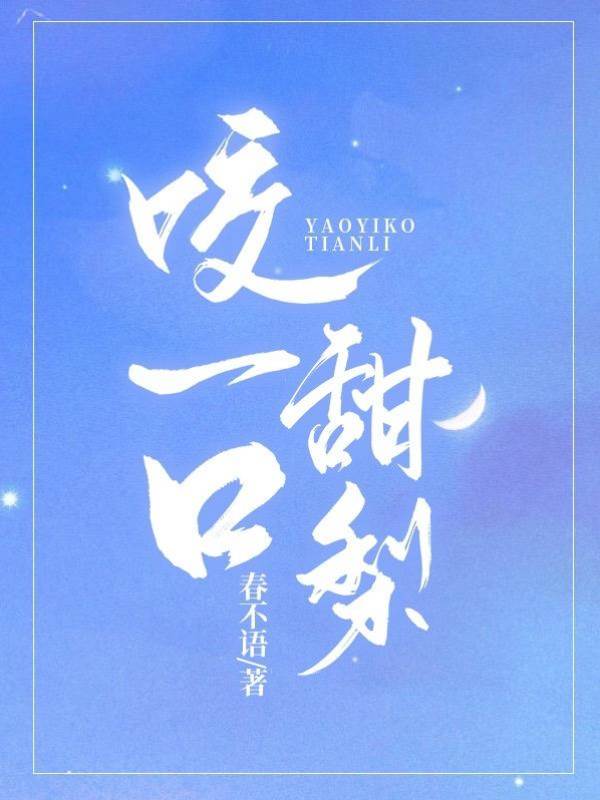
咬一口甜梨
白切黑清冷醫生vs小心機甜妹,很甜無虐。楚淵第一次見寄養在他家的阮梨是在醫院,弱柳扶風的病美人,豔若桃李,驚為天人。她眸裏水光盈盈,蔥蔥玉指拽著他的衣服,“楚醫生,我怕痛,你輕點。”第二次是在楚家桃園裏,桃花樹下,他被一隻貓抓傷了脖子。阮梨一身旗袍,黛眉朱唇,身段玲瓏,她手輕碰他的脖子,“哥哥,你疼不疼?”楚淵眉目深深沉,不見情緒,對她的接近毫無反應,近乎冷漠。-人人皆知,楚淵這位醫學界天才素有天仙之稱,他溫潤如玉,君子如蘭,多少女人愛慕,卻從不敢靠近,在他眼裏亦隻有病人,沒有女人。阮梨煞費苦心抱上大佬大腿,成為他的寶貝‘妹妹’。不料,男人溫潤如玉的皮囊下是一頭腹黑狡猾的狼。楚淵抱住她,薄唇碰到她的耳垂,似是撩撥:“想要談戀愛可以,但隻能跟我談。”-梨,多汁,清甜,嚐一口,食髓知味。既許一人以偏愛,願盡餘生之慷慨。
20.2萬字8 7866 -
連載256 章

全球通緝令,抓捕孕期逃跑小夫人
曾經顏琪以爲自己的幸福是從小一起長大的青梅竹馬。 後來才知道所有承諾都虛無縹緲。 放棄青梅竹馬,準備帶着孩子相依爲命的顏鹿被孩子親生父親找上門。 本想帶球逃跑,誰知飛機不能坐,高鐵站不能進? 本以爲的協議結婚,竟成了嬌寵一生。
45.2萬字8 466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