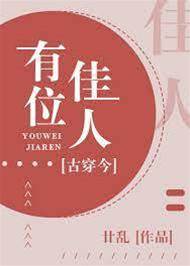《農門貴女有點冷》 第104章 衙門報喜
翻牆出,那自然是翻牆進。
雲蘿翻過牆頭一晃就不見了影,景玥卻站在牆外又看了許久,桃花眼瀲灧,在月下泛著粼粼波,全然一個懷春年郎的模樣,獨自回味著他的好心。
有黑人宛若暗夜的影,悄無聲息的出現在了他的後,「公子。」
景玥依然看著眼前這不高的圍牆,似乎隻需他輕輕一跳就能翻越進去,讓他連語氣中都帶上了些許愉悅,「何事?」
「剛傳來訊息,劉相病重已藥石無醫,劉喜大人卻在此時離開京城,正快馬往江南趕來。」
景玥終於將目從牆頭收回,「可知他為何而來?」老父病重,唯一的兒子卻千裡迢迢的往江南來了?
「尚未探知。」遲疑了下,又問一句,「公子,劉相的日子大概就在這幾天了,您可要回京奔……喪?」
一牆之隔的院子裡,雲蘿翻牆落地之後就順著原路返回,他們的屋裡,有搖曳的燈正從窗戶紙上出來,與外麵的月相輝映。
走過屋簷廊道,推門走了進去。
一進去,文彬就吸著鼻子湊了過來,「好香!三姐,你竟然一個人跑出去吃!」
雲蘿一掌擋在他的臉上將他無的推開,扯了掛在牆上的布巾到門外舀了水洗漱,可惜沒有牙刷,用青鹽刷牙總覺刷不幹凈。
文彬顛顛的跟在旁邊,不滿的說道:「三姐你的跑出去都不我一聲,剛才一轉就找不見你了。」
雲蘿含著水「咕嚕嚕」的漱口,然後張著問:「還有味嗎?」
文彬一臉控訴,「你上都是味!」
雲蘿用布巾,看來還得再洗個澡。
「三姐三姐,你去外麵吃啥了?」
「烤豬。」
「講,那小野豬都被走了!」難道是吃了別的卻安自己其實已經吃過烤豬了?如果真是這樣的話,他就明白三姐為啥一個人出去沒帶上他了。
Advertisement
雲蘿雖不知道他在想些什麼,但看他那眼神就曉得定不是什麼好玩意,便再次按著他的臉把他推了出去,一直推到屋裡麵。
雲萱笑看著他們鬧騰,說道:「別鬧了,快上床歇了吧,不然,明天可就又要賴床起不來了。」
文彬當即不服氣的說道:「我每天都起好早的,纔不會賴床呢!」
雲蘿從他旁走過,眼珠子溜過去斜斜的瞥了他一眼,「難道是我賴床?」
鄭小弟站在原地抓著手指頭扭了一會兒,然後乖乖的爬床上去了。
劉氏還坐在燈盞邊補服,臉上的青紫經過一天時間又消退了許多,在昏暗的燈下,若不仔細看已經看不大出來了。
第二天是八月十四,也是院試放榜的第二天,鄭大福這日一早就開始在村口徘徊,一直等到日落黃昏,鄭年中秋放假回來了,也沒有等到半點訊息。
連鄭穀和鄭收也忍不住的一整天都在翹首以盼,見老父親領著鄭年一家從外頭一臉失落的回來了,就安了一句:「爹不用著急,府城到咱這兒可是有好幾百裡路呢,來回一趟怎麼也得在中途住一宿,明天就定會有訊息了。」
鄭大福功的被安到了,臉舒緩,點點頭說道:「是我著急了,那差爺又不是隻一家報信,來回還這麼遠,現在怕是連縣太爺都還不曉得績呢。」
科舉考試,從院試到鄉試都是在傍晚放榜,放榜後,先有府衙的差役逐一通報在府城等候績的學子,同時傳信到各縣衙,再由縣衙派人通報到中試的學子家中。
從白水村到越州府城足有三百多裡路,尋常人趕路若是稍微拖延一些都要在中途住宿兩個晚上,府衙有快馬,倒是能一天就到,可府衙的人得先到縣城,由縣衙逐一核實確認之後再派人通報,再快也不夠時間在今天之就把訊息傳到白水村。
Advertisement
可即便明知如此,對於掛心考生績的家人來說,仍是會忍不住的早早就開始等候盼。
文彬練字後從外麵玩耍了回來,湊到雲蘿的麵前來輕聲說道:「狗蛋說,裡正阿公今天也在村口和爺爺一起嘮了一天的嗑呢。」
裡正的大孫子李繼祖也在此次的院試之列,期盼之心毫不會比鄭大福的。
雲蘿神微,問他:「姑婆呢?」
「這個我也不曉得。」他出去就找狗蛋玩了一會兒,話也都是從狗蛋那幾個小夥伴裡聽來的,自從開始認真讀書,他在村裡的訊息都閉塞了許多,「不過沒聽說姑婆也在村口。」
雲蘿點點頭,沒再多問。
不過袁家盼了三代人,就盼著袁承能夠重新撐起門楣,這一份期盼怕是尋常人家都遠遠比不上的。
隻是,袁家的祖籍並非本縣,也不曉得會不會通報到這裡來。
各自吃了晚飯,鄭穀和鄭收又去上房坐了會兒,跟老爺子和鄭年說上幾句話,鄭年也問了下兩個兄弟造新房的進展。
雖然分了家,但父子兄弟親人之間仍有割捨不斷的聯絡,時常坐一起說話聊天、互相問候一聲近況再正常不過。
次日一早,鄭大福又早早的往外踱了出去,鄭年在家裡讀了會兒書,終於還是忍不住的也出去等訊息了。
今日的天氣不大好,天剛亮的時候淅淅瀝瀝的下了一陣小雨,到辰時過後才終於了太。
天雖放了晴,雨後的道路卻越發的泥濘難行,一直到將近午時,忽聞村外傳來一陣鑼鼓喧天。
整個白水村都在剎那間轟了,田裡的、家中的,幹活的、聊天的、玩耍的人們紛紛聞著聲音匯聚過來,就見兩個衙差踩著半的泥水,一人牽著兩匹矮馬,一人則敲鑼開道,在裡正和諸多村民的引領下熱熱鬧鬧的往鄭二福家走去。
Advertisement
太婆已經聽到聲音,早領著家裡眷站在了大門外,看著不住靠近的人們,神難掩激。
「恭喜老太太,您的曾外孫袁承小公子高中院試的頭名案首!」
老太太頓時「阿彌陀佛」了一聲,鄭七巧更是喜極而泣,忙了淚水,從袖子裡掏出兩個荷包就塞到了衙差們的手中,「辛苦兩位差爺大老遠的專程跑一趟,家裡也沒啥準備的,這一點小心意給差爺換杯酒喝。」
兩位衙差了荷包,越發的喜逐開,滿口稱讚幾乎停不下來,又對匆匆跑回家的鄭二福說:「您家中好旺盛的福氣,去年是您孫婿得了院試的案首,今年又是您的外甥孫子,這兩年真是盡出年英才,連續兩年的院案首都是年輕的年郎,還是聯絡有親的郎舅。」
鄭二福不由得紅滿麵,胡氏和小胡氏抬出了滿滿一簸籮的花生瓜子大棗,先給兩位差爺塞了滿滿一大兜,然後分給跟來瞧熱鬧的村人抓著吃,又收穫了一大波讚譽和羨慕。
站在門口熱鬧了會兒,其中一名衙差對裡正說道:「接下來,可要到您家去討一杯水喝了。」
裡正一愣,接著整個人都直了起來,雙眼鋥鋥發亮,放開了嗓門聲音震天,「求之不得、求之不得,快快這邊請,莫說是一杯水,好茶好酒都有!」
這兩位剛才見了他卻啥都沒說,隻讓帶路來鄭二福家,還以為他大孫子這次是落榜了,雖有些失落,但想到繼祖年紀還小,他家又一向沒出過啥讀書人,倒也不是特別失。
沒想到峰迴路轉,他大孫子竟然考中了,這驚喜來得太突然,比剛纔在村口時就告訴他可要猛烈得多,老心臟有點承不住。
鄭二福用力的拍了拍他的背,笑著說道:「恭喜恭喜,你家繼祖有出息了!」
Advertisement
裡正咧著,滿臉的笑是止也止不住,「哪裡哪裡,跟你家袁小子比起可就差遠了。」
說了兩句話,然後他就急匆匆的領著衙差往自家去了,瞧熱鬧的村民也呼啦啦的跟著去了裡正家,僅留下零星幾個親近的,簇擁著老太太和鄭七巧進了屋。
雲蘿站在門口看了一眼,見裡頭笑聲不斷就沒有這個時候進去湊熱鬧,轉就要回去。
鄭小弟扯了扯的角,「三姐,你不去裡正阿公家嗎?」
「不是已經知道狗蛋的大哥考中了秀才嗎?還去做什麼?」
他就摳了摳兜在擺上的花生瓜子和大棗,雙眼亮晶晶的說道:「我去問裡正阿婆討喜果子。」
雲蘿於是就明白了他的意思,當即也沒有二話,隻將前麵的擺往上一兜,把他兜著的那些乾果子都轉移了過來,「多討一些。」
「好!」
他轉噠噠噠的跑遠了,而雲蘿則兜著一兜的乾果回到了家中。
回到家裡,就見劉氏在翻箱倒櫃的忙活著,不由問道:「娘,你在找什麼?」
劉氏看一眼,有些發愁,「承哥兒考了頭名案首,總得送點啥,隻是家裡也沒有能拿得出手的東西。」
「你不是給他做了一雙鞋嗎?」
「這哪裡夠?你也不瞧瞧姑婆都送了我們些啥。」
雲蘿了一顆花生來吃,不甚在意的說道:「那你用紅封包幾兩銀子,讓袁表哥喜歡什麼就自己去買?」
劉氏不輕不重的瞪了一眼,轉又自顧著忙碌起來。
雲蘿看了會兒,就有點看不下去了,說:「家裡能有什麼東西?還不如直接去鎮上買呢,買些好點的筆墨紙硯或是書籍,送禮斯文,他也能用得上。」
經過那短暫的幾天相,倒是覺得送他刀槍弓箭或許會更喜歡,可惜這些東西用來送一個新晉的秀纔好像不大合適,還是算了吧。
其實真覺得紅包好的,得了之後想買啥就能買啥。
劉氏被一提醒也回過神來,往外看了眼天,跟雲蘿商量道:「要不,小蘿你去鎮上走一趟?咱家也就你曉得這些東西,我和你爹是連好壞都瞧不出來的。」
「貴的總是要好一些。」
劉氏於是關了屋門,又從箱子底下掏出一個布包,揭開一層又一層,最後出了一錠五兩的銀子來,遲疑道:「這夠了嗎?」
「不需要這麼多!」雲蘿接過銀子,隨意的塞進袖子裡,說,「咱家就這條件,貴重不貴重都是心意,姑婆不會挑禮的。」
要是放在兩個月前,怕是把這屋子裡的東西全都典當了也不值五兩銀子。
劉氏訥訥的點了點頭,就是覺得先前收了姑婆的那麼多東西心裡有些過意不去,正好承哥兒考中了秀才,好歹能還上一份禮。
想到袁承科考,劉氏也想到了自家的大侄子,便說道:「也不曉得你大哥考得咋樣了。」
雲蘿皺眉,「如果考上了,也得給他備一份?」
「自然是要的。」
雲蘿無可無不可的「哦」了一聲,開門出去,隨口說道:「我先去看看。」
剛出大門,就見文彬捧著兜噠噠噠的跑了回來,看到就連連朝招手,低了聲音悄咪咪的說道:「兩位差爺在裡正阿公家喝了一碗水就走了,沒有來我們家。」
「走了?」
「對,走了,現在都該出村了!爺爺和大伯的臉可難看了,三姐你小心些。」
這跟我有什麼關係?
雲蘿輕哼一聲,從他的兜裡抓了一把花生,然後轉拐了個彎,打算避開某些人的路線出村去鎮上。
其實鄭文傑落榜並不意外,他若是考中了,才真的要好奇呢。畢竟去年的縣試和府試他都是低空飛過,排名都在最後幾個了,院試更是連第一場都沒有通過。
這些事不論他自己還是鄭年都是從不會在家裡說的,雲蘿知道卻是從虎頭的口中,而虎頭則是從栓子那兒問出來的。
栓子和鄭文傑雖不是同年,但畢竟在同一個書院裡麵,鄭文傑考過了生也曾在書院裡小小的風了一把。
今日中秋,鎮上又逢大集,往年的鄭家是要來鎮上趕集的,不過去年和今年都遇上鄭文傑科考,來趕集也沒那個心思,就索在家裡等著。
猜你喜歡
-
完結568 章

長安風流
貞觀大唐,江山如畫;長安風流,美人傾城。 妖孽與英雄相惜,才子共佳人起舞。 香閨羅帳,金戈鐵馬,聞琵琶驚弦寂動九天。 …… 這其實是一個,哥拐攜整個時代私奔的故事。
207萬字8 20502 -
完結212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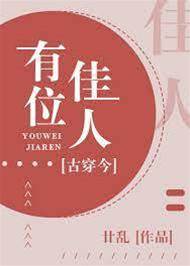
有位佳人[古穿今]
沈嶼晗是忠勇侯府嫡出的哥兒,擁有“京城第一哥兒”的美稱。 從小就按照當家主母的最高標準培養的他是京城哥兒中的最佳典範, 求娶他的男子更是每日都能從京城的東城排到西城,連老皇帝都差點將他納入后宮。 齊國內憂外患,國力逐年衰落,老皇帝一道聖旨派沈嶼晗去和親。 在和親的路上遇到了山匪,沈嶼晗不慎跌落馬車,再一睜開,他來到一個陌生的世界, 且再過幾天,他好像要跟人成親了,終究還是逃不過嫁人的命運。 - 單頎桓出生在復雜的豪門單家,兄弟姐妹眾多,他能力出眾,不到三十歲就是一家上市公司的CEO,是單家年輕一輩中的佼佼者。 因為他爸一個荒誕的夢,他們家必須選定一人娶一位不學無術,抽煙喝酒泡吧,在宴會上跟人爭風吃醋被推下泳池的敗家子,據說這人是他爸已故老友的唯一孫子。 經某神棍掐指一算後,在眾多兄弟中選定了單頎桓。 嗤。 婚後他必定冷落敗家子,不假辭色,讓對方知難而退。 - 新婚之夜,沈嶼晗緊張地站在單頎桓面前,準備替他解下西裝釦子。 十分抗拒他人親近的單頎桓想揮開他的手,但當他輕輕握住對方的手時,後者抬起頭。 沈嶼晗臉色微紅輕聲問他:“老公,要休息嗎?”這裡的人是這麼稱呼自己相公的吧? 被眼神乾淨的美人看著,單頎桓吸了口氣:“休息。”
49.8萬字8 8181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