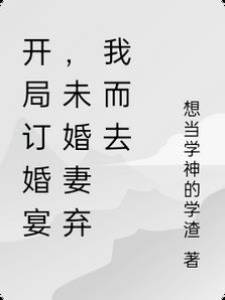《他和星辰吻過你》 第一章 念著
“司歌有什麽難,我會幫襯著,家裏有事,我要是能幫,也絕不會推諉。”周懷謹落下一子,“司歌,我和,不行。”
老爺子急了:“不行?什麽不行?你什麽意思?司歌哪點不好,你和不行?還有顧家的大姑娘,你和人家一起長大,我看你們倒是青梅竹馬的,怎麽也不行?人家顧小姑娘不要你,走了,你想等也等不著了!”
周懷謹任老爺子劈頭蓋臉地罵。
老爺子歎了口氣:“我不你,但你快三十歲的人了,遲早是要和人過日子的。人還是要往前看的,你和七月那姑娘了些緣分,想想別的吧。
“既然不行,和小歌說清楚,別耽誤了人家姑娘。”
周懷謹笑,響亮地答了聲“好”。
正是夕無限好的時候,周懷謹一手撐在二樓的臺上看風景。
大院裏都是這樣獨棟的二層小樓,底下道路開闊,綠樹蔭。
他看見蕭瑀的車開了進來,敢都是周末回家陪家中老人來了。目之所及之,都是一群人一起長大的回憶。
樹蔭下的道路,是一起走過的。那麵牆,是幾個人一起翻過的,顧惜朝作為他的尾,翻不上去,可憐地在牆腳下看著牆上的他們。從他家這棟樓出去,往前走一點,再左拐,就是顧惜朝家。
最遠的小球場是他們幾個人一起打球的地方,幾個小姑娘就坐在一邊的臺階上給他們加油打氣。
顧惜朝的上總有江南子溫婉的氣息,穿一襲素子,不聲不響地看著場,靜好得像是一幅潑墨山水畫。
可是每當他轉過來時,都能看見眼中呼之出的慕和崇拜。
休息時,默默地將水擰開,拿給他。
其他幾個人眼紅,明明手裏已經有水了,還說七月妹妹怎麽就不給他們水。顧惜朝麵皮雖然薄,可還是拿了剩下的水,故作鎮定地擰開,一瓶一瓶地遞給其他人。
Advertisement
景生,周懷謹這些年連大院都不願意多待,吃過飯就開車回自己的住。
邊關月一出診室就拚命地和顧惜朝解釋司歌和周懷謹的關係,這幾年雖然也生周懷謹的氣,可是七月姐喜歡。
“那個司歌和懷謹哥真的沒關係,要說有關係也是周爺爺塞的。我看懷謹哥對一點興趣都沒有,一直都是主的。”
“你胃痛好了,有力氣說這麽多話了?”
顧惜朝擔心的不是周懷謹和司歌的關係,而是周懷謹不再接。
三年了,才明白,一走了之比什麽都簡單,難的是留下的人。三年前做了逃兵,留下他承擔一切,他會原諒嗎?
周懷謹平日裏不是在部隊裏就是在執行任務,難得回來,除了回大院看長輩,就是待在自己的住。
他的住不到一百平方米,是當初他和顧惜朝訂婚之前他用自己攢的工資付的首付,連裝修的風格都是按照顧惜朝的喜好來的。那時候,他以為他們很快會有個家。
周懷謹從電梯裏出來,正掏著鑰匙準備開門,卻看見一個人。
站在他家門口的姑娘刻意打扮過,妝容冷豔,黑的蛋糕,修長的脖頸和凸出的鎖骨,讓像隻黑天鵝一樣麗。
似乎是站累了,倚在門邊,抬起右腳晃了晃腳踝。高跟鞋細細的跟晃過,看上去怎麽也得有個八九厘米。
周懷謹皺了皺眉。
顧惜朝見周懷謹來了,愣了一下,站直了。
“沒想到這裏的治安這麽差了。”他走過,“讓一讓,我開門。”
顧惜朝往旁邊挪了幾步,卻不肯離他太遠。
“我是跟著別人上來的。”
來之前問了沈宴,沈宴告訴周懷謹還住在這兒。沈宴問要做什麽,沒好意思告訴沈宴。也不知道他到底在不在,畢竟他沒多假,一年四季幾乎都在部隊裏,權當運氣吧。
Advertisement
周懷謹是個麵麵俱到的人,當初買這裏的房子,最為看重的一點就是安保,其次才是配套設施。他不能常常在邊,一個小姑娘住的地方,自然得安全些。
這個小區,連單元門都要指紋才能開。
周懷謹開了門,手撐在門框上看顧惜朝。
不語。
他拉了門把要關門:“沒什麽事的話回去吧。”
猛然也手過去握住門把,拚了命地往裏。周懷謹不是不過,而是怕傷著,順當地進來了。
他鞋也不換了,轉過就往裏麵走,沒什麽好臉。
顧惜朝也不管腳下還穿著高跟鞋了,一路小跑過去不管不顧地從後麵抱住周懷謹。
“我是真的知道錯了。對不起,小謹哥哥。我們好好的好不好?”
周懷謹的材壯偉岸,寬肩窄腰翹長。和時下的一些男不同,他的每一塊都實得恰到好,讓人覺得有力量卻不誇張。
顧惜朝的手不安分地挪著,往下再往下,悄然搭上他的皮帶扣。
他像是電一般,猛然打落的手。
他沒有控製好力度,骨與骨發出不小的撞擊聲。他淡淡的眼神掃過去,看見的手背已經通紅。
顧惜朝漆黑的眸子裏有委屈的神,可就是不放棄,上前一步雙手又地扣住他的腰。
他打,痛。可這樣的痛,比他經曆過的又算得了什麽?
“今天見到你和司歌在一起的時候,我是真的怕了。”
周懷謹低著腦袋,看扣在他腰上的手,角略有弧度:“怕什麽?”
“怕你真的有一天,和別人結婚生子,再不回頭。”
說得好似什麽都知道一樣。
周懷謹沒答話。
的腦袋在他背上蹭了蹭:“你們一定沒在一起對不對?”
Advertisement
他不想回答的問題。
和他從小一塊兒長大的,怎麽說也當了他許多年的跟屁蟲,他的態度稍有鬆,便敏地覺出來了。
“我今晚留在這裏好不好?”
“不行。”
周懷謹冷地回絕,三年不見,臉皮倒是見長。
“姑娘家家,一點都不矜持。”
他轉過來,一個反手就拉住的手腕,使了點巧勁,把人往外帶。
的手腕冰得駭人,他的指腹在輕微間,卻像是燃起了燎原的火。
周懷謹克製著自己,不去想其他的。
顧惜朝拗不過他,還沒反應過來自己便已經到了門外。
材高挑,骨架卻很小,有一種纖細窈窕的。眼睛裏帶著淚看人的時候,語還休,十分惹人憐。
現在就用這種眼神看著周懷謹,纖細的雙臂用盡了全力抱著他的手肘。
“那你讓我看看你的傷。”
他盯著的眼神裏有嘲諷的意味:“我渾上下都是傷,你要看哪個?”
顧惜朝知道,他訓練、演習、出任務,被荊棘劃傷,被蛇咬傷,被子彈傷,那些於他都不是傷。
“離心髒最近的那一個。”
“沒有。”周懷謹決然否認。
“東子哥說,兩年前你在執行任務的過程中了傷。蕭瑀哥也說,你被毒販捅了一刀,離心髒很近。”
“他們是不是還說,我差點就要死了?”
顧惜朝點頭。
周懷謹嗤笑一聲:“一群王八蛋,胡說八道。”
顧惜朝搖搖頭:“沈宴哥會嚇我,可東子哥和蕭瑀哥不會。給我看看,好不好?就看一眼!”
幾乎是在低聲下氣地求他。
“沒有。”
周懷謹兩手撐著門框,是打定了主意不再讓進門了,更不可能給看。
“不早了,趕回家。”
話音剛落,門“砰”的一聲關上了。
Advertisement
顧惜朝看著閉的大門,有些無奈又氣憤地跺腳。
眼裏有晶瑩的東西閃了閃,卻被生生地憋了回去,權當自作自好了。
多年的軍旅生涯使得周懷謹的作息一向都十分準時,將人送走了,他便開始洗漱。
人都躺到床上了,他腦子裏像放電影般一幕幕全是剛才的場景。
顧惜朝穿得極,無袖的子,還未及膝。即使是在這樣的夏夜裏,的手還是冰涼的。這樣的孩子,長得又是極為勾人的,大半夜的在外麵晃,一點都不安全。
周懷謹躺不住了,翻坐了起來。
剛坐起來,他又嘲諷地笑了一下。
管幹什麽呢!那麽大的人了,早過了讓人替心的年紀。
他手去拿床頭櫃上的煙,東西剛拿到還沒點燃,又被扔到一邊。
周懷謹認命地歎了一聲,利落地翻下床穿服。
他拿了手機,才想起新換的手機裏早沒了顧惜朝的電話。從前的那個號他倒是還記著,隻是時過境遷,也不知道還用不用。
他一邊給沈宴打電話,一邊準備出去。
剛把門打開,他便愣住了。
沈宴把電話接起來,喂了好幾聲沒人回應,在電話那邊罵了一句,大半夜呢,擾人清夢。
周懷謹把電話掛斷。
顧惜朝竟然沒走,可憐地抱臂站在門外,似乎是覺得冷,微弓著背,一團。
周懷謹心想,都是自找的。
“走吧,我送你回去。”
顧惜朝眼睛亮了一下,然而又認真地一字一句道:“可是我沒帶鑰匙。”
從小就是這樣,看著乖巧溫婉,平時的時候也算得上乖巧溫婉;可耐不住他寵著,耍起小聰明鬧起脾氣來也是一套一套的。
周懷謹今天偏不信這個邪了。
他三步並作兩步走到邊,將其往牆上一摁,一隻手將兩手抬高,另一隻手快速地將的搜了一遍。
他搜得利落、清冷、仔細,不帶任何,像是在搜以往麵對的每一個嫌疑人一般。
顧惜朝翹著角笑意盈盈地看著周懷謹,心卻狂地跳著。
他手上的溫度滾燙,手掌間還有常年訓練留下的繭子,有些糲。
全上下,除了握在手裏的那部手機,當真是什麽都沒有帶。
他鬆開了的手。
確實不是存了別的心思,是因為沒來得及,除了想見他,沒有他想。換了服揣著手機,就出來了,哪裏記得什麽鑰匙錢包。
笑靨如花,坦坦地看著他。
瞳孔漆黑,有,像是無垠大漠裏手可及的星辰。
他挑了挑眉:“我會開鎖。”
“這麽晚了,麻煩你不好吧?”說著,眼睛還往他沒來得及關上的門那邊瞥著,半個背都靠在牆上,小步小步地挪著。
“不算晚。”
周懷謹抬手看了看手表,不到十二點。
夜很寂靜,空曠的樓道裏隻剩他和僵持著,聽得見腕表的嘀嗒聲,也能聽見彼此的呼吸。
的呼吸是紊的,偏偏看向他的水眸裏帶了哀求的意味。
“我那邊太遠,你知道的。你送我過去回來還要許久,開夜車不好的。大半夜的……”
“進來。”
他回往裏走,留下顧惜朝愣了兩秒,才反應過來他在說什麽,於是跟個小尾似的,趕跟在他後麵往屋裏走。
他打開鞋櫃去找拖鞋,翻了半天才找出一雙。
黑的,大,一看就是他的。
顧惜朝快速地往鞋櫃裏瞟了一眼,都是男的鞋,悄悄地彎了角。
晃晃腳,高跟鞋落地,瑩白的腳像魚兒一樣鑽進他拿出的拖鞋裏。
周懷謹麵無表地看著。
腳踝纖細,腳背白皙,很好看。
他覺得自己的目尚算克製收斂,卻像是惡作劇一般又在他麵前晃了晃。不等他有所回應,從他邊溜了過去,走到客廳環視一圈,又穿過客廳,直奔他的臥室。
說是登堂室也不為過。
如果不是那件事發生了,這裏將會是他們的家。裝修的時候顧惜朝也沒盯著,對這裏算是悉。
臥室沒有關門,裏麵的景一覽無餘。
猜你喜歡
-
完結264 章

情是回憶如困獸
曾經發誓愛我一生的男人竟然親口對我說: 顧凝,我們離婚吧!”三年婚姻,終究敵不過片刻激情。一場你死我活的爭鬥,傷痕累累後我走出婚姻的網。後來,我遇見師彥澤。站在奶奶的病床前,他拉著我的手: 顧凝,跟我結婚吧,你的債我幫你討回來。”我苦澀的笑: 我隻是個離過婚,一無所有的女人,你幫我討債? 他笑笑點頭,深似寒潭的眸子裏是我看不懂的情緒。 很久以後,我才明白,在他心裏那不過是一場遊戲 .可師彥澤,你知道嗎?那時候,我是真的想和你過一生。
45.2萬字8 19116 -
完結1774 章

荊棘深處
厲墨和唐黎在一起,一直就是玩玩,唐黎知道。唐黎和厲墨在一起,一直就是為錢,厲墨知道。 兩個人各取所需,倒是也相處的和平融洽。只是最后啊,面對他百般維護,是她生了妄心,動了不該有的念頭。 于是便也不怪他,一腳將她踢出局。……青城一場大火,帶走了厲公子的心尖寵。 厲公子從此斷了身邊所有的鶯鶯燕燕。這幾乎成了上流社會閑來無事的嘴邊消遣。 只是沒人知道,那場大火里,唐黎也曾求救般的給他打了電話。那時他的新寵坐在身邊。 他聽見唐黎說:“厲墨,你來看看我吧,最后一次,我以后,都不煩你了。”而他漫不經心的回答, “沒空。”那邊停頓了半晌,終于掛了電話。……這世上,本就不該存在后悔這種東西。 它嚙噬人心,讓一些話,一些人始終定格在你心尖半寸的位置。可其實我啊,只是想見你,天堂或地獄
276.9萬字8 29007 -
連載16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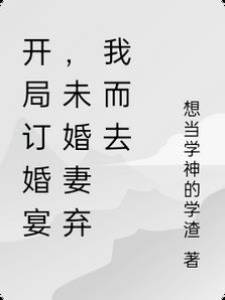
開局訂婚宴,未婚妻棄我而去
微風小說網提供開局訂婚宴,未婚妻棄我而去在線閱讀,開局訂婚宴,未婚妻棄我而去由想當學神的學渣創作,開局訂婚宴,未婚妻棄我而去最新章節及開局訂婚宴,未婚妻棄我而去目錄在線無彈窗閱讀,看開局訂婚宴,未婚妻棄我而去就上微風小說網。
25.2萬字8.18 2427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