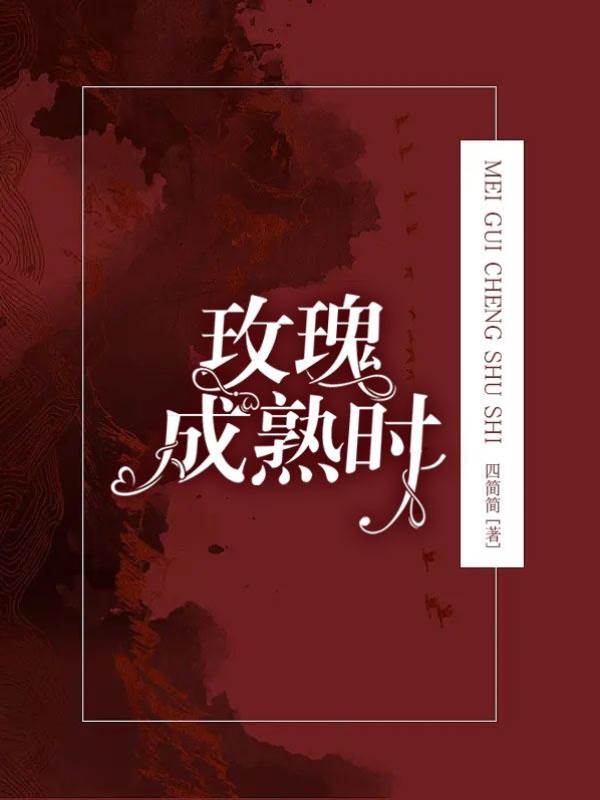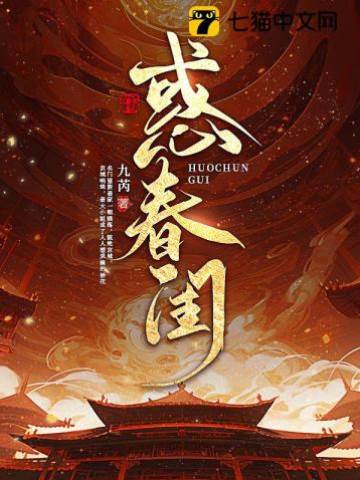《眾神肯為我走下神壇了?不稀罕了》 第7章 忽然間,他好像明白了什麼
“司謠這是瘋了吧!”
沒等沅忱回應,底下被司謠一通發言驚到的弟子們已經顧不得此時的場合了,又紛紛議論起來。
“這還是我第一次見,有人上趕著要求被罰的,嘶,是不是腦子出問題了。”
“……”
周圍的議論還在繼續,一旁靜靜聽著凌樾卻是心復雜。
別人不知道,他卻是知道的,司謠這不是瘋了,只不過是想讓師尊的目多留在上一會兒罷了。
這人為了得到師尊不惜讓出自己的金丹,更是為了拔除與師尊之間的障礙……
想到司謠之前和自己提的計劃,凌樾就一陣氣惱。
心想著這段時間一定要看著點司謠,以防真的做錯事,傷了小師妹。
這般想著,他不又看向司謠和沅忱,見還在極力向師尊推薦罰方式,就不有些干著急。
如果師尊真的同意了,以現在的,本是吃不消的。
“師尊……”眼看沅忱的臉隨著司謠的話越來越難看,他不自覺站起來,為司謠求。
“司謠師妹不是故意來遲和無禮的。”
“因為失去金丹,沒了靈力的緣故,上的傷痊愈得慢,在昨日才剛醒過來,還很虛弱。”
“今日能來已是艱難,遲到了和顧不上禮數也是有可原。”
“師尊您就饒過這一回吧。”
“!!!”司謠瞬間警鈴大作。
在凌樾站出來時就有些不好的預,沒想到就了真!
生怕沅忱真的就聽信了凌樾的讒言,連忙打斷了他,“師兄又不是我,怎知我不是故意如此行事的?”
Advertisement
“我怎會不知,你昨日……”凌樾也急了,顧不得此時的場景,當即就和司謠爭論起來。
“我昨日怎麼了?我昨日還和你較量了一番。”雖然不是拳腳功夫,口舌之爭也算是較量了吧。
司謠真的快被凌樾氣死了,這人到底怎麼回事,偏要幾次三番打斷死遁的計劃。
像以前那樣不管不顧,或是加把刀多好。
“司謠!”凌樾怒了。
兩人就這麼堂而皇之的當著沅忱和眾弟子的面爭論了起來。
在場的弟子們都傻眼了。
令他們傻眼的面不是兩人的爭論,而是不喜司謠的大師兄居然會為司謠求,在司謠不領的況下還似在擔憂對方。
“夠了!”聽夠了二人的爭論,沅忱終是出了聲,臉上的神已經難看到了極點,“為師平日便是這般教你們的?”
“徒兒知錯。”凌樾立即跪地認錯。
“但憑師尊責罰。”這是司謠的。
但就這麼一句話,沅忱本因凌樾的認錯而臉好轉的神當即又難看了起來。
他看向司謠,漆黑的眸中蘊藏著無限危險之意。
這人從今天見他的第一面開始,似就像是在故意惹怒他,剛才還想要他主罰。
為什麼?
腦海中忽然想起在提議怎麼罰時,心里像被大石堵住的不暢。
又想起以往討厭的沈予行,昨日一反常態的為來找他的形,再看剛才同樣不喜的凌樾方才的行為。
忽然間,他好像明白了什麼。
司謠這是在同他置氣,置那日他沒留下的氣,置氣的同時,又耍起了在沈予行和凌樾那很功的苦計。
Advertisement
呵,以為他和沈予行與凌樾一樣那麼好騙麼?
“凌樾,講習結束后自去刑罰堂領罰。”自認為自己掌握了司謠小心思的沅忱當即做出了決定。
“是。”凌樾對此并無意義,只是有些擔憂的暗中看了司謠幾眼。
“至于司謠。”罰完凌樾,沅忱又看向司謠。
被點名的司謠瞬間期待起來。
心里想著連凌樾都要去刑罰堂領罰了,沅忱那麼討厭,罰一定不會被凌樾更輕。
這下,終于可以死遁了。
“依照凌樾所說,你上還有傷,本尊便先不重罰你,待到你傷好之際,本尊便再決定如何置你。”沅忱說。
司謠:“???”
是不是出現幻聽了?
“其實不用對我手下留的。”有些艱難的開口。
“就這樣吧。”沅忱一錘定音,見的反應,他以為自己猜對了,無趣的收回目,又開口道:
“不過,本尊雖先饒了你大過,小過卻不容你,今日你來遲了便是遲了,這般散漫,不能不罰。”
“你就站在一旁,直到講習結束。”
說完,便不再給一個眼神。
司謠:“……”
死亡不易,司謠嘆氣。
事回歸正軌,原以為事就這樣過去了。
不料,半炷香時間都還沒過,又有一來遲的人到了。
“鳶兒因貪玩來遲了些,是鳶兒錯了,師尊,您罰鳶兒吧。”祝鳶單膝跪地請罪。
眾人紛紛看向高坐上的沅忱,想看看剛以來遲罰了司謠的他,會怎麼罰祝鳶,心里都有些擔心起來。
擔心祝鳶會被同樣的責罰。
Advertisement
司謠則一副看好戲的樣子看著。
想看看被全修真界譽為最公平公正的修真界第一名,道宗的宗主,要怎麼在眾弟子的面前不聲的偏袒和袒護人。
是的,袒護,并不認為沅忱真的會為了這麼點小事罰祝鳶。
事實證明,眾弟子都擔憂錯了,而也想錯了。
“無事。”沅忱只是淡淡的掃了祝鳶一眼,便若無其事的道:“來了便坐下吧,你剛好,不宜累。”
明正大的袒護,沒有任何的遮掩和需什麼不聲。
在場的弟子們心里放心了的同時,又不由自主的看向司謠,眼中神有些憐憫,包括凌樾。
他看著司謠,張了張口想和說些什麼,最終卻什麼也沒說。
直到這時,他似乎有些理解司謠為什麼那麼討厭祝鳶了。
“是,師尊。”祝鳶開心的起,坐到了位置上。
【敲!沅忱這狗比太過分了吧,還有周圍這麼多人,見到不公平的事都只會干看著嗎!】將這幕看在眼里的系統忍不下去了,直接破口大罵。
【媽蛋,氣死本系統了!】
“淡定淡定。”司謠卻是輕笑了聲,在腦海中回應系統,“這不是正常做麼,有什麼好生氣的,該習慣了才是。”
在場的眾人雖然聽不到司謠和系統的對話,但聽見了這聲輕笑。
莫名的,都不自覺僵起來,每個人都不是很自在,只覺得一張臉火辣辣的,也不敢再去看司謠。
這本該已經是習以為常的事,今日也不知道為何,心里總有幾分虧欠。
也覺得司謠這一聲輕笑很是刺耳。
Advertisement
同樣覺得刺耳的還有沅忱,一反平日里的孤高清絕,他的眉都皺了起來。
整個現場的氣氛一時都有些怪異。
直到祝鳶坐,沅忱又開始了難道一次的講學才漸漸好轉。
只是這次,每個人都不似之前那麼專心了。
聽著聽著都會不自覺朝司謠投去幾眼,這其中,又數凌樾更甚。
幾乎每隔幾秒,都會朝司謠投去一秒。
司謠倒是沒察覺到這詭異的氣氛,此時的正在腦海中和系統對話。
“系統,我這麼覺有些暈?”問系統。
【暈嗎?】系統一聽,立即開始檢測起宿主的來,【哦,是該暈的。】
【經系統檢測,宿主由于失去金丹,沒有靈力,這幾日又沒進食,之前還失過多。】
【今日又費力爬這麼高的山,這里環境比之山下更冷,寒氣沒有靈力的抵抗直接侵蝕宿主的。】
【現在還只被罰站著,不能坐下休息。】
【幾番下來,自然就不住了,您沒覺到這些不適,也是因為開始了屏蔽負面狀態的功能。】
【所以您會覺到暈是正常的,嗯,幾秒后,您還會直接當場暈倒。】
猜你喜歡
-
完結632 章

絕配良緣,獨寵小醫妃
傳說北野王北冥昱的眼睛盲了,其實,他的眼睛比鷹眼還要亮。 傳說呂白鴦是個啞美人,其實,她的聲音比誰都好聽,連天上的鳳凰鳥聽到她的歌聲都會飛下來在她的頭頂上繞幾圈才肯飛走。 一出調包計,大婚之日,兩頂花橋一齊出府,一齊浩浩蕩蕩地走過京城的大街。 呂國公府上的三千金呂白鴦原本該嫁的人是當今聖上最寵愛的東滄王殿下北冥淵,卻在新婚夜后的隔天醒來時,發現自己的夫君變成盲了眼睛的北野王殿下北冥昱。 陰差陽錯,啞千金配盲夫北野王,絕配!且看他們夫妻怎麼驚艷逆襲,扭轉乾坤,聯袂稱霸江湖,袖手天下,情定三生。
60.3萬字8 194836 -
完結131 章

甜爆!小作精又在撩哄大佬了
[雙重生 雙潔 甜寵 撩哄 追夫 極限拉扯 1V1]十八歲的岑挽笑容明媚張揚,陸北恂隻看一眼便深陷其中。婚後,岑挽把對陸北恂的感情壓抑在心底深處,不曾表露。一年後,陸北恂死了,岑挽痛苦不已,又得知所有真相,極度悔恨,與仇人同歸於盡。岑挽剛意識到她重生了,陸北恂就甩了離婚協議,要與她離婚。她開啟死纏爛打追夫模式,這一世,她要做個狗皮膏藥,甩都甩不掉那種。後來,她被陸北恂以極度占有的姿勢抵在牆上:“我給你最後一次選擇的機會,要離開嗎?”岑挽嬌笑:“我想愛你。”“確定嗎?確定後再想離開我會用特殊手段讓你乖乖聽話。”岑挽無辜眨眨眼:“我現在不乖嗎?”從那以後,她成了陸北恂私有物。某晚,陸北恂附在她耳邊,聲音低磁:“想跑?晚了。”[上一世,他是感情裏的敗將,輸得徹底。這一世,再次重蹈覆轍,他賭對了,他的女孩沒讓他輸。——陸北恂]
22.7萬字8 2574 -
完結149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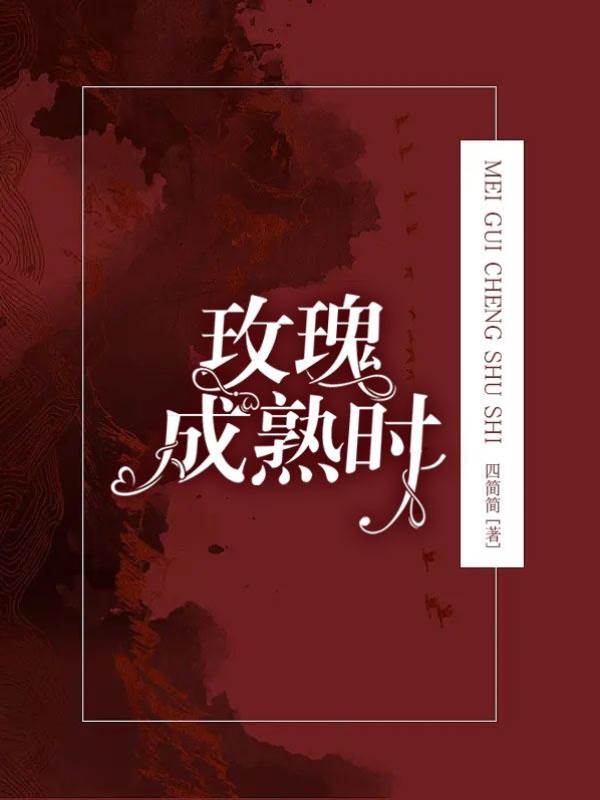
玫瑰成熟時
蘇落胭是京北出了名的美人,祖籍南江,一顰一笑,眼波流轉間有著江南女子的溫婉與嫵媚。傅家是京北世家,無人不知傅城深是傅家下一任家主,行事狠辣,不擇手段,還不近女色,所有人都好奇會被什麼樣的女人拿下。蘇落胭出國留學多年,狐朋狗友在酒吧為她舉辦接風宴,有不長眼的端著酒杯上前。“不喝就是不給我麵子?我一句話就能讓你消失在京北。”酒吧中有人認了出來,“那個是蘇落胭呀。”有人說道:“是那個被傅城深捧在手心裏小公主,蘇落胭。”所有人都知道傅城深對蘇落胭,比自己的親妹妹還寵,從未覺得兩個人能走到一起。傅老爺子拿著京北的青年才俊的照片給蘇落胭介紹,“胭胭,你看一下有哪些合適的,我讓他們到家裏麵來跟你吃飯。”殊不知上樓後,蘇落胭被人摁在門口,挑著她的下巴,“準備跟哪家的青年才俊吃飯呢?”蘇落胭剛想解釋,就被吻住了。雙潔雙初戀,年齡差6歲
23.5萬字8 17099 -
完結275 章

閃婚后首富老公裝窮上癮
為應付父母催婚,紀云緋閃婚同一所醫院的醫生顧瑾。她以為他們倆都是普通打工人,雖然現在窮,但只要一起努力,未來就充滿希望。可沒過多久,紀云緋詫異地看著自己名下一摞財產。“車子哪來的?”“喝奶茶中獎送的。”“別墅哪來的?”“老家的房子拆遷換的。”“他們為什麼喊我院長夫人?”“我連續一百天沒遲到他們就讓我當院長了。”紀云緋“……我信你個x!滾!”顧醫生抱緊老婆卑微挽留“別走,沒有你我就一無所有了。”火山護士x冰山醫生高甜無虐,女主不挖野菜,全程搞錢!
52.2萬字8.25 46700 -
完結17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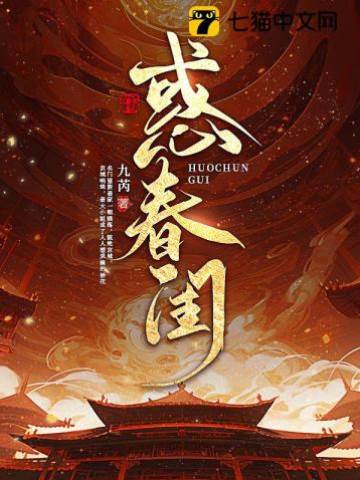
惑春閨
名門望族薑家一朝隕落,貌絕京城,京城明珠,薑大小姐成了人人想采摘的嬌花。麵對四麵楚歌,豺狼虎豹,薑梨滿果斷爬上了昔日未婚夫的馬車。退親的時候沒有想過,他會成為主宰的上位者,她卻淪為了掌中雀。以為他冷心無情是天生,直到看到他可以無條件對別人溫柔寵溺,薑梨滿才明白,他有溫情,隻是不再給她。既然再回去,那何必強求?薑梨滿心灰意冷打算離開,樓棄卻慌了……
31.5萬字8.18 7894 -
完結868 章

病態陰鷙!京圈大佬被寵成小哭包
"前世,陸昭昭錯信他人,間接害死了愛她入骨的男人。重生回兩人相親第一天,陸昭昭果斷拉著宋斯年領了結婚證。她忙著虐渣打臉,面對述情障礙的老公,陸昭昭就只有一個原則,那就是愛他。陸昭昭不知道的是,她是宋斯年唯一的光,他病態、偏執卻唯獨不敢把他真正面目暴露在她面前。可紙終究包不住火,當他的一切被擺在她眼前的時候,宋斯年緊緊摟住了她的腰,紅著眼,埋在她的頸窩里聲音怯怯的問,“昭昭,你是不是不想要我了?”"
134.7萬字8.18 54915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