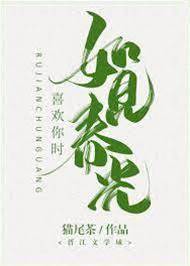《撩欲》 第68章 白襯衫下黑到極點的心
祁硯按著的腳腕,不讓。
“乖一點。”
畢竟踢的話,他倒沒事,就怕扯著舒漾的傷口。
看這個況,可能還要吃點消炎藥,以防傷口惡化。
隻是蹬了蹬,舒漾就疼的直皺眉,忍不住吐髒字。
“艸……”
有些痛是後知後覺的,昨天的時候,舒漾還不覺得會這麽嚴重,畢竟祁硯做事有迷。
隻是胃部難,像是有人在肚子裏釘釘子,一陣反胃想吐。
今天傷就明顯開始發作了,純粹的是痛。
“我不會真要進醫院吧?”
想到這,舒漾小拳頭直接往他上砸,“祁硯,都怪你都怪你都怪你!”
男人毫沒躲,俯親著,語調,“好好好,怪我,我的錯。”
“乖一點好不好,不塗藥會發炎的。”
他今天醒來就馬上安排人送藥過來,想在舒漾睡覺的時候,把藥塗了。
就是知道這小朋友醒來後,肯定沒那麽好說話。
果然,現在一點都不配合。
剛才隻是看了看那傷,紅的有些目驚心。
Advertisement
他難得小心翼翼,本不敢,怕一不小心就下手重了。
“你那會兒怎麽不想著會發炎?”
舒漾完全聽不進去任何好話,就是個冷嘲熱諷的氣包。
看著祁硯上的白襯衫,和鼻梁上明的眼鏡,顯然是又恢複以往冠楚楚的樣子,更是心理不平衡。m.x33xs.
“現在穿的人模人樣的,準備做人了?”
誰不知道那白襯衫下,是一顆黑到極點的心。
那雙疏離的眸子,和八百年不人的清貴佛子臉,本就是假象。
祁硯無從反駁,先把藥放下,坐到旁邊,一手把人抱過來。
“老婆,你生氣可以,你想怎麽罵就怎麽罵,但是先把藥塗上好嗎?”
“發炎了一時半會兒好不了,還會滋生病菌的。”
“……”
舒漾心裏真的有點害怕祁硯說的那些,心裏強裝鎮定的不去看他。
這次不把事捋清楚,以後那還得了。
一次躺三天的程度,幹脆不用出門了。
“明明我上的傷,都是你一手造的,現在又來裝老好人。祁硯,我真是看你了!”
Advertisement
昨天不管說什麽,好的壞的髒的,哭的昏天黑地,祁硯理都不帶理一下。
每次都連哄帶騙的說著,“寶寶,最後一次。”
最後已經快昏死過去,地上丟了一個又一個,也沒等到那最後一次到頭。
再也不會相信,這個男人裏的鬼話。
簡直就是謊話連篇。
男人裏的話,十句話,九句假,還有一句床i|上的,更假!
“寶貝,對不起。”
祁硯又無奈又拿沒辦法,事是自己做出來的。
也知道小孩現在說的是氣話,自然不會往心裏去。
“衝是真的,擔心你也是真的,你生病我會心疼的。”
舒漾還在氣頭上,有臺階不下,祁硯就一直遞臺階。
他換個出發角度,試圖說服。
“對不起寶貝,昨天是我們結婚後的第一次,又恰好上我過生日,我的生日願就是每天都可以和你在一起,哥哥承認是有些衝了,原諒我好不好?”
舒漾瞪了他一眼,“你那有些衝?”
Advertisement
都快懷疑,是祁硯畢生仇人的程度,恨不得分分鍾弄死。
祁硯說話溫溫的,“寶寶,是你自己的,傷了要惜知道嗎?”
他的耐心完全是這幾年,在舒漾邊鍛煉出來的。
以至於即便這個人再難哄,也並不覺得有什麽問題。
把人養了才好。
以後沒人得了舒漾的脾氣,還怕他的寶貝去找別的野男人嗎。
舒漾抿著,有些被說了。
沒像剛才那麽強勢,隻是小聲的抱怨著。
“原來你也知道是我的。”
祁硯:“我的也是你的。”
舒漾撇嫌棄,“婉拒了您嘞!”
見緒好轉了些,男人眸中多了笑意。
他們是夫妻啊,他寶貝的不就是他的。
壞了他以後怎麽辦。
當然心疼。
看到一旁的藥膏,舒漾有些別扭,“你把藥放那就好了,我自己會塗。”
祁硯對這最後的倔強,忍俊不。
他的寶貝老婆,怎麽這麽可啊。
舒漾不明所以,“你笑什麽?”
Advertisement
祁硯的腦袋,“你看得見嗎?打算自己瞎塗?”
“……”
舒漾避開他的眼睛,“塗藥又不要什麽技。”
雖然好像這種事自己來,確實覺怪怪的。
可是,讓祁硯下手,也好不到哪裏去啊!
簡直無法麵對。
祁硯失笑的看著,“那什麽要技?”
舒漾臉一黃,“……”
急忙轉移話題,“還塗不塗藥了!”
祁硯睨了一眼床中心,眉眼一挑,示意躺好。
舒漾視死如歸般往床上一倒,把臉一捂。
“你快點!”
。您提供大神妘子衿的
猜你喜歡
-
完結388 章

前妻不好惹:復婚?沒戲
人人都說司徒總裁對她專一深情,眼中才容不得其他女人。 可誰知道她千淨茉也不過是走不進他眼中的'其他女人'罷了。 結婚兩年,她嬌蠻過、溫柔過、體貼過、惱怒過、低聲下氣過、無微不至過...... 卻從未走進他心裡過...... 這本是一場無愛的婚姻,她卻懇切強求著能用心血澆灌開出一朵花來。 可心血用盡,這場婚姻,依舊寸草不生。 眼前卻是丈夫跪在別的女人腳邊深情呢喃堅定承諾......
105.7萬字8 18663 -
完結18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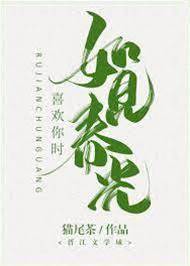
喜歡你時,如見春光
朋友給周衍川介紹了一個姑娘,說她不僅臉長得好看,學識也很淵博。 周衍川勉為其難加好微信,禮節性問:“林小姐平時喜歡什麼?” 林晚回他:“我喜歡看鳥。” “……” 周衍川眉頭輕蹙,敷衍幾句後就沒再聯繫。 後來朋友問起他對林晚的印象,周衍川神色淡漠,連聲音都浸著寒意:“俗不可耐。” · 時隔半年,星創科技第三代無人機試飛,周衍川在野外見到了林晚。 她沐浴在漫山春光之中,利落地將三角架立在山間,鏡頭對準枝頭棲息的一隻小鳥,按下快門時,明艷面容中藏進了無限柔情。 回城的路上,周衍川見林晚的車子拋錨,主動提出載她一程,怕她誤會還遞上一張名片:“你放心,我不是壞人。” “原來你就是周衍川。” 林晚垂眸掃過名片,抬頭打量他那雙漂亮的桃花眼,幾秒後勾唇一笑,“果然俗不可耐。” 周衍川:“……”
28萬字8 18189 -
完結169 章

驚覺相思不露,原來隻因入骨(盛夏裔夜)
四方城有一聲名狼藉的女人,盛夏。男人認為她人人可夫;女人認為她放蕩不堪。可,實際上她不過是在愛上了一個人而已。為這個人,她這輩子,第一次用了最見不得人的手段。婚後五年,她受盡冷嘲熱諷,受遍他的冷暴力,她為他九死一生,依舊換不回他的回眸。“裔夜,愛盛夏,那麼難嗎?”她問。他隻說:“...
74.6萬字8 10065 -
完結252 章

離婚后,我虐前夫千百遍
暗戀江時羿的第十年,顧煙夙愿得償,成了江太太。她以為,他們會一生一世一雙人,直到他的白月光回國。那一夜,她被人所害陷入危難,滿身鮮血,求助于他,卻聽到電話那端女人的嬌笑。暗戀他十年有余,離婚轉身不過一瞬間。后來,江時羿在每個深夜看著她的照片,數著她離開的時間,從一天一周,到一月一年。直到經年后再重逢,他孑然一人,眼尾泛紅地盯著她,而她領著軟軟糯糯的小姑娘,泰然自若同他介紹“我女兒。”
49.7萬字8.18 24233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