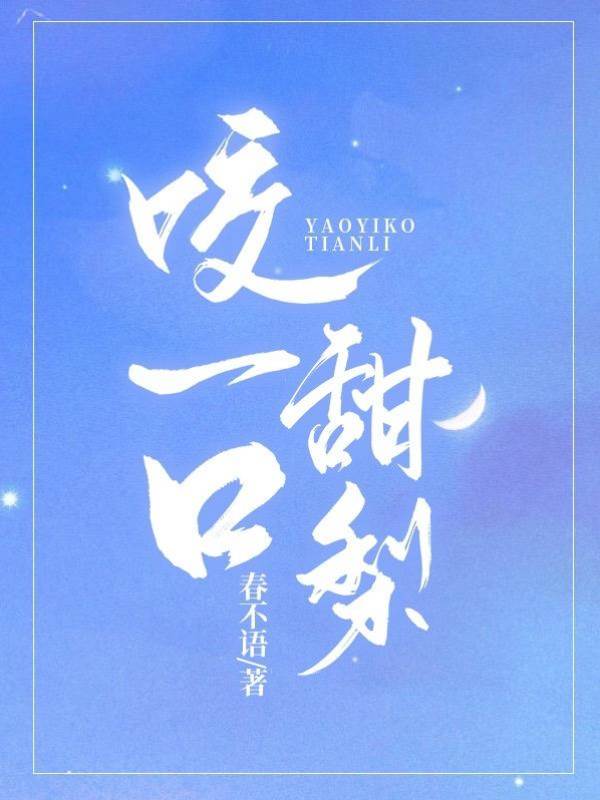《如虹不落》 第 82 章
紀箏差點炸。
周司惟及時收回逗人的手,回到駕駛座開車,轉移話題:「據我所知,溫遇深隻有一個姐姐,而他姐姐早年喪夫之後終未再嫁,應當是沒有外甥的。」
「也許是表親。」紀箏猜測,手機響起來,是葉梅打來的電話,連忙接起來。
明天就是婚禮,葉梅打來電話,催促早點回家。早在婚禮時間確定下來之後,葉梅就態度堅決,要搬回家住,即便隻是走個形式,也必須從家裡出嫁。
加上別的事忙東忙西,這段時間和周司惟見面並不多。
快到家的時候,紀箏遠遠便看見葉梅攏著厚針織衫等在門口,下車,周司惟跟著也下來,將忘拿的懷聿和弗蘭克斯送的禮送過來。
「小周開車回去慢點。」葉梅關切道:「天黑,注意安全。」
紀箏接過盒子,心一跳,礙於葉梅在場,不能說些什麼,隻能看著周司惟和葉梅說了幾句話後開車離去。
Advertisement
婚禮前一夜基本是沒有什麼好睡的,紀箏被葉梅拉著說了很久的話,迷迷糊糊睡了一會兒之後又早早就醒做妝發。
場所辦在一棟北歐挪威風格的洋房別墅,外觀皆是雕著緻圖案的深卡其古磚,室穹頂鑲嵌彩玻璃,穿過,被折得斑斕和。
別墅是中國式園林,小橋流水環繞著織錦木與古杏樹等名貴樹木,紅毯從的草地鋪到盡頭。
紀箏親自挑的地方,場面布置也都是用了心。
從早到晚,紀箏沒睡醒,耳邊又被妝發師等一群人環繞著,耳朵腦袋都是懵懵的,打著哈欠換上婚紗,由著別人幫整理。
這婚紗試穿過,並不是第一回見,然後轉看到鏡子的剎那,還是剎那間驚醒了過來。
不比上次的試穿,這次做足了妝發,長發半編起來,潔白飄逸的頭紗延至地面,化妝師的好手藝讓面龐鮮活生了起來,越發顯得明緻,一顰一笑都顧盼生輝。
Advertisement
而上的這件婚紗,本便像一場夢,輕紗層層堆疊。整件婚紗墜滿緞織就的玫瑰,寶石鑲嵌出流溢彩的彩,輕微作間仿佛鎏彩月籠。
然驚艷地看著鏡中人,不由得慨:「周司惟真是好福氣。」
頭紗掀到前面遮住臉,紀箏拿上捧花,在引領下走出去。
挽著紀城譽的手,走上長長紅毯,紅毯的盡頭,是周司惟。
白的輕紗朦朧,紀箏看不清他臉上的表,但仍然能覺到,他隻落到一人上的目。
春日的溫如水,院中草木花葉隨風輕輕拂,送來清麗香氣。
紅毯兩側是觀禮賓客,椅背上繫著白紗與鮮花。
人造噴泉呈圓形噴出的水流在空中微微霧化,籠罩在日下,塑造出朦朧又夢幻的彩虹。
草長鶯飛,滿園春。
周司惟凝視著向他走來。
Advertisement
他想起很多很多個從前,想起暗無天日的斥責和辱罵,一下下落在上的菸頭和棒。
想起終日充滿人的哭聲和男人怒罵的家。
那並不能稱之為家,周司惟從來厭煩這個字眼。
想起青年時期,那一段如夢似幻,終究破滅的好時。
想起曾經年復一年的孤寂與空曠。
到今日,都不復存在了。
以後也將不存在。
他從來不曾過這個世界,世界也不曾善待於他。
可是世上有,於是他願意收起所有戾氣怨恨,隻餘溫和寬容。
神世人,他隻。
紅毯走到盡頭,紀箏停在周司惟面前。
從爸爸臂彎中出手,帶著白緞面手套的手,放到他掌心。
周司惟合攏手,握於其中。
約在面紗下的明容,對他輕輕一笑。
後噴泉造出的彩虹在驀一刻亮如五彩琉璃。
Advertisement
「你願意接他為你的丈夫,從今以後永遠擁有你,無論環境時好時壞,是富貴是貧賤,是健康是疾病,都他,尊敬他,珍惜他,直至死亡將你們分開嗎?」
「我願意。」
周司惟俯,拉著的手,隔著面紗,邊印下一吻。
紀箏眸中映著璀璨日,亮盈盈看著他,目不轉睛。
他的鼻尖,停在毫釐之距的地方,目溫深。
「落落,」他說:「死亡也不能將我們分開。」
猜你喜歡
-
完結223 章

總裁追婚記:嬌妻哪裏逃
三年前,初入職場的實習生徐揚青帶著全世界的光芒跌跌撞撞的闖進傅司白的世界。 “別動!再動把你從這兒扔下去!”從此威脅恐嚇是家常便飯。 消失三年,當徐揚青再次出現時,傅司白不顧一切的將她禁錮在身邊,再也不能失去她。 “敢碰我我傅司白的女人還想活著走出這道門?”從此眼裏隻有她一人。 “我沒關係啊,再說不是還有你在嘛~” “真乖,不愧是我的女人!”
29.6萬字8 5231 -
完結1939 章

替嫁后我被大佬纏上了
所有人都說,戰家大少爺是個死過三個老婆、還慘遭毀容的無能變態……喬希希看了一眼身旁長相極其俊美、馬甲一大籮筐的腹黑男人,“戰梟寒,你到底還有多少事瞞著我?”某男聞言,撲通一聲就跪在了搓衣板上,小聲嚶嚶,“老婆,跪到晚上可不可以進房?”
290萬字8.18 189231 -
完結105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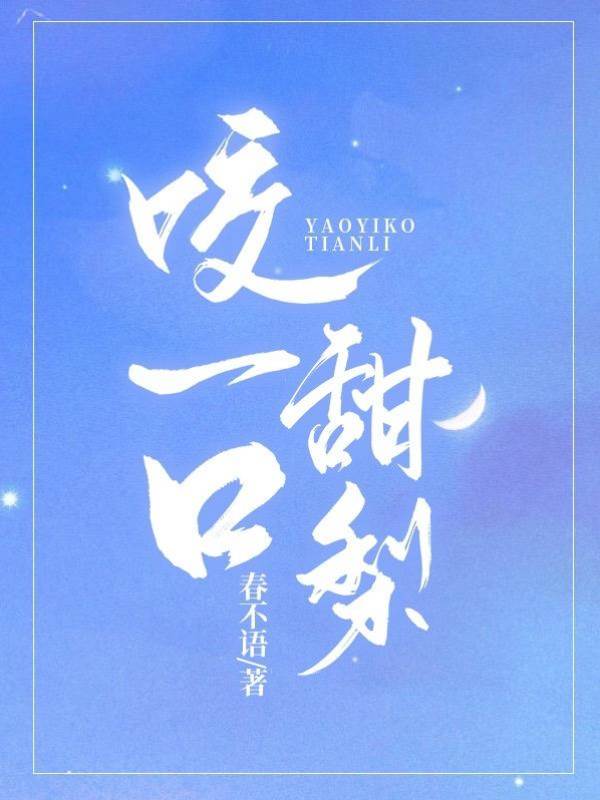
咬一口甜梨
白切黑清冷醫生vs小心機甜妹,很甜無虐。楚淵第一次見寄養在他家的阮梨是在醫院,弱柳扶風的病美人,豔若桃李,驚為天人。她眸裏水光盈盈,蔥蔥玉指拽著他的衣服,“楚醫生,我怕痛,你輕點。”第二次是在楚家桃園裏,桃花樹下,他被一隻貓抓傷了脖子。阮梨一身旗袍,黛眉朱唇,身段玲瓏,她手輕碰他的脖子,“哥哥,你疼不疼?”楚淵眉目深深沉,不見情緒,對她的接近毫無反應,近乎冷漠。-人人皆知,楚淵這位醫學界天才素有天仙之稱,他溫潤如玉,君子如蘭,多少女人愛慕,卻從不敢靠近,在他眼裏亦隻有病人,沒有女人。阮梨煞費苦心抱上大佬大腿,成為他的寶貝‘妹妹’。不料,男人溫潤如玉的皮囊下是一頭腹黑狡猾的狼。楚淵抱住她,薄唇碰到她的耳垂,似是撩撥:“想要談戀愛可以,但隻能跟我談。”-梨,多汁,清甜,嚐一口,食髓知味。既許一人以偏愛,願盡餘生之慷慨。
20.2萬字8 7865 -
連載256 章

全球通緝令,抓捕孕期逃跑小夫人
曾經顏琪以爲自己的幸福是從小一起長大的青梅竹馬。 後來才知道所有承諾都虛無縹緲。 放棄青梅竹馬,準備帶着孩子相依爲命的顏鹿被孩子親生父親找上門。 本想帶球逃跑,誰知飛機不能坐,高鐵站不能進? 本以爲的協議結婚,竟成了嬌寵一生。
45.2萬字8 4662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