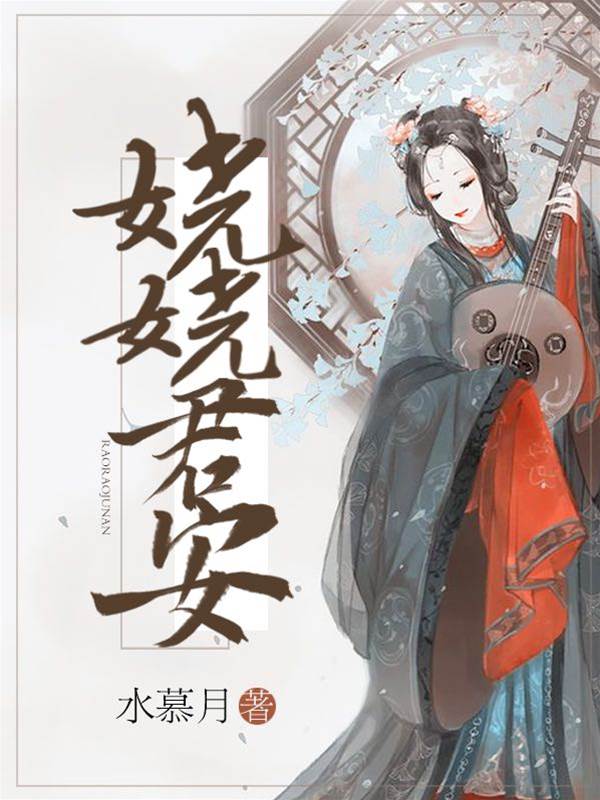《何不同舟渡》 第114章 笑中淚
一赤烏躍出江麵,天邊霞萬丈,金的芒熠熠生輝地照在上,一切仿佛都神聖極了,此不應是人間,而是天上宮闕。
謝卻山有種錯覺,這並不是他偶然窺見了自然之,而是神明專門為他上演了一場刺破黑暗的大戲。
隨著旭日越升越高,線反而和下來,均勻地揮灑在山川之上,這種膨脹的幻覺最終輕飄飄地、平穩地落了地。
沐浴在日下,瞇著彎彎的月牙眼,略顯得意地看著他。恍惚間,好像在他眼裏看到了晶瑩剔的東西,笑容緩緩地僵住了,有些難以置信。
“謝卻山,你掉眼淚了。”
謝卻山覺得自己快要被這太照得散了,照得化了,他猛地回神,下意識便否認了。
“沒有。”
他地轉想回房間。
“啊啊啊——”
南忽然一個沒坐穩,整個人往後傾去,手胡地揮舞著,像是要跌江中。
“南!”
謝卻山一著急,連忙回想手拉住,卻隻聽鐵鏈錚地一聲,他的手沒能夠到,隻在空氣中撈了一下。
他的大腦嗡得一下空白了一瞬。
結果南自己氣定神閑地從船舷上跳了下來,趁勢握住了謝卻山的手,臉上出了一個狡黠的笑容:“我騙你的。”
湧上頭顱的沸騰著在他裏回落,謝卻山錯愕地頓了頓,剛才那個瞬間,他真的以為自己抓不住了。
而就在這個他毫無防備的時候,已經湊到了他麵前,認真地注視著他的眼睛:“你就是哭了。”
他立刻否認:“是太刺眼了。”
他怎麽可能當著的麵落淚。謝卻山悶頭往屋裏走。
“你胡說。”
南屁顛屁顛地跟上去,彎著腰探出腦袋去看他,他偏過頭不讓看。
Advertisement
“——你不會真以為我要掉下去吧?”
“——我就跟你開個玩笑,你生氣啦?”
“——咋還不理人呢。”
“——誒,哭就哭了,這有什麽不好承認的。”
“都說了沒有!”他有些氣急敗壞了,出了鮮有的緒失控。
“那我要哭了。”
謝卻山:?
謝卻山回頭,見固執地站在原地,氣呼呼地看著他。真的是說哭就能哭,眼裏湧出豆大的眼淚,一顆一顆白珍珠似的往外蹦。
怎麽還反咬一口呢。
“誒……你,你別演。”
南本來是有點裝的,可他這麽一說,忽然就真實起來,心裏的委屈一腦都湧了出來。
哪演了。分明為他提心吊膽,他居然還說演的!
這下好了,這句話反而讓南越哭越兇,索一屁坐在地上,嚎啕大哭起來。
一張梨花帶雨的臉龐皺,氣呼呼的,像是做給他看似的,用力而誇張地噎著,可細看又像是真的傷心。
謝卻山不知道該怎麽麵對哭泣的南。他甚至都清楚這也許是的小伎倆,但這小伎倆是為了他,他還是非常心疼。以前在他的生命裏不就要哭的孩還是他的妹妹謝小六,但那好像又不一樣,小時候他們總是會有明確的爭執,謝小六才會哇哇大哭,可現在南是為什麽而哭呢?他有點無措,他並沒有哄孩的經驗。
他繞到麵前,在邊蹲下,小心翼翼地了一下。
“別哭了,好不好?”
但南本不買賬,一下子就地打開了他的手。
“不好。”
“為什麽呀?”
“你都不跟我講話……”一癟,想到這兩天謝卻山本不搭理,還一直熱臉冷屁,頓時覺得委屈極了,才說了幾個字,又哇哇地哭了起來,“你這個沒良心的,虧我還帶你看日出……你還兇我……”
Advertisement
“我沒有。”謝卻山覺得自己冤枉死了。
“你就有!”
這個時候,不管說什麽,都絕對不能反駁。謝卻山也不犯倔,立刻態度極好地認錯。
“對不起,兇你是我不對。”
“那你以後要跟我講話!”
“好,我天天都跟你講話。”
目的達了!
得到這樣的承諾,南心裏有點高興,這點高興迅速過了的委屈,甚至浮到角,了一個忍俊不的弧度,但又知道不能太得意忘形,否則顯得太刻意,又迅速忍了下來。
但這點小小的變化,還是被謝卻山捕捉到了,他無奈地了的臉蛋。
南雖然氣消了,但自知氣勢不能矮,怎麽能隨便和好呢,立刻把謝卻山的手扯下來。
也不知怎麽的,謝卻山突然起了一點無聊的勝負,不肯鬆手,捧著南的臉使勁,這臉蛋白白極有手,像是在麵團。南打不過就加,也報複似的手,一把起謝卻山的臉。
兩個人看著被對方揪得變形有點稽的臉,噗嗤一聲,不約而同地笑了出來。
彼此的目都漸漸了下來,含著幾分旖旎的暗波,像是劫後餘生的息。
謝卻山突然又將手放了下來,曖昧轉瞬即逝,很快恢複如常
南忽然很認真地看著謝卻山,眼中著疑。
“你為什麽都不……不……”
起頭幾個字還是理直氣壯的,說到後來聲音越來越小,臉頰莫名紅了起來。
謝卻山不知道還有什麽審判,誠惶誠恐地聽著。
“……不願同我親近。”
最後幾個字小聲如蚊蠅,但謝卻山聽清了。
他的臉一下子也紅了,他沒想到話題會落在這麽一個讓人麵紅耳赤的地方。
他慌地抬眼,臉上青青白白一片淚痕,底下泛出點紅暈來。除了赧,還有真實的困。
Advertisement
他們之間,從未有過山盟海誓的隻言片語,但相信的本能。思想、語言、神態,都可以偽裝,唯有本能裝不出來,通過每一次的親,都能到他也是著的。
可不知道,現在他怎麽能這麽冷淡,究竟是裝出來的,還是真的?
本於說出口,但在緒崩潰的當下,的念頭和困愈發強烈。就是人的擁抱與親吻,人是,要先誠實地麵對自己的。
難道他沒有過這種嗎?
他對這個世界,就沒有一點留,包括對也一樣嗎?那他們算什麽?水鴛鴦?
知道他的艱難,可依然有點傷心。
謝卻山張想辯解什麽,混的思緒最終還是梗在間。
他以為隻有他在痛苦地忍著,與自己、與外界拚命對抗,此刻他才後知後覺地意識到,這些日子的聒噪無畏需要多大的勇氣,心裏也抑著巨大的委屈。
實際上,比他更勇敢。
他傾過,近乎虔誠地親吻了。
這是一個臨淵羨魚的吻。
南撲簌而無聲地流著淚。他什麽都沒有說,可有些明白了。
……
自那之後,謝卻山從一蹶不振的沉默中緩了過來。也許是南日複一日的搖染了他,也許是因為金陵那邊遲遲沒有消息,昭示著事在往好的方向發展,總之,這一點點態度的緩和讓南覺得有希了。
是一個抓著一點桿就要往上爬的人,既然謝卻山開始配合了,就要在他鬆之時,趕想辦法和他一起逃出這個地方。
當務之急還是想辦法打開謝卻山手上的鐐銬。
前幾天就觀察過了,這是玄鐵鏈,砸也砸不斷,隻能從鎖頭上花功夫。
倒是會一點難以啟齒的開鎖的本事,開個普通的小鎖不在話下,但這可是章月回上的鎖,他想要關住一個人,絕不可能讓人輕易逃。
Advertisement
鎖的結構十分複雜,南拿鐵搗鼓了半天,一無所獲。
甚至開始破罐子破摔地想,真想著章月回把人放了,不行就做出濺三尺,死在他麵前的架勢,但也知道章月回的境也沒那麽容易,能幫的,他其實已經幫了。
兩個大活人,還能被一把小小的鎖困住不!
南越挫越勇,整日就抓著謝卻山的手研究鎖頭,這弄得謝卻山也寸步難行。
這下倒好,他是想跟說話來著,一開口出聲,便一擰眉頭要他閉,得細細聆聽鎖機關咬合的聲音。
謝卻山耐著子任折騰,老老實實地坐著,連大氣也不敢,隻能拿了本書卷看。
半晌,一點聲都沒出,一直抓著他的手,保持著側耳傾聽的姿勢。謝卻山有點疑,小心翼翼地側頭去,發現竟趴在他的上睡著了。
手裏還抓著一鐵,柳眉輕蹙,睡著的表仍是一臉嚴肅。
謝卻山忍俊不,輕輕抬手開的眉。
他細細端詳著的臉龐,初見時這張麵黃瘦的臉逐漸變得盈白潤,像是長開了的樹,枝頭爭先恐後地冒出花朵,不知不覺間,原來已是滿枝芬芳了。也許是他給了雨,但恣意地按著自己的方式在長。
蓬的生機,真好。
他想一直活在這份春天裏。
漸漸地,他的眼神卻又落寞下來。
這時,南猛地驚醒,茫然地抬頭張了一下,都已經夜了。見謝卻山偏著頭在看,有些不好意思起來,心虛地角,還好沒流口水。
“我可沒睡過去,剛剛是在閉目思考。”
謝卻山附和地點點頭,也不破。
故作忙碌地用手扇了扇風:“哎呀,這天氣是越來越悶熱了,腦子都轉不了,我,我去開個窗。”
南跑到窗邊,推開了窗戶,由著江風灌進來,腦中瞬間清醒了不。
心裏的焦灼又湧上來。這鎖怎麽都搗鼓不開。
這可不是遊戲或者玩笑,這關乎著謝卻山的命,給了自己很大的力。
忽然安靜下來,謝卻山有些疑。
謝卻山抬頭了一眼,趴在窗沿上,隻穿了一件寬大的春衫,微黃的燈籠將衫照得半,窈窕的肢擺弄出隨意的曲線。風扯著袍衫,著,若若現,朦朦朧朧。
食也。
謝卻山歎了口氣,他都不知道自己在當什麽聖人。
他走到窗邊,自後麵環抱住了。
溫熱的懷抱覆了上來,南驚訝地側臉眼眸著他,覺得他有點反常,但又覺得自己想多了,倏忽開心地笑了起來。
想轉過,但他就這麽固執地箍著,將下放在的肩窩上,臉頰著的烏發。
“別。”
半晌,南還是好奇,問道:“你在看什麽?”
“看景。”
這大半夜,外麵都黑漆漆的。
“哪來的景。”
“都在這裏了。”他沒頭沒腦地回了一句。
江風和。
謝卻山出神地發著呆,與一起著靜謐的此刻。
他們見天地日月,見江海山川,卻也隻是蜉蝣。得一刻屬於彼此的安寧,竟也覺得人生已經值得。
——
金陵。
遮得不風的房間裏,完若展開了一張紙箋。
“已確認:代號雁即謝卻山。”
完若角勾起了一個勝券在握的笑容。
局中博弈瞬息萬變,焉知這是誰的局?
猜你喜歡
-
完結389 章

農門姐弟不簡單
穿越而來,倒霉透頂,原身爹爹戰亂而死,送書信回家後,身懷六甲的娘親一聽原地發作,立即生產,結果難產大出血而亡。 謝繁星看著一個個餓的瘦骨嶙峋還有嗷嗷待哺的小弟,她擼起袖子就是乾,看著滿山遍野沒人吃的菜,有這些東西吃,還會餓肚子、會瘦成這樣? 本以為她這是要帶著弟妹努力過活,改變生活過上好日子的,結果,弟妹沒一個簡單的。 本文又名《弟妹不簡單》《弟妹養成記》《弟妹都是大佬》《全家都是吃貨》
70.4萬字8.18 36046 -
完結10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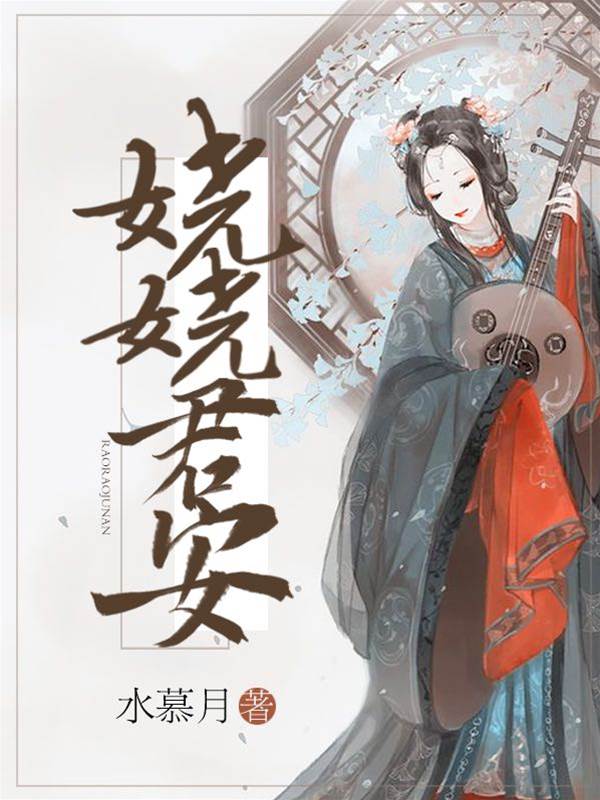
嬈嬈君安
原想著今生再無瓜葛,可那驚馬的剎那芳華間,一切又回到了起點,今生他耍了點小心機,在守護她的道路上,先插了隊,江山要,她也絕不放棄。說好的太子斷袖呢!怎麼動不動就要把自己撲倒?說好的太子殘暴呢!這整天獻溫情的又是誰?誰說東宮的鏡臺不好,那些美男子可賞心悅目了,什麼?東宮還可以在外麵開府,殿下求你了,臣妾可舍不得鏡臺了。
16.6萬字8 14001 -
完結171 章

錯撿瘋犬后
病嬌太子(齊褚)VS聰慧嬌女(許念),堰都新帝齊褚,生得一張美面,卻心狠手辣,陰鷙暴虐,殺兄弒父登上高位。一生無所懼,亦無德所制,瘋得毫無人性。虞王齊玹,他的孿生兄長,皎皎如月,最是溫潤良善之人。只因相貌相似,就被他毀之容貌,折磨致死。為求活命,虞王妃許念被迫委身于他。不過幾年,便香消玉殞。一朝重生,許念仍是國公府嬌女,她不知道齊褚在何處,卻先遇到前世短命夫君虞王齊玹。他流落在外,滿身血污,被人套上鎖鏈,按于泥污之中,奮力掙扎。想到他前世儒雅溫良風貌,若是成君,必能好過泯滅人性,大開殺戒的齊褚。許念把他撿回府中,噓寒問暖,百般照料,他也聽話乖巧,恰到好處地長成了許念希望的樣子。可那雙朗目卻始終透不進光,幽深攝人,教著教著,事情也越發詭異起來,嗜血冰冷的眼神,怎麼那麼像未來暴君齊褚呢?群狼環伺,野狗欺辱時,齊褚遇到了許念,她伸出手,擦干凈他指尖的血污,讓他嘗到了世間的第一份好。他用著齊玹的名頭,精準偽裝成許念最喜歡的樣子。血腥臟晦藏在假皮之下,他愿意一直裝下去。可有一天,真正的齊玹來了,許念嚴詞厲色地趕他走。天光暗了,陰郁的狼張開獠牙。齊褚沉著眸伸出手:“念念,過來!”
26萬字8 7046 -
完結232 章

陛下輕點罰,宮女她說懷了你的崽
為了活命,我爬上龍床。皇上不喜,但念在肌膚之親,勉強保了我一條性命。他每回瞧我,都是冷冷淡淡,嘲弄地斥一聲“蠢死了。”我垂頭不語,謹記自己的身份,從不僭越。堂堂九五至尊,又怎會在意低賤的宮婢呢?
43.7萬字8.18 5197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